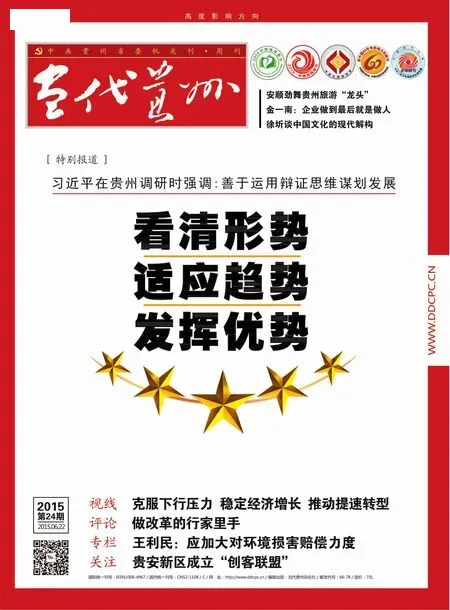應當加大環境損害賠償力度
應當加大環境損害賠償力度
遏制環境污染,應當從過去單純依賴行政罰款逐步轉化到注重損害賠償,從過去僅賠償受害人直接損失到逐步地增加對生態損害的賠償,從單一的侵權損害賠償轉向多元化的救濟機制。

王利明
中國人民大學常務副校長。“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國法學會副會長,中國民法學研究會會長。系新中國第一位民法學博士。
紫金礦業污染案件,經媒體曝光之后,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紫金礦業位于福建上杭縣的紫金山銅礦濕法廠發生污水滲漏事故,9100立方米廢水外滲引發福建汀江流域污染,造成沿江上杭、永定魚類大面積死亡和水質污染。此后,被判罰三千萬,該判罰出臺后紫金礦業的股票不跌反升,大大出乎人們的預料。這一事件表明,單純依靠行政罰款或罰金的方式來處理環境問題,達不到懲罰違法行為、促使企業改過的目的。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我國的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也為此付出了沉重的環境污染代價。如何采取有效措施,保護環境,治理污染,是全社會普遍關注的熱點問題。
環境污染的問題難以有效解決,在很大程度是因為違法成本過低。紫金礦業不過是眾多的環境治理困局中一例而已,系列污染事故的產生,都因處罰數額過低而廣受詬病。
對于環境污染的治理,首先應當看到的是,過多地依賴行政手段來解決這一問題,已經被實踐證明是行不通的。一方面,行政處罰并非以損害后果作為確定處罰數額的依據,甚至某些處罰與損害后果并無直接的關聯。行政機關也會受其能力所限,難以對有關損害后果進行準確認定。因此,處罰的結果大多遠遠低于污染所造成的實際損失。另一方面,行政處罰的制度并不能夠為環境污染受害人提供充分的保障。實踐中,通過行政處罰所獲得的款項是國有財產,應上交國庫,而環境污染的受害人并沒有因此獲得補償。這既不利于保護受害人,且不能通過利益機制,有效地調動受害人主張權利的積極性。環境保護不僅是政府的責任,公眾亦有責任。國外在環保方面特別強調“公共參與”,而“公共參與”的一個重要機制就是通過損害賠償來鼓勵受害人的積極參與。實際上政府的公共行政資源是有限的,僅僅依靠政府來監管很難擔當起環境保護的重任。
其次,在環境污染案件訴訟到法院后,損害賠償認定機制的不足,是造成目前環境違法成本低的另一個原因。應當承認,“損害賠償”相對于行政處罰具有明顯的優越性。從公共參與的層面來看,受害人的請求可以對潛在的環境污染主體形成一種壓力,且通過這種方式能夠對受害人提供必要的救濟,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維護受害人的權益。但問題在于,是否損害僅僅限于直接受害人的損失?就環境污染而言,其損害包括以下兩個部分:一是直接受害人的損失,如漁民魚蝦死亡的損害,周邊居民飲水困難的損害等;二是生態環境的破壞,通常土地或河流在受到污染后,常常需要幾十年、上百年的時間才能恢復,且治理的費用往往數額巨大。
環境污染損害賠償應當加大力度,以解決賠償力度不足的問題。賠償應當與損害相一致,使受害人恢復到損害發生前的狀態,這是千百年來自然法上的通行準則,違法者應該對所造成的損害后果負責,將其生產成本內部化,這既是效率的要求,也符合公平正義的原則。環境污染賠償案件中僅僅只是考慮直接受害人的損失,也并未將生態環境損害的賠償計算進去,這種損害主要就是對生態的治理和恢復的費用。 生態環境本身是一種公共利益,破壞生態環境其實損害的是公共利益。對這種公害,即便受害人沒有提出賠償的請求,國家有關機關也應當介入。必要時,國家可以作為侵權受害人而向侵害人提出請求。
加大環境污染的賠償力度,確實有可能會遇到企業因無力承擔而破產的困境。因此,這就需要通過建立環境保險機制,來預防此種風險。由于環境污染常常構成大規模侵權,即造成眾多的直接受害人的損害,在保險之外,還應建立社會救助機制,向受害人提供有效的救濟。此外,環境污染侵害的不僅僅是私權,還侵害了公共利益。在實踐中確實有一些污染受害人可能基于各種原因并沒有主動提起訴訟,在這種情況下可以通過公益訴訟來追究污染行為人的責任。公益訴訟的提起人可以是有關環保部門、檢察機關,也可以是有關環境保護組織和團體。公益訴訟的設立也將會為遏制環境污染提供一個有力的保障。
紫金礦業污染案件給我們帶來的啟示是,我們應當從過去單純依賴行政罰款逐步轉化到注重損害賠償,從過去僅賠償受害人直接損失到逐步地增加對生態損害的賠償,從單一的侵權損害賠償轉向多元化的救濟機制,建立侵權賠償、責任保險、社會救助基金相互協調、互為補充的多元化救濟機制,多管齊下,以綜合、有力的手段形成強有力的環境保護體制。
(責任編輯/吳文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