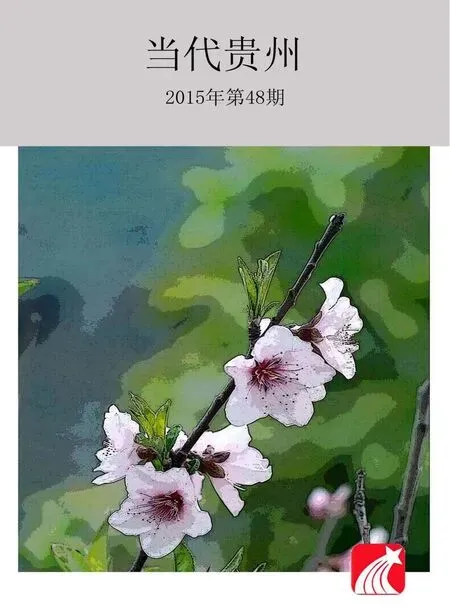東拜王城祭
文丨余未人
山國文境
東拜王城祭
文丨余未人
紫云格凸河景區是上蒼格外垂愛的一處景觀,峭壁深潭、奇山洞穴、綠蔭覆蓋。其中,觀音山一側的苗寨是苗族古代英雄亞魯王之子歐地聶的后裔繁衍生息之地,經過數百年歲月的淘洗,這里古風猶存。在人生的重大節點,歐地聶的后裔七十多戶人,至今依然在傳統儀式中度過。傳統的力量在這里強悍無比絕非偶然,因為這里曾經是“東拜王城”,一個易守難攻的古戰場。灰白色的石塊已被風雨磨蝕了棱角,層層疊疊地堆砌著城基,歷史的訊息從這里隱隱析出。它究竟是哪朝哪代的遺跡?有多古老?據貴州省考古所的專家考證,從石縫間的粘合劑來分析,大約是明代。
東拜王城被群山環抱,我向村民們詢問周邊的山名。可他們對這些天天眼見的山,卻很難想起它的名稱,一人想起來了,他人又不同意,各說不一。原來,因為苗族村民們日常生活都用苗語,所以對這些漢語地名、山名的記憶漸漸淡忘了。我問了好幾位老人才算“考證”出來。這里有虎頭山、觀音山、營上、羊角屯。這些漢語名稱是明代軍方屯兵的遺痕。原來,屯兵在這條進出麻山的要道上,就是把守進出麻山的大門啊。
這里曾有一段漫長的沒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戰敗者拋盔棄甲隱遁于麻山深處,而勝利者也沒能守在這里生根開花。對古戰場的憑吊讓人黯然。戰爭曾讓這里刀光劍影殺聲震天,也讓這里“鳥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
當時光流逝,經歷了數代人的循環往復之后,勇敢者又把目光瞄向了這里。他們拖家帶口從麻山腹地遷徙而來,最先定居的是王家。他們在王城的遺址上建家園,砍來竹子編織竹篾墻,割來芭茅草蓋上屋頂,雞鴨牲畜讓這里回蕩著鮮活的生命氣息。他們接續了歷史,東拜王城生機日漸恢復。先祖歐地聶王子早已回歸祖奶奶的天外世界,然而王氣卻在這里氤氳綿延,在寶目一次次的法事中蘇醒,在東郎一次次的唱誦中恢復生機。是這份執著的信仰讓他們堅強地生存下來。

東拜王城一景(白文浩/攝)
20世紀40年代,麻山的楊大伯從麻山腹地出來闖蕩謀生,為東拜王城下的一戶雇主割馬草。他來到王城,眼前是一片斷壁殘垣,而四周林木葳蕤,虎狼出沒,這強悍的、英雄的氣息就是東拜王城之魂。清澈的山泉在王城活潑流淌。它是苗人的生命之泉,有了它,就能夠養活苗人。雇主答應讓楊大伯在東拜王城遺址造屋安身。這里的生存條件與貧瘠的麻山不可同日而語。人往高處走,苗人就是一個歷經遷徙、四海為家的民族。1948年,楊大伯率領兩手空空、家徒四壁的親友們告別故園,從麻山腹地風塵仆仆地遷來,在東拜王城安家了。20世紀50年代,梁家又來了。
當年東拜王城只有羊腸小道通往山下,山里人在這里過著封閉的、難以溫飽卻自給自足的日子。麻山苗人們來到這個被視為陰冷、肅殺的王城遺址安家,正是一種富有遠見卓識的目光使然。
2013年11月,楊正江等苗人中的有識之士在東拜王城倡議了一場養育心信、祭祀先祖的祭儀。這個倡議一呼百應,王城的苗人們說做就做,當天便開始為期十多天的素食。
到了為先祖下葬安靈的12月4日,四鄉八寨的苗人們蜂擁而至,一整套儀式有條不紊地進行著,一幅巨大的“芒就”(族徽)在風中獵獵飄揚,沒有喧嘩,沒有擁擠,苗人們心無旁騖,十分靜穆,這是一種精神的指引。連那些“無冕之王”、攝影“發燒友”,也不得不遵照祭祀的禮規用上了長鏡頭,不敢逾越雷池前往葬儀的核心區域。
人們關注的焦點是砍馬儀式。那是一匹英俊瀟灑的馬,它正在麥田里悠悠吃草。然后被牽到臨時辟出的砍馬場上,接受婦女們的膜拜、喂谷穗,領受砍馬師的三叩九拜。最后在那里完成自己的神圣使命。(作者系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顧問、貴州省文史館館員 責任編輯/姚源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