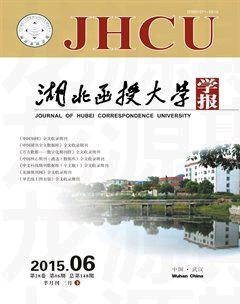淺析《挪威的森林》中的生死鏈條及其死亡原因
李瑞華
[摘要]《挪威的森林》由一系列依靠死亡而連接成的生死鏈條構筑了整篇小說。死亡是敘事線索、敘事動力以及敘事內容,小說的死亡觀既深受存在主義的影響也有日本傳統文化的影子,不僅可以看作是村上春樹對日本傳統文化的傳承,更是他對美的更深層次理解以及對人生的深刻思考。
[關鍵詞]《挪威的森林》;生死鏈條;死亡原因
[中圖分類號]1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5918(2015)06-0180-02
“敘事性”是這部小說與其他文體區分開的顯著特征。在看似散漫的生活敘事背后,也具有明顯的敘事脈絡和清晰的敘事內容。格非曾說過,所謂的敘事小說是“由時間上的延續性與事件前后的因果關系構成”的。在《挪威的森林》中,“時間上的延續性”便是依靠死亡而連接成的生死鏈條,一系列的死亡事件以及由此而引發的生死悖論中的生存體驗則構成了“事件前后的因果關系”。在《挪威的森林》中,死亡是敘事線索、敘事動力以及敘事內容,我們可以將其視作“一連串的死亡故事”或“由死亡引發的故事”。
一、生死鏈條
死亡事件不斷出現在整部小說中,從木月的死開始,到直子的死亡為結束,中間一連串的死亡事件將人們束縛于生死困境中。直子的救贖之路、渡邊在生與死之間的猶豫與徘徊、初美平靜地自殺等,都不斷推動著小說的發展。木月的死亡是一個開端,它深刻、用力地撕開了直子內心脆弱的傷口,讓她難以去直接面對現實所發生的一切,只能逃到阿美寮。同時也將渡邊往陰間拖拽,使其長時間以來難以釋懷。木月與直子的先后死亡是渡邊對生死領悟的來源,而作為木月與直子通向現實世界的橋梁,渡邊在直子去世后更是悲傷到不能自已,深陷生死的漩渦之中。可以說,每個小說人物的內心都對死亡懷揣著特殊的體驗與感受,圍繞著死亡不斷在現實生活中痛苦掙扎,而這種生與死的矛盾沖突則構成了《挪威的森林》的主要內容,不斷推進著整個小說的敘事發展與節奏。
這些依靠死亡而連結成的生死鏈條在小說中縱橫交錯形成了一個完整的結構網。每條生死鏈是否存在依賴于它能否維持生死平衡,這一過程則左右著小說的敘事發展。小說中有這樣幾條生死鏈:木月一渡邊一直子、直子一渡邊一綠子、永澤一渡邊一初美。
木月一渡邊一直子和直子一渡邊一綠子這兩條生死鏈,分別是小說中最主要的和最為完整的,可以說,木月的死是小說中重要的關鍵點之一,他的死既使直子無法自拔,致其崩潰而自殺,又模糊了渡邊的生死界限的認識,更使其游離于生死兩端。木月的自殺使木月一渡邊一直子這一鏈條中斷,木月與直子都是死亡的象征,那么這兩條生死鏈可以合為一條。其中,木月和直子是陰界的代表,綠子是陽界的代表,而渡邊則掙扎、困惑和徘徊在陰陽兩界,正如直子對渡邊所說的“對我們來說……你的意義就像根鏈條,把我們同外部世界聯結起來的鏈條。”渡邊本來希望將直子拉回到陽界,卻一步步地欲被處于極度自我封閉狀態的直子引向陰界,以至于連現實生活中活潑可愛的綠子都無法輕易地將其拉回到現實世界中,“你總是蜷縮在你自己的世界里,而我卻一個勁‘咚咚敲門,一個勁兒叫你。于是你悄悄抬一下眼皮,又即刻恢復到原狀。”木月和直子的先后自殺曾一度使渡邊陷入死亡的陷阱中不能自已,此時綠子的出現則讓渡邊恢復了不少生存的動力。而且后來渡邊得知直子已死,一個月的旅行也并未緩解直子的死帶給他的打擊,返回東京后他意識到一個事實“直子死了,綠子剩下。直子已化為白灰,綠子作為活生生的人存留下來。”終于他撥通了綠子的電話,通過綠子離開了死亡的邊緣,得到拯救。
如果說木月一直子一渡邊一綠子是小說的主要敘事線索的話,那么,永澤一渡邊一初美則是小說的輔助線索。永澤就像綠子一樣作為陽界的象征,而初美則如同直子,作為陰界的象征,渡邊無疑又處在中間。但是,由于初美割腕自殺,而且在初美死后渡邊斷絕了同永澤的聯系,因此這條生死鏈失去了平衡,被迫中斷。
小說中的生死鏈并不是一條一條孤立的狀態,而是有許多蔓延和延伸,豐富和推進著小說的發展。就像渡邊,他一個人不但與木月、直子、綠子有聯系,還與永澤和初美聯系著。還有直子,她聯系著自己的姐姐和叔叔的死亡。綠子則經受著父母的離世。它們共同豐富著生死鏈的脈絡和小說的敘事。但是在生死鏈中,一旦有一方走向死亡,那么整條生死鏈將失衡而不復存在。隨著木月和直子的先后死去,渡邊終于偏向了綠子,同時使這條生死鏈失去了平衡,曾長期迷失自我的渡邊此時卻更加失重,想開始新的生活卻在撥通綠子電話的一剎那茫然失措。這些生死鏈生動的表現了現代個體所要面臨的理想與現實的沖突。
二、死亡原因
《挪威的森林》中對死亡的偏愛并不是村上春樹一時心血來潮,也并非他獨樹一幟的風格。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存在主義生死觀
村上春樹作為戰后成長起來的一代作家,雖然也受到日本傳統文化的浸染,但是由于日本對西方文化的大力引進,也深受歐美文化的影響。村上春樹的西化傾向是其創作的主流。純正日本傳統文學作品能在世界范圍內得到如此多的青睞和共鳴是不可想象的。林少華認為村上春樹的作品特色之一,是“他往往用非日本的視角,即西化的視角來審視,把握和感受日本社會的種種現象”。這與他的成長背景以及個人興趣有很大的關系。從《挪威的森林》中可以看出,作者喜歡披頭士,喜歡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蓋茨比》等。他喜歡的是西方文化而不是日本傳統文化,他的小說更多的體現的是西方文化的影響,而不是延續日本的文學傳統,相反,二者之間是一種斷裂。他大跨度的想象、簡潔明快的語言、歐化的句子以及孤獨自我的把玩都證明他對日本傳統文學的反叛,而這種反叛卻正好迎合了20世紀以來的歐美文學潮流。作為小說的核心生死觀念便在這一潮流中與盛行的存在主義思潮接軌了。
由此可以看出,《挪威的森林》中的生死觀并非僅僅是日本傳統生死觀的延續,更是存在主義生死觀的表現,村上春樹所做的是將這兩者進行了融合,將其打造成了一種具有一定普適性的青年所共同的生死體驗,這也與存在主義人本、人道的人類普適性主題不謀而合。endprint
(二)日本傳統生死觀的滲透
死亡是文藝作品永恒的主題。日本文學史中也早有記載。公元905年左右編訂的《古今集》“通過對櫻花的歌群的吟誦體現了由畏懼死亡、逃避死亡向親近死亡、贊美死亡的生死觀的轉換。”稍晚出現的《源氏物語》(約公元1000年)中流露出來的“物哀”格調更是成為了日本文學的優良傳統,被川端康成等一批作家發揚光大。加上日本文學慣有的細膩語言技巧,日本文學以其對“死如秋葉之靜美”的描畫而成為世界文壇中一道明艷的風景。
日本民族之所以形成這種獨特的生死觀念,以下兩個因素是不可或缺的。首先,日本是個四面環海的島國。大海的瞬息萬變,加上日本多火山、多地震,雪災臺風頻繁,相對惡劣的環境使日本人自古就形成了生命易逝、孤獨封閉的心理。無所憑依的形勢、自然災害的摧殘,正因為他們知道一切都是轉瞬即逝的,所以日本人特別鐘情于瞬息消逝的晨露、紅葉和櫻花。這種情緒逐漸演化成為對破滅、對死亡的崇拜。所謂“花當櫻花,人當武士”,櫻花花開即盛,花期又短,盛開后隨即隨風而逝,始終保持美的形態。武士的宗旨是“忠誠、信義、廉恥、尚武、名譽”,他們一直用生命去捍衛武士的思想精髓,一旦不能做到或受到屈辱,他們會毅然決然的拔出刀劍割向肚腹。肉體雖然死亡,但精神不死,依然會得到贊頌。這種鐵血的做法被認為是日本的氣節,備受推崇。其次,佛教中人生虛幻無常觀與日本的“物哀”“傷感”剛好契合,更是堅定了日本對死亡的贊美。日本人不相信超越的虛無縹緲的神,而是相信人死可以復活,相信世道輪回之說。就像《挪威的森林》中渡邊說的“死并非生的對立面,而作為生的一部分永存。”死亡是高尚的藝術,死亡是美的最高境界。人物的死并不是凄慘的,雖然生命結束,但生活的恐懼、煩惱與孤寂也隨之消失了,是一種解脫,是在日本傳統生死觀影響下的追求美的方式。
三、結語
作者通過《挪威的森林》中依靠死亡而連接成的生死鏈條,向人們展示了在對待個體面對死亡的絕望和恐懼時,要在接受死亡是永恒的前提之下,淡然地接受死亡,不懼怕死亡,并且以一種更堅強的方式繼續活在這個世界上,無論世界多么灰暗,心靈多么孤獨痛苦,都要從悲哀中掙脫出來,繼續活下去。就像林少華說《挪威的森林》“既是死者的安魂曲,又是青春的墓志銘。死給生者留下只有通過死才能學得和體會的東西。”
參考文獻:
[1]格非.小說敘事研究[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37.
[2]村上春樹.挪威的森林[M].上海:上海譯出版社,2007.
[3]尤海燕.古代日本人生死觀的轉換及“飛花落葉”美意識的形成[J].外國文學研究,1999(3):37.
[4]張文初.文學:死亡的出場[J].湘潭師范學院學報,1997(4):31.
[5]林少華.為了靈魂的自由:村上春樹的文學世界[M].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10.
[6]徐崇溫.存在主義哲學[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665-669.
[7]陸揚.死亡美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8]杰·魯賓.傾聽村上春樹:村上春樹的藝術世界[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