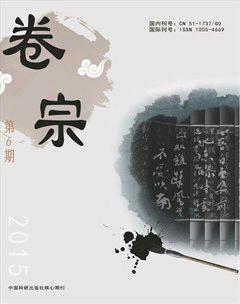去個性化研究現狀淺析
周思雨?鄧雙喜?尹潔?曹永歡?鄧萍
摘 要:去個性化作為社會心理學的一個研究領域,在國內的研究相對較少。本文結合相關文獻和空集調研,對去個性化產生的原因、歷史發展及相關實驗進行梳理和分析,并就去個性化的積極作用及去個性化的未來研究方向進行探討。
關鍵詞:去個性化;研究現狀
(基金項目:大學生研究性學習與創新性計劃項目< 湘教通[2014]248號— 381>)
很多時候,當個體面對一件事的時候,他可能是清醒而冷靜的,但一群人就很容易變成烏合之眾。他們盲目并且興奮,任由別有用心的人操縱和引導整個事件的節奏和方向,在自己并沒有意識的情況下,說出平時不敢說的話或做出自己平時不敢做的事。因此,去個性化被認為是群體中個人喪失其同一性和責任感的一種現象,導致個人做出在正常單獨條件下不會做的事情。[1]社會心理學和社會學家們都有研究分析去個性化,但分析層次不同。社會心理學家分析層次主要針對個體置身于社會環境中的情況,他們強調內部心理過程的作用。而社會學家更關注于廣泛的社會、 經濟、 政治和歷史因素影響特定的社會中的事件。
1 去個性化產生的原因
很多心理學家就去個性化產生的原因進行了大量的推測與研究,其中Zimbardo認為個體去個性化的產生與這些因素有關:匿名性,個體責任喪失,喚醒,感覺超負荷,新的或無組織情境,行為卷入以及服用改變意識的物質[2],其他心理學家在解釋去個性化的原因時認為主要來自前面兩個方面。而筆者認為去個性化的產生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1.1 匿名的背景
根據弗洛伊德自我結構論的觀點,個體在匿名狀態下,超我的作用是非常小的,自我也相應地喪失了強而有力的約束力,本我則表現得非常積極。當個體處在群體中,或者虛擬的網絡中就會使人難以辨認個體的真實身份,外人不知“廬山真面目”,個體就會毫無顧忌地違反社會道德和傳統習俗,甚至法律法規。這樣個體的獨特性喪失,個體的自我糾正能力降低。例如,人們喜歡用各種社交軟件和陌生人談天說地,他們一點都不擔心是否會有人認出自己,這就是利用在網絡上的匿名性的原因,釋放出本我,言論絕對自由。
1.2 責任分散的心態
一個人單獨行動時,通常是責無旁貸地承擔完全責任。但在群體行為中,反社會行為的責任就落在了群體身上,個人可以推卸責任。同時個人也覺得“罰不責眾”,這樣,個人的責任就分散了。在群體中,個體受到的壓力減少,認為自己不會受到懲罰,就不會有內疚感,從而更加放縱自己的行為。責任分散的心態加上匿名的背景,使得一些缺乏社會經驗的個體遺忘責任感,做出一些不當的事情來。例如,應急車道是發生交通事故時救援的生命線。社會車輛不得在非緊急情況下在應急車道行駛或者停車,這是所有駕駛員都應知道的交通法規。但現在很多駕乘人員無視這一點,恐怕很大原因在于心存僥幸——大家都停,不可能全部處罰。
1.3 自我意識的缺失
筆者認為,去個性化行為發生的決定因素應該是個體意識水平的高低。由Freud的“本我”理論得知,本我不知道“對”與“錯”,對現實世界的正確與錯誤全無所聞,不會抑制自己的行為,他只是追求心滿意足,按照“快樂原則”行事。本我的這種特性與現實社會的矛盾,導致本我在現實社會總是被抑制在無意識層面,而個體也只能遵照自我的“現實原則”為本我服務。但到了群體中,與本我相矛盾的現實社會不復存在,個體的行為更容易受到他人的影響。而當個體意識水平降低時,那么個體在社會中受到誘惑的抵抗力將大大降低,因此才更容易受到他人的影響,只有當一個人能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的角色和社會責任,他才能做出正確的自我引導。
2 去個性化研究的發展
去個性化起源于歐洲社會學,最早由法國社會學家Gustave Le Bon在研究群體行為時發現。在他撰寫的專著《烏合之眾》一書中表示,在群體中,每種感情和行動都具有傳染性,其程度足以使個人隨時準備為集體利益犧牲其個人利益。這是一種與他的天性極為對立的趨向,若不是成為群體的一員,他很少具備這樣的能力。[3]
1952年,Festinger等人研究了Le Bon的觀點,創造了一個新術語——去個性化,它是指群體中的個體有時候會失去對自己行為的責任感,使自身自我控制系統的作用減弱甚至喪失,從而做出平時不敢做的反社會行為。[4]在某種程度上,Festinger等人同意Le Bon的群體行為理論,他們認為個性確實被淹沒在群體之中會導致他們的責任感減弱。但是他們強調把去個性化從群體理論中區分出來,他們認為個體在群體中個性的喪失是因為被群體思維所取代,去個性化導致喪失了對內部或道德約束的控制。
1969年,P.G.Zimbardo驗證了去個性化的影響因素,如匿名和責任的分散[5]。同時,Zimbardo沒有限制于應用在群體環境中;他也應用去個性化理論在“自殺、謀殺和人際間敵意”之中。
然而,Diener對Zimbardo的去個性化假說表示不滿,他認為論據是錯誤的。1980年,他主張注意個人價值觀念通過自我意識提高自我調節的能力。在群體環境中,個體會丟失理性計劃自己行為的能力,更加強受群體暗示的影響而行動。[6]因此,根據Diener的假說,自我意識的減弱是“去個性化的明顯特征”。他打算嚴格關注匿名性作為去個性化的主要因素創造了一種經驗主義的障礙,需要在主題上改變經驗主義調查的方向。
之后Russell Spears和Martin Lea(1995)創建了去個性化效應的社會認同模型,Postmes和Spears(1998)對有關去個性化的60項研究進行了元分析。[7]這些都為去個性化這一理論提供了依據和證明。
3 去個性化的相關實驗
3.1 去個性化的實驗
1952年,Festinger、A. Pepitone和T. Newcomb進行了去個性化的實驗。[8]被試者均為男大學生,先將他們分為兩組,一組為可辨組,被試者被貼上自己名字的標簽,在明亮的房間進行實驗。一組為去個性組,被試者要求穿長袍、戴面具,只能露出眼睛和鼻子,彼此都不知道對方的名字和樣子,并在昏暗的房間進行實驗。實驗開始后,實驗者要求兩組被試者在他們身處的環境中議論自己父母的缺點與不足。
結果顯示,去個性組的被試者們大多都會肆無忌憚地數落自己父母的缺點,充分表現了對自己父母的不滿情緒。實驗結束后,所有被試者填寫調查問卷,以了解被試者對再次參加議論的喜歡程度。數據表明,去個性化組比可辨組對群體成員更加富有吸引力,即男大學生們更傾向于在去個性化組里再次議論自己父母的缺點。
這個實驗體現了去個性化其中的一個特點——匿名性。去個性化組和可辨組對比可知,男大學生在匿名情境中更加無所顧忌地說出自己的真實想法,自身情緒爆發也在特定的環境中暴露得更加徹底。因為他們處在去個性化的狀態下,認為沒人知道他們的身份,從而不怕人知道自己內心的真實的想法。就像課堂上眾人起哄時的心態,他們認為沒人會知道自己也參與在其中,不會被懲罰或被自身道德所束縛。進一步擴大到社會中,去個性化可能會使個體毫無顧忌地與社會規則與道德習俗相悖,做出自身一個人平時決不會做出的行為。
3.2 Zimbard 的女大學生電擊實驗
1969年,心理學家Zimbard做了一個電擊實驗[9]。被試者是一些女大學生,他將女大學生分為兩組。第一組被Zimbard稱為“去個性化”組,被試者都穿上帶頭罩的袍子,只露出眼睛,彼此都不知道對方,實驗者也不會叫她們的名字,整個實驗在昏暗的條件下進行。第二組被Zimbard稱為“個性化”組,被試者都穿平常的衣服,每個人胸口都掛了一張印有她們名字的牌子,實驗在明亮的房間進行,彼此可以看清對方,實驗者會在實驗中叫對方的名字。實驗開始,實驗者讓兩組被試者電擊打扮成女大學生的Zimbard的助手,被試者被告知不需要負任何道德上的責任,只是為了實驗需要,實際上助手并不會被電擊。兩組被試者均可以在鏡子中看到那個被電擊的人。當被試者按下電擊按鈕時,助手便大聲哭喊,讓被試者認為是真的被電擊了,很痛苦。
結果顯示,去個性化組被試者比個性化組按電鈕的次數多達將近兩倍,而且每一次按下按鈕的持續時間也比較長。
從這個實驗中我們可以了解到,當個人和其他人在同一種集體中時,他就會認為集體行動時自身責任是模糊而分散,認為每一個參與者都會有責任,細化每個人的責任后會變得很小,甚至于近乎沒有,因此任何一個個體都不必為集體行為而承擔罪責,他便會減少自身的心理壓力與內疚感,并覺得可能不會被懲罰,從而他的言語和行為會變得更加放肆。甚至有的成員會覺得他們的行為是被允許的或者在道德上是正確的,因為集體作為一個總體參加了這一行動。
3.3 Diener的萬圣節糖果實驗
1976年,Diener進行了一個萬圣節糖果實驗。在研究中,研究人員在客廳的桌子上放了一碗糖果,一名觀察員藏起來記錄孩子們“不給糖果就搗蛋行為”。在一種情況下,一名實驗者詢問兒童一些表明他們身份的問題,比如:他們住哪里,父母是誰,叫什么名字等等。在另外一種情況下,兒童是完全匿名的。觀察員也記錄兒童是單獨一人還是在群組中。在每一組情境中,實驗者會邀請兒童進房間,然后說自己會去廚房所以會離開這個房間,并告知每一個孩子只能拿一塊糖果。
結果,匿名群組的兒童比其他情況下的兒童多拿了遠不止一塊的糖果。在60%的情況下,匿名群組的兒童多拿了糖果,有時甚至拿了整碗的糖果。匿名單獨組和非匿名群組的情況并列第二,20%的兒童多拿了不止一塊糖果。最少的就是非匿名單獨組的兒童,只有10%的兒童多拿了糖果。
在糖果實驗中我們可以看到,處于匿名組和在群組中的孩子更容易多拿糖果,這些孩子都缺乏對自我的約束,即便實驗者只允許他拿一塊糖果,但他也會有“沒人知道自己是誰”、“身處集體中多拿了一塊糖果不會被發現的”、“他們都多拿了我也可以多拿的”的這種心理。從孩子們多拿糖果的這種行為來看,是遵循了Freud的“本我”理論。很多孩子們還處于一種對現實世界的道德觀沒有辨別性的年齡,也就不會抑制自己的行為,只會按照“快樂原則”行動——多拿糖果。即便少數孩子會覺得違背大人的話會被懲罰,但當孩子們到了群體中,那種自責便會不復存在,也更加容易被身邊多拿糖果的孩子的影響,認為別人也多拿了糖果那我也可以多拿,從而做出平時自己不會多拿糖果的行為。
4 去個性化的積極作用的分析與利用
從一系列去個性化的相關研究我們得知,去個性化這一心理學現象有著一定的消極影響。但我們要善于辯證地分析看待,既要克服其消極的一面,也要挖掘出其積極的一面。
4.1 促進自我提升
在現實社會中,人們總會受到個人因素和社會因素的影響而難以重塑自我、自我提升。假如你是一個內向、不敢在眾人前發言的人,那么你可以多參加有意義的學校社團活動,在群體中你會發現原來自己也是一個開朗活潑的人,從而能找到自信心,逐漸在活動中提升自我,最后能在眾人面前從容的發言,說出自己的見解,成為一個優秀的領導者。而當你是群體的領導者時,在舉行集體活動之前就必須做好安排,不能讓別有用心的人利用活動造成混亂與不安。在活動中,作為領導者也要臨危不亂,始終要保持清醒的頭腦和較高的工作質量,不能被去個性化的特點所迷惑,從而喪失自己的立場。
4.2 增強集體凝聚力
團結就是力量在當今社會依然是不變的真理,韋伯斯特也曾說過:“人們在一起可以做出單獨一個人所不能做出的事業;智慧+雙手+力量結合在一起,幾乎是萬能的。”因此,在集體中每個人的個性被隱藏,從而顯示去個性化的狀態。例如,在進行拔河比賽時,每個人都同時用力往同一個方向使勁,這個時候每個人都處于一個去個性化的狀態中,集體的利益為大,人們都會為一個相同的目標而努力,從而忽略自身,服從集體。因此,去個性化有利于增強集體的凝聚力,有利于整個團隊的高效運行,有利于社會的蓬勃發展。
4.3 推動網絡助人行為
現實社會與網絡社會相對比,我們會發現現實生活中很少人會有助人行為,因為生活中存在著一種“旁觀者效應”。而網絡上卻不同,我們時常可以在網絡上看到正能量的傳遞,人們在匿名的情境下更容易發生助人行為。在網絡的情境下使助人者產生去個性化,從而更能主動幫助他人。他們會在網絡上給別人提供各種幫助,各抒己見,處于網絡中的人們會表現出強烈的去個性化狀態。因此,去個性化中的匿名性有利于推動網絡的助人行為。我們可以有效的利用去個性化的特點,將網絡助人行為進一步推向現實社會,這樣更加有利于社會的發展與進步。
5 對未來國內研究的展望
結合去個性化的相關文獻的分析與總結,發現國外有大量值得我們借鑒與參考的資料,除了去個性化的定義和原因、影響分析外,還包括去個性化的實驗、模型等。但目前國內對去個性化這一概念的關注程度較少,就目前國內的相關研究而言,其研究方向僅局限于學生、網絡等方面。對于現實社會中去個性化現象的研究相對比較少,分析尚為粗淺,同時對去個性化原因方面的研究也處于停滯狀態,沒有新的發展。當前社會背景之下的去個性化現象還是各式各樣,所以需要研究者重新理解去個性化現象的心理機制,探究去個性化行為的表現形式,使得未來的研究,更多聚焦于對去個性化深入的實證研究。為了豐富去個性化的心理機制理論,將去個性化更加本土化,為了揭示中國現代社會文化背景,在個體與群體關系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參考依據。
參考文獻
[1]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中國大百科全書(心理學卷)[M].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2,4.
[2]蘭玉娟,佐斌.去個性化效應的社會認同模型[J].心理科學進展,2009.
[3]Gustave Le Bon.烏合之眾[M].中央編譯出版社,2014,1.
[4]侯玉波.社會心理學[M].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7.
[5]Zimbardo P. The human Choice:Indi Viduation,Reason,and Order Versus Deindividuation,Impulse,and Chaos[A].In W.J Amold,&D.Levine,Nebraka Symposium on Motivation[R].1969.
[6]Postmes, T. & Spears, R. (1998). Deindividuation and antinormative behavior: A meta-analysis. Psychological Buttetin, 123, 238-259.
[7]王兆芬,劉海剛.“去個性化”在社交困難學生成長中的作用探索[J].中學生心理健康教育,2011,6.
[8]Festinger, L., Pepitone, A., &; Newcomb, T. (1952). Some consequences of de-individuation in a group. Th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47(2, Suppl), 382-389.
[9]白玉萍.破譯心靈密碼——經典心理實驗啟示[M].北京:中國林業出版,2004,6.
作者簡介
周思雨(1994—),女,湖南長沙人,衡陽師范學院南岳學院2012級應用心理學專業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