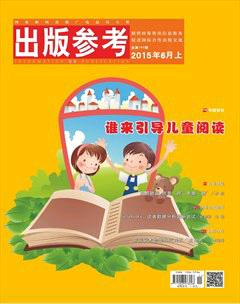看得見風景的地圖
余青
考古學家認為在人類文明的發展過程中,地圖存在于文字之先。我們可以從人類自身發展的歷史中找到地圖的印跡,追溯古往今來的繪圖家們和探險家們的精彩探險故事。地圖曾經是精美的藝術和昂貴的奢侈品。幾千年來,人類以非常多元的模式描繪和展現和認知著世界,地圖既是國家與權力的象征,也是一個看得見風景的世界和智慧寶庫。
商務印書館最近出版的《十七世紀歐洲與晚明地圖交流》一書為讀者帶來了一個看待地圖的全新方式。初看書名,讓人覺得這是一部關于人文地理方面的著作,不過翻卷而閱,讀者可以發現,嚴謹的書名下不僅蘊含著對藝術史與中西交流的思考與延伸,還蘊含著一個藝術和科學的世界。本書作者采用了放大的觀察方式,把地圖史、中西交流和視覺圖像交錯在一起,并構建出一個立體的人文主義坐標,試圖在縱橫脈絡之間尋找某種不易察覺的內在聯系。
本書以科學、交流與藝術三部曲的形式,將有關地圖的精彩故事貫穿在十七世紀中西交流的宏大歷史背景之中,不僅以詳實的文獻資料敘述了地圖歷史發展的“長時段”,還重點陳述了歐洲地圖在晚明時期與中國交流的“短時段”。它旨在從藝術史的角度出發,以地圖圖像作為視覺、藝術與交流的載體,論述地圖圖像的發展歷程以及在晚明時期與中國的交流活動。書中不僅告訴讀者歐洲與中國古代地圖的淵源與演變,它們的科學基礎、藝術表現和對社會文化的影響與互動,還談到了文藝復興至巴洛克時期歐洲的制圖家作品中所呈現的科學與藝術之間固有的內在聯系。
在地圖的演進過程中,科學無疑是至關重要的。該書的第一部《科學》論述了地圖發展的歷史。對十七世紀的制圖來說,科學與藝術是兩股積極的力量。耶穌會士初到中國時,正是憑借科學之力才打開傳教的局面,這種情景在晚明的地圖繪制中再次上演。中國與歐洲地圖交流恰好始于這一時期,耶穌會士在傳教時意外發現晚明士人熱衷于了解歐洲的《世界地圖》。傳教士們試圖學習用中國地圖的繪制方法來繪制世界地圖,而中國的學者們自此也將目光更多地投向域外的廣闊世界。他們在自己的著作中將這些西方地圖摹刻下來,在其間留下了中西交流的印記。在第二部《交流》中,作者以微觀的視野詳細敘述了耶穌會傳教士先后來華與地圖的故事。作為增進天主教信仰和傳播教義的主要載體,各類科學圖籍從西方傳入并流行于明中后期,這些典籍涉及天文、地理、植物、科技活動及歷史風俗等,十分多樣和深入,且此類文獻通常圖文并茂,以圖證教,既反映了歐洲科技發展,也記錄了耶穌會士來華后的所見所聞。晚明時期人們可以接觸到多元的文化、知識和習俗。當時歐洲的耶穌會士們接受過系統的學術和科學訓練,掌握了諸多科學技能,得以在晚明時期的中國施展才華,這也與晚明社會的文化氛圍極為相宜。書中著墨最重的在于第三部《藝術》,這也是書中最好看的部分。
地圖的藝術風格是一個有趣且復雜的話題,但這一領域恰恰還不為人們深入了解。地圖史是否對應藝術史的發展,尤其是藝術家在多大程度上改變了地圖的圖示,這些都是需要更進一步研究的話題,對它們的探討也許會重新定義科學與藝術對人類文化的改變。例如人們只是粗略地知道畫家們,尤其是山水畫家們可能參與了古代中國地圖的繪制,但繪畫中的透視觀察和表現等因素究竟對制圖起到多大影響,由于史料的缺乏依然無法得到考證;而歐洲在這方面相對明確,從文藝復興時期到十七世紀,為數眾多的藝術家(尤其是銅版畫家)直接參與并影響著地圖繪制,歐洲地圖始終具有很強的裝飾性和繪畫表現。畫家們使地圖變得生動、立體和不落俗套,地圖也成為畫家們用來表達想象力、神話、象征與宗教影響的一個樂園。藝術家廣泛參與制圖給地圖的面貌添加了唯美的注腳,使我們在幾百年之后的今天還可以看到一個五彩斑斕的地圖世界,并帶給我們豐富的視覺享受。這里,我們不應錯過書中的一個微觀視點——有關《水紋》的論述,水紋變化是令人難以察覺的地圖繪法發生演變的微觀證據,歐洲與中國地圖的繪法異同也在地圖的水紋中得以展現。
(作者單位系商務印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