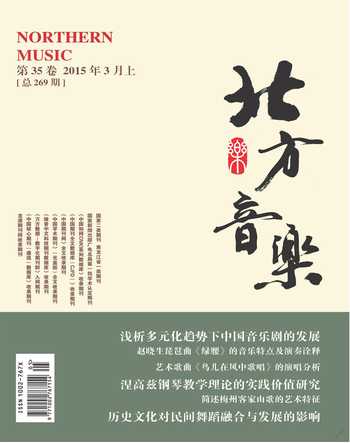歷史文化對民間舞蹈融合與發展的影響
【摘要】農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交接和融合,使甘南的“莎姆舞”流變為卓尼藏巴哇的“藏族莎姆”、岷縣的“漢族莎姆”和卓尼勺哇的“土族莎姆”。文章探析了“莎姆舞”的源起的歷史生態文化背景,指出可見的舞蹈形態動作的特征,以及隱含在舞蹈背后屬于舞蹈創造者與傳承者的歷史文化特征作為舞蹈的兩大特點,體現了舞蹈背后的歷史感、民族的堅毅性格以至人類本身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與渴望。
【關鍵詞】藏巴哇;流傳區域;民間舞蹈;莎姆舞
前言
民間舞蹈有兩個重要的特征:可見的舞蹈形態動作的特征,以及隱含在舞蹈背后屬于舞蹈創造者與傳承者的歷史文化特征。“莎姆舞”是流傳于卓尼藏巴哇一帶的藏族民間舞蹈,其來源和歷史演變已經沒有明確的歷史記載,只剩下一些民間故老相傳的口頭傳說,甚至連“莎姆舞”中的許多舞種也已失傳,原來多達三四十種舞蹈動作和唱腔之后到現在較完整流傳下來的不到十種,其保護工作已到了刻不容緩的境地。為了能更好地理解“莎姆舞”的內涵和傳承這種舞蹈,有必要去了解“莎姆舞”的歷史生態文化背景,從歷史文獻的記載中去了解這塊土地上曾發生的歷史,去感受這塊土地上曾生活人們的歡笑、淚水乃至鮮血,去領悟他們對幸福祥和的期盼,從而體會到舞蹈背后的歷史、舞者的堅毅性格以至人類本身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與渴望。只有理解舞蹈背后的所承載的民族歷史文化特征,才能對“莎姆舞”做出一脈相承地創新與延續,更好地傳承歷史文化與民族特質。
一、“莎姆舞”源起的地域地理
卓尼地處農區與牧區的過渡地帶,天然處于文化割裂帶上;同時,卓尼又處于民族走廊中重要的位置,歷史上許多民族大遷徙都經過這里,戰爭時期又是軍事戰略要地,多民族的歷史活動對該地區有著重要影響。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該地區風俗文化的形成、民族性格的鑄就與精神特質的形成,同時受中央王朝的統治政策以及該地區的實際管理者兩方面的共同影響。民族民間舞蹈作為民族地區的歷史文化、民間風俗、民族特質的重要的載體之一,其表演過程中反映的文化特點不容忽視。
(一)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的交接處
甘南自治州位于安多地區東北部,而卓尼更在甘南的東北部,直接與漢地相鄰。地理位置上,卓尼縣東與定西地區所屬岷縣、漳縣為鄰;南與迭部縣相接;西南與四川省若爾蓋縣睦鄰;西與碌曲、夏河縣境毗連;北與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康樂及定西地區渭源縣接壤;中部與臨潭縣環接,兩縣邊界參差交錯,互有兩塊“插花地”,莎姆舞的流傳地藏巴哇地區即被臨潭縣隔開。這一地區屬多民族聚集區,生活著有諸如藏族、羌族、土族、回族、漢族等諸多民族,長久以來,不同民族之間的文化傳統與風俗習慣相互影響,相互融合,卻又各具特色。
受海拔與降雨等因素的影響,自古以來卓尼在地理上天然處于農區和牧區的過渡地帶,其西北是廣闊的安多牧區,東南則是以農耕作業為主的區域,而縣境內也是從西北到東南由牧區向農區過渡,藏巴哇地區以農業經濟為主。農業的生產生活很大程度上要依賴天氣狀況,在當地冰雹等惡劣的氣候特征對農耕為主的生產生活造成了嚴重的影響,因此祈福禳災在當地的民俗中占據了重要位置。[1]
雖然當地的居民是以藏民為主,在文化區域上該地區屬于安多藏文化區,但由于地處農區和牧區的過渡地帶,與漢文化區接壤,當地的文化同時吸收了游牧文化和農耕文化的特點,并且帶有顯著的地域特色,這樣的文化特點反映在當地民眾的各種民俗社會活動中,當然這些民俗活動包括“莎姆舞”在內的民族民間舞蹈。
(二)隴西走廊
卓尼在地理上的另一個特征是處于“隴西走廊”之上[2]。費孝通先生在對甘肅地區考察之后提出了“民族走廊”這一個重要概念,指出“一定的民族或族群長期沿著一定的自然環境如河流或山脈向外遷徙或流動的路線。在這條走廊中必然保留著該民族或族群眾多的歷史與文化沉淀。對民族走廊的研究,不僅對于民族學、民族史上的許多問題的解決有所助益, 而且對于該民族當前的發展亦有現實意義。”[3]隴西走廊作為一條重要的民族走廊,是古代重要的交通要道并且具有顯著的戰略地位,歷史上多次的民族遷徙過程都經過卓尼,或是此地成為戰爭沖突的前沿區域。民族遷徙以及戰爭沖突促進了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和經濟往來,各個民族之間的語言文化、風俗習慣、民族心理、生活方式相互影響,從而讓卓尼形成了具有濃郁地域特色的民族文化。
在生產技術落后的古代,由氣候地理位置特征決定的經濟作業方式無法得到有效改變,因此其農區到牧區的過渡地帶兩千多年來未曾改變,卓尼天然處于兩類文明的邊緣地帶上;卓尼另一個地理特征——位處隴西走廊之上,交通地理位置使得它成為民族遷徙時必經之地。這兩個特征決定了當爆發軍事沖突之時,此地又成為軍事戰略要地。翻開歷史,卓尼確實一直處于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的沖突之中,兩種文明猶如齒輪緊緊咬合在一起,而卓尼在歷史的夾縫中緩緩前行,有時甚至不得不以鮮血給這塊土地留下兩種文明相融合的印記。
二、“莎姆舞”發展的地域文化
(一)歷史上卓尼統治政策對宗教的影響
處于邊緣文化地帶的區域,一方面中心文化地帶的統治者無法對該地區實行有效地長期管理,因此當地的實際的統治權利往往掌握在當地的民族首領或部落頭目的手中;另一方面,來自中心文化區的統治者通過各種方式向該地區不斷地輸出政治、文化的影響。審視歷史上的卓尼,其在和平時期總被這兩種作用力支配著。從羌漢戰爭到唐宋時期的吐蕃化,再到明朝時期的移民政策,以及清代的改土歸流都體現了這兩種作用力對當地民眾的影響。藏族文化中心則通過宗教文化來輸出自己的影響力。清代時,當地的卓尼土司借清政府的力量壯大了自己在當地的勢力,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并積極推廣藏傳佛教,打擊該地區原有的苯教勢力。經過長期的發展,當地民眾的信仰逐漸由苯教向藏傳佛教轉變。
(二)卓尼民族源流和語言
洲塔教授對甘肅藏族的族源做了這樣的描述:“甘肅藏族的族源來自共同發祥于青藏高原腹地、具有同一先祖的吐蕃人(包括軍隊和駐牧部落)與西羌各部落的結合,并吸收了部分漢人和其它民族人口的成分。”[4]卓尼境內的藏族的形成也大致如此,當地的藏族是由從衛藏地區來的吐蕃先民、以及當地的古羌人和漢人吐蕃化而形成的,
卓尼藏族語言屬漢藏語系藏緬語族藏語支,溯其族源雖多為吐蕃后裔或被同化了的土著羌民,[5]但因其長期脫離大本營而多操安多方言,并且均在其土語群中略留有原籍的方言特征。由于卓尼地處偏隅,長期脫離本民族大本營而構成其獨特的土語群和方言孤島。在卓尼東部有一部分人自稱藏巴哇,藏巴哇意為來自后藏地區的人,因此當地人使用的藏語一些詞匯仍然留有后藏地區古藏語的特點。[6]同時藏巴哇也是當地地名,也是“莎姆舞”主要的流行地區。
三、“莎姆舞”的流變
莎姆舞是以巴郎鼓為道具的一種古老的民間舞蹈,巴郎鼓為一種雙面羊皮鼓,其擊打的方式和形狀很像貨郎使用的撥郎鼓,所以又稱其為巴郎鼓舞。[7]它融鼓、舞、樂為一體,皆有宗教性和娛樂性,舞蹈是當地民眾表達對來年美好生活祝愿和祈禱風調雨順的一種表現。歷史上,“莎姆舞”流傳的區域遠比現在大得多,各地的“莎姆舞”經過長期地發展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如今在卓尼及其附近的莎姆舞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有不同的表現方式。按其流傳的區域可分為三類:卓尼藏巴哇的“藏族莎姆”、岷縣的“漢族莎姆”、卓尼勺哇的“土族莎姆”。簡單地說,“漢族莎姆”是“藏族莎姆”在漢文化影響下的變異,“土族莎姆”主要借鑒了“藏族莎姆”的舞蹈道具。
(一)“藏族莎姆”
“莎姆”在卓尼境內主要流傳于縣境東北的藏巴哇的藏族聚居區,其東西南北分別與岷縣、臨潭、渭源、漳縣接壤,它包括三個鄉,即洮硯、柏林、藏巴哇。在唐蕃戰爭之后,一部分的軍士留居此地,與當地土著羌族融合而繁衍至今,他們自稱為藏巴哇(意為后藏人)。明清以至民國時期,這一地區的藏族分別由卓尼楊土司、岷縣后土司、臨潭昝土司、會川趙土司統治。[8]
關于“莎姆”的起源,當地有一段神話故事。傳說在很久以前,連年大旱,顆粒無收。鄉民們苦于饑荒,只得殺牛宰羊,祭祀山神,乞降甘露。當他們虔誠地跪伏在山前祈禱時,山中隱隱傳出一陣鼓樂相伴的歌聲。于是他們默默記下了曲調和鼓點的大概,回去后便制作了一種能搖動發響,帶長把的雙面羊皮鼓,在村中心的場地上點上一堆篝火,即興跳起了巴郎鼓舞,將祈求的愿詞唱了出來。在他們至誠感召下,天上果然降下了甘露。從此,每年的春節之后就開始跳“莎姆舞”,正月十五日為歇日,正月十六就將巴郎鼓供起。
由于長期的戰爭、遷徙的歷史,以及宗教因素的影響,“藏族莎姆”的表演表現出了很大的深沉性,唱腔婉轉悠揚,歌詞大都是祈禱神靈的佑護以及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
(二)“漢族莎姆”
在岷縣,巴當鼓舞主要流傳于中寨鎮古莊村下轄的業力溝、根扎路、喬家溝、牦牛溝、窗兒崖、牙利山六個自然村,村民基本都是漢族。中寨鄉位于縣城北部,東接小寨鄉,北鄰卓尼縣柏林鄉,西與堡子、維新兩鄉接壤,南鄰西江鄉。在明代漢族遷入之前,該地區原本屬于少數民族聚居區,明朝初期在該地區遷來了大量的來自江南地區的移民,隨著漢民遷入的增多,在此影響下,當地的藏族也逐漸漢化,但源于藏族的巴當鼓舞卻得以流傳下來。[9]因此,在當地的“莎姆舞”表演隨處可見江南地區的漢文化元素參與其中,可以說“漢族莎姆”是“藏族莎姆”在漢文化影響下的變異。
岷縣的“莎姆舞”在表演過程和形式與藏族莎姆類似,大致分為迎神——娛神——送神三個階段。同時“莎姆”也是一種眾人參與的大型祈福活動,在經歷2013年地震災害后,新年里岷縣中寨鎮的群眾集體跳“莎姆”祈求四季平安,風調雨順,也是尋求一種心理安慰。
由于漢民族較為內斂的性格,“漢族莎姆”的舞蹈動作幅度相對較小;此外,在表演中還引入了龍、紅旗等漢文化元素;歌詞雖然采用藏語,但往往大多數人都不知其含義。
(三)“土族莎姆”
土族主要分布于青海,甘肅兩省。青海的土族主要受蒙古族文化的影響,但與青海的土族不同,卓尼勺哇的土族深受藏族文化的影響,其使用的語言和藏巴哇使用的藏語接近,[10]其歌舞風格也受到當地藏族的影響。
“土族莎姆”流傳于康多勺哇土族自治鄉,亦為一種巴郎鼓舞,當地又稱為“嘎兒日”。表演中的舞蹈道具與藏巴哇地區的巴郎鼓形狀相似,但更顯精巧。而且不論在表演形式上,還是舞曲的歌詞、曲調都絕無相近之處:土族的“嘎兒日”可由婦女表演,既可在露天表演,又可在室內表演,視表演者人數而定。由嘎爾爸(總排練指揮)領舞,圍繞點燃的篝火邊歌邊舞,忽聚忽散,口哨指揮,先左后右各繞三圈,然后動作變緩,速度轉慢,原地扭動腰身,鼓和燈則輕響輕搖,男女分成兩排,問答日月星辰,每次回答后,演員隨即搖鼓擺燈交換位置和跑隊形,并繞場旋轉,如此反復多遍。演員一手拿鼓,一手打燈籠,邊跳邊唱。歌詞內容極豐富,一首兩段,每段3句,一問二答,即興編詞,即使從晚上直唱到天亮也不乏其詞。但嘎兒日舞曲的樂曲卻僅有一首,調式為五聲羽調式,節拍規整,速度適中,旋律進行具有藏族弦子舞的風格可舞性很強。[11]
四、結語
在文化地理上,卓尼位于安多藏區的東北部,在漢、藏兩大文化區的邊緣地帶。自然地理的特點決定了它是游牧文明和農耕文明的過渡地帶,歷史上游牧民族和農耕民族之間的沖突常在此地爆發,但和平時期這里也是兩者之間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場所;同時,這里也是西北地區重要的民族走廊,多民族的歷史活動都在此留下了重要的影響。這些自然和人文的特征都在族群活動的“細枝末節”——“莎姆舞”中得到了反映:惡劣的自然環境決定了祭祀是舞蹈的重要的一部分內容,多民族的活動促進了多元文化的交融,而后“莎姆舞”又在各個族群中發生了演化和變異。
參考文獻
[1]卓尼縣志編纂委員會.卓尼縣志·地理志[M].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1994:63.
[2]馬寧.藏漢結合部多元宗教共存與對話研究[D].廣州:中山大學,2010.
[3]李紹明.藏彝走廊研究與民族走廊學說[J].藏學學刊,2005(1):2-5.
[4]洲塔.甘肅藏族部落的社會與歷史研究[M].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6:12.
[5]丹曲,謝建華.甘肅藏族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31-33.
[6]魏賢玲.卓尼藏族研究[D].蘭州:蘭州大學,2007.
[7]桑杰.甘南卓尼藏族民間的莎姆舞[J].西藏藝術研究,1999(4):14-19.
[8]卓尼縣志編纂委員會.卓尼縣志·建置志[M].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1994:171.
[9]后永樂.明代洮岷地區移民與社會變遷[D].蘭州:西北師范大學,2012.
[10]勉衛忠.話說甘南勺哇土族[J].中國土族,2004(4):35-37.
[11]卓尼縣志編纂委員會.卓尼縣志·文化藝術志[M].甘肅:甘肅民族出版社,1994:594.
作者簡介:靳波(1987—),女,藏族,甘肅蘭州人,四川理工學院藝術學院教師,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民族舞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