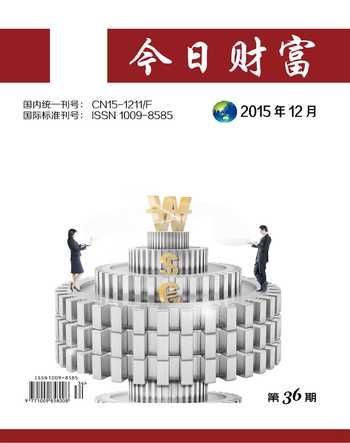《吉檀迦利》的隱喻研究
莊逸秀
摘要:《吉檀迦利》共分為103篇,是由泰戈爾本人用英文從孟加拉語詩作《吉檀迦利》、《渡船》和《奉獻集》里,選擇部分詩作而最終作成。《吉檀迦利》的孟加拉語詩作是韻律詩,而翻譯成英文之后變成自由詩。本章中,筆者將基于概念隱喻理論和詩學隱喻對《吉檀迦利》中的隱喻使用進行解讀,并對其進行語篇分析。
關鍵詞:隱喻
一、從概念隱喻角度看《吉檀迦利》
(一)、結構隱喻
《吉檀迦利》的隱喻基礎即為結構隱喻。作者在該詩集中有一個清晰地說話和行動的對象,這個對象貫穿于全文中,被作者以一種非常近的關系稱呼為“你”,有著與常人并無二致的動作和語言,例如:“這小小的葦笛,你攜帶著它逾山越谷,從笛管里吹出永新的音樂”;“你從寶座上下來,站在我草舍門前”。事實上,文中的“你”是我們可以視作目標域,該目標域的源域可以理解為一個抽象的概念,是作者在詩集中飽含深情獻禮的對象。通過隱喻,作者將這個對象作為一個活生生的人進行傾訴。同時,這個對象被作者冠以多種稱呼,例如“唯一的朋友”、“我最愛的人”、“愛”、“我的詩人”等等。Lakoff(1980)指出,概念隱喻的系統性雖然可以幫助人們去理解另外一個概念,這個理解卻并不是完整的,而是部分的。在突顯的同時,目標域的其他方面被隱藏或弱化,被突顯的方面是和源域密切相關的。
正如Lackoff(1993)所言,“隱喻是我們用來理解抽象概念,進行抽象推理的主要機制”;“隱喻讓我們用更具體的、有高度組織結構的事物來理解相對抽象的或相對無內部結構的事物”。在概念隱喻中,語言中的隱喻表達方式與隱喻概念體系是緊密相連的,思維與語言都具有系統性(趙艷芳,1995)。我們可以看到,貫穿詩集的還有一個結構隱喻的框架,即“生命是個旅程”。這樣的一個眾所周知的結構隱喻并沒有被作者非常明確地點明,但是卻不著邊際地蘊含在整個詩集中,使全詩的隱喻表達顯示出一定的整體性。
(二)、空間隱喻
空間隱喻相對而言是最不容易辨別的,因為它“置于人體、人的日常經驗及知識”,“絕大部分常規概念隱喻系統是潛意識的、自動的、使用起來是毫不費力的,正像我們的語言系統及概念系統的其他部分一樣”(Lackoff,1993)。王寅(2005)指出,概念結構中的所有事件和狀態主要是根據空間概念化組織起來的,并且所有的語義場幾乎都有類似于空間的組織結構。人們通常將一些抽象概念投射到具體的空間方位上,這些抽象概念包括情感(高興與悲傷)、數量(多與少)、道德(美德與墮落)、身體狀態(疾病與死亡)、政治經濟(繁榮與蕭條)等,涉及到多種語義域。
在《吉檀迦利》這樣感情充沛的詩作中,我們自然也可以看到空間隱喻在烘托情感方面的作用,如:“它炫耀著像將燼的世情的純焰,最后猛烈的一閃。”(It shines like the pure flame of being burning up earthly sense with one fierce flash.)
二、從詩學隱喻看《吉檀迦利》
在《吉檀迦利》中,也有擴展這種手段的應用。擴展就是將常規隱喻中的源域進一步擴展延伸,使其具有更加豐富的內涵。該詩集中最基本的常規隱喻就是“生命是旅程”,這里“旅程”作為源域還屬于較為籠統的概念,作者將其進行了多方位的延伸,使“旅程”的概念更加飽滿起來。例如作者為“旅程”加入困境:“不理連連呼喊的狂嘯的東風,一張厚厚的紗幕遮住永遠清醒的碧空”;“糧袋已空,衣裳破裂污損,而又筋疲力盡”;旅途中的目標:“在那里,心是無畏的,頭也抬得高昂;在那里,知識是自由的;在那里,世界還沒有被狹小的家國的墻隔成片段;在那里,話是從真理的深處說出……”顯然,我們也可以在該詩集中看到將各種隱喻組合而形成復合隱喻,例如在“我把她深藏在心里,到處漫游,我生命的榮枯圍繞著她起落”一句中,我們可以看到結構隱喻、空間隱喻和本體隱喻的結合,其中,結構隱喻存在于“深藏在心里”(keeping her in the core of my heart);空間隱喻存在于“我生命的榮枯圍繞著她起落”(around her have risen and fallen the growth and decay of my life),而該句本身就是一個結構隱喻。
三、從語篇角度看《吉檀迦利》
前文已經提到,語境在語篇對概念隱喻實例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語境和語篇間具有互動關系,語境創造語篇,語篇也同樣創造語境,而文本的深層意義就產生于這兩者的磨擦之中。《吉檀迦利》詩集中兩層意義:本義和隱喻意義。本義可以根據語境加以理解,而隱喻的定義表明理解目的域的意義要依靠源域,源域與本義相聯系,因此隱喻意義的理解要靠本義,因此要結合讀者的知識與經驗通過本義的中介經過推理從語境中獲得(任紹曾,2006)。
為了了解語篇如何展開,需要考察語篇的進展方式和要點。《吉檀迦利》小句的主位以人稱代詞居多,“我”和“你”的使用次數均超過百次。這說明作者頻繁地從第一人稱的角度出發,與創造出的人物進行交流、抒發情感,而這正是貫穿語篇的重點。詩集中小句的新信息基本上構成了積極與消極這兩種基調,如“是你拉上夜幕蓋上白日的倦眼,使這眼神在醒覺的清新喜悅中,更新了起來”;“云霧遮滿天空,雨也不停地下。我不知道我心里有什么在動蕩,--我不懂得它的意義”等,共同凸顯出了生命的復雜。
《吉檀迦利》是部分為103個段落的詩集,結構也顯得較為復雜。小句的主位多圍繞“我”和“你”展開,小句的新信息是“我”和“你”之間在“旅程”中發生的一系列關系;就語段而言,依托不同的語境,“我”和“你”被投射到旅程中不同的身份,由此展開各種新的信息,其中語境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吉檀迦利》中,宏觀主位并不在篇首容易辨識的位置,實際上,整個詩集是就“生命是個旅程”這個隱喻概念展開的,這樣的隱喻框架已經蘊含在詩集的字里行間,也點出了語篇所涉及的兩個領域:將“旅程”投射到“人的生命”上,說明這一概念隱喻在這里將被語篇化。宏觀新信息就是“旅程”中的各種遭遇。
四、結語
本文基于概念隱喻的理論,從結構隱喻、空間隱喻和本體隱喻出發,對《吉檀迦利》詩集中所運用的隱喻手段進行分析,在該詩集中,我們可以看到結構隱喻、空間隱喻和本體隱喻的融洽地結合,使得詩集在主題的呈現上各為多樣化和形象化;基于詩學隱喻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到詩集中不乏通過概念工具對常規的概念隱喻進行的策略性操縱,使主題的呈現更具整體感,詩中所塑造的形象也更為飽滿。通過對《吉檀迦利》進行語篇分析亦可發現,該詩集在結構安排上張弛有度,在語篇的推進中前后呼應,使得“生命是旅程”的概念隱喻框架很好地溶于整個詩集中。
參考文獻
程瑾濤.(2013).詩學隱喻的創造力理據——隱喻的語境研究新視角.外語與外語教學,4,011.
黃婉梅.(2014).《吉檀迦利》的愛情主題闡釋:基于篇章語言學視角.安徽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42(2),241-245.
金克木.(1981).泰戈爾的《什么是藝術》和《吉檀迦利》試解.南亞研究,1.
劉小琴.(2011).論概念隱喻.語文學刊:外語教育與教學,(10),19-20.
苗興偉,&廖美珍.(2007).隱喻的語篇功能研究.外語學刊,6,5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