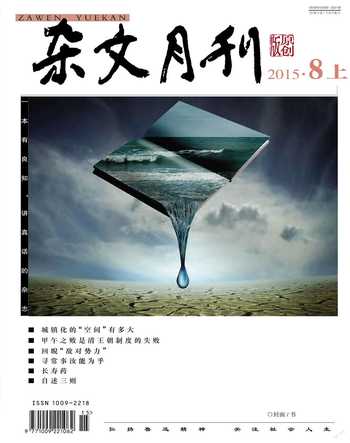張集馨何以“反潮流”
游宇明
咸豐九年(1859年)九月初八日,年已花甲的張集馨奉旨署福建布政使。出乎京官的意料,張氏陛辭離京,居然不聲不響,沒給各部官員留一絲一毫“別敬”。一眾京官們嘴上沒說什么,心里卻將牙齒咬得咯咯響。
清代腐敗盛行,有些腐敗行為甚至成為一種大家都認可的“習慣性動作”,誰也不覺得有什么不對,也少有人想到要革除它們,比如地方官收取漕規、關規、鹽規、火耗、三節兩壽禮等各種陋規,比如京官收取地方官的“別敬”“冰敬”“炭敬”。換句話說,在那個特定環境下,送這些東西是“理”所當然的,不送則會顯得特別突兀,非常“不友好”。
張集馨其實并不是海瑞式的人物,他雖未在任上貪多少錢,對官場的潛規則卻也是身體力行的。史料記載: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張集馨被補授陜西督糧道這個肥差,曾花幾萬兩銀子買禮物、送別敬,以致弄得連就任的盤纏都成了問題。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張集馨升任四川按察使,入京請訓,“別敬軍機大臣,每處四百金,賽鶴汀(賽尚阿)不收;上下兩班章京,每位十六金,如有交情或通信辦折者,一百、八十金不等;六部尚書、總憲百金,侍郎、大九卿五十金,以次遞減;同鄉、同年以及年家世好,概行應酬,共用別敬一萬五千余兩”。
有清一代,不要說張集馨這樣的官員,就是身為總督、極其厭惡官場腐敗的曾國藩同樣無法免俗。同治七年(1868年)七月二十日,曾國藩由兩江總督改任直隸總督,十二月入京請訓,在京盤桓一個多月,正月二十日出都赴保定任職。從十四日開始,他就開始籌劃別儀,除十八日外,每晚臨睡前都要審核別敬單,甚至在出都的當天上午,還審核了一次。由此可見他對送“別敬”之重視。
其時各種“敬”禮如此盛行,署福建布政使時的張集馨為何要如此“反潮流”呢?在年譜中,張集馨這樣解釋:“京中同人,以及同事,原該留別,竊思時勢艱難,無從借貸。且我年已六秩,官興闌珊,不值熱中要求權貴,即或百端羅拙,抵任后無力償還,累己累人,諸多窒礙。且思命中如果能升至巡撫,何至兩遇坎坷,其福命之衰薄,已可想見!今已立定主意,三五年內決志回京,何苦終身不悔,甘心降氣,為人屬吏耶!”在年譜的另一處,張集馨間接地說明了不送別敬的更深層的緣由:“應酬不可謂不厚矣。及番案牽連,朝右士大夫持公論者甚少,轉以附會琦文勤為余罪案……余資格官聲,當開府者久矣,曾未聞有力陳政績上有識之士宸知者,則應酬又何恃乎?”這兩段話,說了三個意思:一是自己年老,對升遷已沒有多少興趣,不必要巴結權貴;二是自己經濟情況不好,要送“別敬”就得借錢,而當時“時勢艱難,無從借貸”;三是遭遇坎坷時,那些曾經收受過他好處的人并沒有為他說話,他覺得再送“別敬”不值得。
關于張集馨的“兩遇坎坷”,這里稍稍解釋一下。道光三十年(1850年)張集馨本已成為河南布政使,眼看就要高升巡撫寶座,卻因牽連于當年做甘肅布政使時發生的琦善捕殺良番案,被革職遣戍軍臺。一年多后獲釋賞四品頂戴,補授河南按察使,未赴任即平調直隸幫辦軍務,遭直隸總督桂良誣諂,留在勝保軍營將功折罪,直到咸豐六年(1856年)才又賞四品頂戴,署甘肅布政使,在布政使、按察使的臺階上徘徘徊徊,一晃就是十來年。而事實證明,張集馨遭遇的這兩次挫折都是冤案,本人并無過錯,他對自己前期給京官們所送“敬”禮的意義由此生出疑心理所當然。
由張集馨送“別敬”的經歷,我們可以看到清代各種“敬”禮背后的一個真問題:“敬”其實只是一個借口,實質上是送“敬”之人赤裸裸的利益算計,那就是希望得到受“敬”者的特殊關照。張集馨的“反潮流”,其實不過是對官場生意的一次利害“盤底”。由此聯想到現在某些喜歡給有權者送禮的人,他們的禮物背后藏的又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