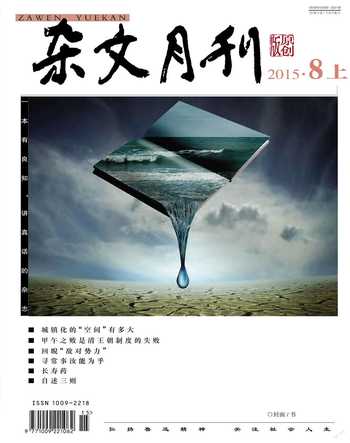畫鬼容易畫狗難
汪金友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中有個故事,一位畫家為齊王作畫,齊王問他:“畫什么最難?”畫家回答:“畫狗和馬最困難。”齊王又問:“畫什么最容易?”畫家說:“畫鬼怪最容易。”齊王不解:“為什么?”畫家解釋:”因為狗和馬,人人都熟知,每天都能看到。如果你畫得不像,人家很快就會發現。而鬼怪一類的東西,從來就沒有人見到過。所以你就可以隨心所欲,想怎么畫就怎么畫。”
按說,狗與馬這些動物,人所共知,旦暮見之,應該是最容易畫的東西。一般的畫家,寥寥幾筆,就能惟妙惟肖地畫出一只狗或一匹馬。但正因為狗與馬是人們最親密、最熟悉的動物,人人心中都有一只、一匹真實的狗與馬,所以畫家畫出來的狗與馬,就最容易為人挑出個理兒來。
以畫狗為例,首先,會有人說三道四:看他畫的這只狗,兩只耳朵怎么豎了起來?這哪是狗,我看像一只狼。再看這狗的尾巴,怎么那么長?還有,這家伙呲牙咧嘴,目光兇狠,一看就不是一只好狗。
接著,可能就會有人對號入座:你怎么畫我們家的狗?經過我們同意了嗎?這侵犯了我家狗狗的肖像權和隱私權。
繼而,還會有人懷疑你的創作意圖:現在全社會絕大多數的狗,都是好狗。無論看家護院還是陪伴主人,它們都忠心耿耿,盡職盡責。還有很多的狗,為盲人帶路,幫警察破案,做過不少的好事。而你畫的那些狗,要么咬人,要么擾民,要么隨地大小便,絕大多數的好狗你不畫,單畫少數幾條癩狗,這不是成心敗壞狗的名聲嗎?
既然畫狗(畫馬)不容易,那就畫鬼吧。于是在中國歷史上,就出現了很多擅于畫鬼的大畫家。比如吳道子、陸探微、張僧繇、閻立本、董伯仁、韓干、梁楷、崔白等,都畫得一手“好鬼”,留下了很多的“鬼畫”。
不單畫家作畫,話家開口說話講故事,越是人們熟悉的真實存在的素材,越是難講,于是就如作畫一般,那就專講鬼故事吧。蒲松齡,就是最擅講鬼故事的一位,且講出了大名堂。郭沫若為他的故居題聯:“寫鬼寫妖高人一等,刺貪刺虐入骨三分。”老舍也曾這樣評價蒲松齡的《聊齋志異》:“鬼狐有性格,笑罵成文章。”蒲松齡雖滿腹學問,卻屢試不中,72歲時方補為貢生,人生修齊治平的夢想無法實現,只好借鬼怪之口,或刺貪刺虐,或揚善懲惡。
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科學文化的傳播,越來越多的人,都知道在我們這個世界上,根本就沒有鬼,于是不會再把人生意愿寄托于虛幻之中,而更希望關注現實的狗與馬。這一下,畫家及話家們的日子就不好過了,尤其是一些濫竽充數并充出一些名和利的人,就更難過了。可難過也得過,一些聰明的畫(話)家就想出個新轍——其實還是故轍一條——畫(話)現在的人們所不熟悉的東西:你不熟悉皇帝,他就畫(話)皇帝;你不熟悉江湖,他就畫(話)江湖;你不熟悉盜墓,他就畫(話)盜墓;你不熟悉戰爭,他就畫(話)戰爭……不是實畫實說,也不是戲畫戲說,而是憑著自己的想象,隨心所欲,胡畫(話)、亂畫(話)、瞎畫(話)。而且這樣的“畫(話)作”,還經常被搬上熒屏,擺上書架。只要他沒有畫(話)出丑態,只要他的畫(話)合乎所謂的“絕大多數”,就沒有人對他的畫(話)挑真假。
既然生活中有狗,狗模樣有好有孬,狗脾氣有溫順有兇惡,狗行為有咬人的有助人的,一句話,狗有好狗也有壞狗,你畫出來的狗,自也可有好有壞。無論你畫與不畫,無論你對畫出來的狗挑東挑西,現實之中,每個時代,都有好狗,也有壞狗。
【豆 薇/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