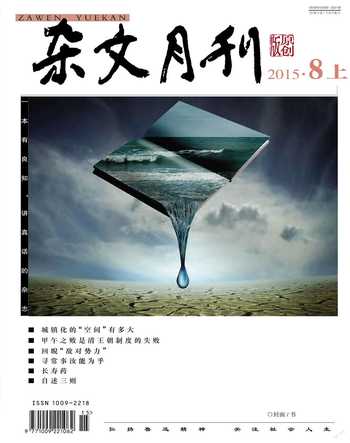貼手農具
李業成
有兩個農業符號給人的印象最深,一是歷史課本上的那張耜,耜是最早的犁田農具;再一個是頭戴草帽,身披蓑衣,肩荷一把鋤頭的佝僂老農。這兩個農業符號都與農具有關。
古時有個典故,有一位將領,每日枕著戈睡覺,有人問他何故,他說:“我以此戈取功名!”這個典故含譏諷之意,但除卻那份功利心,這種務實得沒有雜念雜質的事業態度,當與老農差不多。
老農手里的農具就是用來謀食的,農人與農具有著說不出的感情。農人之外,可能很少有人近距離見過那些農具,或親手摸一摸那些農具,他們對農具只是一個大概的印象,只認識農具的形,不認識農具的情。農具不只是一個形體,也是一個感情體。我是摸著農具長大的,一家人下地干活,一人一件農具,很少混用,各人的農具各人用得順手。同樣是一把鐵锨,一把鋤頭,不同的人用起來感覺差別非常大,如果這些農具順手好用,既出活兒又減少疲勞,用得不順手,結果就相反。這些農具的好用與否最主要的取決于柄。比如鐵锨,它的木柄選擇有彈性的獨木才好,借助木柄的彈性,干起來活兒來就會節省不少力氣,而且借助锨柄的彈性產生的那種節奏感讓人愉悅,覺得像變了一個人似的。镢柄和鋤柄同樣都有自己的最佳原理。自己手里的農具用久了,不僅順手還會產生感情,每一件農具使起來都貼手應心。
鐮刀也是一個農業符號,它幾乎就代表了一個“農”字。那長得像樹一樣的高粱、苞米,在鐮刀下刷刷倒地,成片的金黃色的稻麥,在鐮刀下刷刷仆倒,人站在田野上,最大的痛快感就是手中握有一把鐮刀。鐮刀的造型天生宜收割和砍伐莊稼,它的短柄、長鋒、利刃、鈍背,在一個農人拉開的架式中,產生出最佳收割效果。鐮刀不分工,是男女通用的農具。古人造字,“男”字一目了然,就是農田里的體力人,而“女”字,猶如一個人與一架織布機造形,這就是男耕女織的農業社會的勞動分配。但女人后來也和男人一同下田,從事強度輕一些的勞動,鐮刀就是現成的一種適宜她們下田勞作的農具。女性懷抱稻禾,鐮在手,頭頂花帕,秋風爍金,在田野上極有詩意。勞動體現美,勞動與農具配合體現出人肢體的美,是原始的舞蹈。南風緊,麥梢黃,布谷鳥急急叫,萬事俱備,只欠鐮刀。于是天不亮,村莊里一片磨鐮聲。這是爺們兒的工作,把全家人用的鐮和備用的鐮全部提前磨好,磨出一指寬的白刃,然后嘩啦啦地抱到田頭,一展鐮刀之威。
一個農人手里的一件農具可以用一生。一把镢頭,是一生用不完的,磨損了,再讓村頭匠鋪里的鐵匠掛上一塊鋼繼續用。隨著收割機的使用普及,我本以為鐵匠這一行過時了,死猴了,沒想到,大集上居然見到有人在機動三輪車上生起鐵匠爐,真為他們的堅持高興。镢柄也是可以用一生的,镢柄都是柞木,最差的也是槐木,材質堅硬。所有镢柄、鋤柄、锨柄都像打蠟烤漆一樣光滑,這是長時間勞動的手磨成的。勞動者手上的農具不僅有他們的體溫汗水,勞動者每一次筋動脈跳也都與手中的農具互動。這就是手與農具的關系。我和農具一同下田,一同收工,不同的是,我躺著睡,農具站著睡。
記得早年鄉村有一種“掃盲”識字課本,至今還記得其中的文字:“叉筢掃帚揚場锨,碌碡簸箕使牛鞭……”兩句話就包含了七種農具,一篇課文能包含上百種農具。農具與農業、農業勞動密不可分,有一些農具現在雖然不用了,甚至見不到它的影子了,但它們都是農業的符號,就像耜和鋤頭是農業的符號一樣。滅草劑不是。
【童 玲/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