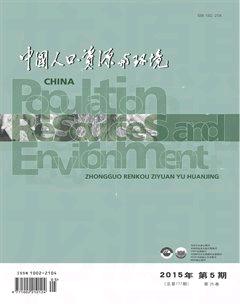碳交易與碳稅兼容性分析
魏慶坡??


摘要
隨著氣候問題日益突出和減排形勢的持續嚴峻,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國家開始嘗試多策并舉的方式來削減碳排放。但這兩種“單一對峙”的減排制度能否兼容成為我國低碳路徑選擇必須解決的一個現實問題。文章通過分析絕對減排目標和相對減排目標與碳稅的兼容性,提出相對減排目標下的碳交易能夠和碳稅兼容,共同實現減排目標;接著針對絕對減排目標下的碳交易與碳稅的相悖問題進行分析,提出通過引入限價模式、調整對象適度重合和有限分離、跨期儲存機制、項目抵消減排等揚長避短形成組合制度,以緩解碳交易對減排成本不確定和碳稅對總量控制的制度缺陷。從我國承諾的碳強度減排目標和碳交易試點實踐出發,基本對策是:立足我國實際,以社會經濟發展為基本目標下分階段進行:從中短期看,應采納碳稅和碳交易(相對減排目標)雙策并舉的模式進行減排;從長期來看,我國應該嘗試運用碳稅和總量控制和交易的碳交易(絕對減排目標)模式推動減排。
關鍵詞碳交易;碳稅;組合模式;中國減排;碳強度
中圖分類號X32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2104(2015)05-0035-09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5.05.005
隨著氣候問題的日益突出,國際社會對適應和應對這一變化的合作正在逐步加強。相對傳統環境政策工具——命令—控制的僵化性,擁有總量控制優勢的碳排放權交易市場(以下簡稱“碳交易”)和依靠價格導向的碳稅憑借市場化、激勵機制、靈活性、以及潛在財政收入等贏得了諸多國家和地區的青睞[1]。當今利用碳交易進行減排的國家和地區有:歐盟、澳大利亞、新西蘭、美國加州、加拿大魁北克、中國七個碳交易試點等;而北歐國家,如丹麥、挪威、芬蘭等則采用碳稅進行減排。作為全球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中國面臨著來自國際和國內的雙重減排壓力。為此,黨的十八提出要利用市場機制引導節能減排,運用制度創新保護環境,這表明市場機制和制度建設將成為我國應對氣候變化問題的主要政策導向。碳交易試點啟動運營后,財政部和環保部開始醞釀環境稅[2],擬對排放二氧化碳的單位或集體征收碳稅。這一方面體現了當下環境問題的復雜性,需要多策并舉實現“兩型社會”;另一方面也彰顯了中國政府削減碳排放,踐行國際減排承諾的決心。
1問題提出
理論上,在充分競爭、信息全面的市場中,碳交易和碳稅在減排效果上并無差異。因此早期對于碳交易和碳稅都是替代性方案的分析,而非相互補充的思路;實踐中,基于庇古理論的碳稅與源于科斯定理的碳交易受到了諸多現實因素影響,制約了理論減排效果的實現。具體而言,碳稅稅率的設定需要考慮邊際個人成本和邊際社會成本的差異,由于不同地區存在邊際減排成本和邊際社會成本的區別;礙于信息不對稱和地區差異性,即使當今數據基礎和統計技術不斷提升,為預估減排總量設定碳稅稅率依然困難重重。相比碳稅,基于科斯定理和產權理論的碳交易通過設定污染物總量創制出排放權的“稀缺性”,賦予其經濟價值,進而在減排主體之間形成交易市場。減排主體結合自身邊際減排成本和交易價格,以理性經濟人的思維參與碳市場激勵體系,削減溫室氣體排放,從而確保環境整體效果。但正如王毅剛所言,碳交易一直被認為“理論非常吸引人但實踐中并不可行”;尤其具體交易制度規則設定等難度較大,使其一度僅停留在概念中。
其次,如果減排成本預期較高,碳稅條件下的一些減排主體將選擇多繳稅以換取排放額度,導致總體排放量不減反增;而碳交易由于設定了排放總量,利用配額價格的變動來傳導減排成本的變化,導致減排成本具有不確定性。同時碳交易和碳稅的減排效果不僅受到經濟效率的影響,而且還要顧及部門行業競爭和收入分配問題,這些現實因素也會對減排運作機制形成制約,進而影響整體減排效果。從實際減排成本方面而言,兩者在預期減排效果的效率方面并非完美。出于單一政策解決單一問題的思維,以及效率、經濟、必要性等因素考慮,早期對于碳交易和碳稅替代性方案的研究遭遇到了現實障礙。因此,以實踐應用為導向,通過相互補充的思路調整優化兩者契合度是探索制度創新一個新方向和新任務。
國外對環境政策疊合(Policy interaction 或 Policy mix)的研究最早來自于政治學的貢獻:Wildavsky提出重疊是眾多政策發展的重要緣由,對內部問題的調整會帶動對外部問題的應對。Majone認為在政策眾多情形下,新方案將導致新問題出現,如政策重疊、管轄混亂以及其他一些始料未及的后果。環境問題方面,Roberts和Spence 提出應結合數量機制(Quantitybased approach)和價格機制(Pricebased approach)兩項政策來降低社會成本;Smith 提出在命令-控制的基礎上,附加稅收和補貼機制;Pizer 發現混合路徑略微優于價格機制,卻明顯勝過數量機制;Sorrel和Sijm 提出政策組合應謹慎設計,并且目標透明[10];Either和Pethig分析了歐盟ETS和不參加ETS而實行碳稅部門的減排協調問題[11]。除去大量關注替代性研究的同時,國外學者也對碳交易和碳稅在低碳減排方面的補充性進行了一些研究,并對潛在問題進行了積極分析,為我國環境政策工具制定提供了理論指導。
在低碳減排背景下,國內學者也對此問題進行了分析。許光[12]提出為了有效規制環境問題,應聯合運用碳交易和碳稅;在總結國際碳稅和碳交易的經驗后,朱蘇榮建議應結合兩者的各自優勢,綜合運用;通過對中國能源、經濟和環境的動態CGE模型的分析,應借助碳稅規制分散行業,實施碳交易調節排放集中行業,也有提出應先碳稅后碳交易的兩步走戰略。但王慧、曹明德則認為結合經濟、環境和外交等方面分析,碳稅更適合中國;而趙駿、呂成龍通過簡析兩者利弊,支持中國采納碳交易。
相比國外,國內減排起步較晚,研究粗放且缺乏深度。國內學者從兩者的理論起源、機制原理、政治可行性、市場接受度、國際競爭力、社會經濟影響等方面簡單分析,倡導組合運用。這種寬泛倡導有“病急亂投醫”之嫌,且缺失了對兩者契合度和可行性等核心問題進行分析,也缺少對碳交易和碳稅的兼容性進行系統研究。根據經濟模型,Aldy和Pizer指出氣候政策微調將影響多個經濟部門,且如果多個同時調節的政策內部存在較大離散,結果將很不理想。Fischer和Preonas提出多重政策調節之下,碳交易市場將無法準確反映出邊際減排成本。此外,環境政策工具還會涉及稅收、勞動力市場、商業往來、行政管理等大多數經濟部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