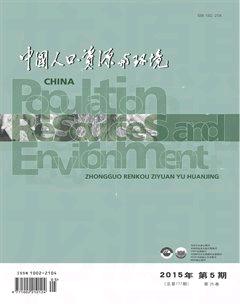承接產業轉移背景下區域土地利用空間協調評估



摘要
在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等政策背景下,我國東部沿海地區向中西部地區產業轉移的步伐明顯加快。合理配置產業空間布局是承接產業成功轉移的基礎,轉移企業對于區域土地利用現狀、土地供給指標和地方產業轉移政策的關注度也逐漸提高。促進產業轉移需要中部地區合理利用和保障土地資源,不同類型產業對土地利用、社會經濟等方面的需求也存在顯著差異。如何協調承接產業轉移與區域土地利用之間的關系逐漸成為研究熱點,尋求多類別、多層次的產業用地空間引導與配置方案,協調產業發展與土地利用綜合效益最大化對政府和轉移企業都具有重要的實際指導意義。本文圍繞承接產業轉移與區域土地利用的緊密聯系,基于動態系統協調理論,建立了包含動態修正的空間協調評估模型,從產業轉移、土地利用與企業耦合三方面進行綜合評估,確定產業轉移的具體空間引導方案,并以皖江城市帶及滁州市為研究對象進行了實證分析,以某汽車制造企業為例模擬了承接企業轉移的綜合協調評估過程。結果表明:滁州市承接產業轉移與土地利用空間協調度在皖江城市帶處于中度協調等級,承接產業類型具有顯著空間分異特征;最適宜承接汽車制造企業x轉移的地區為滁州市轄區郊區,第二、三位分別為全椒縣與天長市,各地區承接不同類型的產業園區提供了綜合協調的空間平臺和政策平臺。文章最后根據研究結論對我國產業轉移與區域土地利用等方面針對性地提出了政策建議。
關鍵詞承接產業轉移;區域土地利用;協調度模型;皖江城市帶;滁州
中圖分類號F06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04(2015)05-0144-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5.05.019
我國東部沿海地區受要素成本不斷上漲、資源環境壓力明顯加大等因素影響,迫切需要加快經濟轉型,推動結構調整升級,促進產業轉移。中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建設逐步完善、要素成本優勢明顯、內需潛力巨大,在國家促進中部崛起戰略與擴大內需、產業結構調整等政策背景下,承接長三角等東部沿海地區產業轉移的步伐明顯加快。促進承接產業轉移需要中部城市對土地資源的合理利用與保障,當下“保增長”和“保紅線”的問題在中部地區尤為突出,不同類型產業對土地利用、社會經濟等方面的需求也存在顯著差異。如何協調承接產業轉移與區域土地利用之間的關系逐漸成為研究熱點。尋求多類別、多層次的產業用地空間配置方案,協調產業發展與土地利用以實現綜合效益最大化對政府和轉移企業都具有重要的實際指導意義。
本文以承接產業轉移與區域土地利用為背景,基于動態系統協調理論,從產業與產業用地等多方面進行協調度評估,建立了土地利用空間協調度模型并進行實證分析,為承接產業轉移和區域土地利用的空間配置提供有效的技術支撐。
1研究綜述
產業發展依托于它們所在的地理空間,因此空間引導與配置方案是承接產業成功轉移的基礎。我國中部地區的承接產業轉移類型主要是第二產業,且轉移步伐逐漸加快,因此轉移企業對于區域土地利用現狀、土地供給指標和地方土地政策的關注度也逐漸提高。目前學界主要關注于產業轉移機制方面,如基于價值鏈分類研究生產制造業、總部經濟和研發企業的轉移機制,分析各產業的集聚發展階段特征,測度空間集聚效應等;新經濟地理學(NEG)則以規模收益遞增和壟斷競爭為理論框架更完整地解釋了企業遷移的動力機制;方勁松從跨越式發展視角考察了長三角產業向安徽轉移的過程,認為大規模承接價值鏈低端制造產業會加大資源環境承載壓力,抑制承接地新興產業發展;豆建民從環境污染的角度出發,發現地方政府為了招商引資而對轉移產業降低環保標準,由此產生的環境污染問題日益凸顯。另一方面,產業轉移的區位選擇與空間規劃研究逐漸增多。江霈研究了中西部工業產業轉移過程中空間布局、要素流動和集聚經濟的影響;馮根福發現資源密集型產業是空間轉移的主要對象,而勞動密集型產業由于自然資源的不可移動性基本不發生遷移;馮長春等人基于生態功能和生產效率的空間規劃路徑研究了皖江城市帶承接產業轉移的空間適宜性。
受實踐經驗和數據限制,金融危機后關于我國產業轉移的理論和實證研究比較缺乏,現有研究分析區位變化產業的特征時,往往采用歸納總結和案例分析兩種方法,難以準確地把握產業空間分布變化特征,并且幾乎沒有提出真正將轉移企業落實到承接地的空間引導和配置方案。正確量化產業轉移與區域土地利用的空間協調與耦合關系,一方面可以為政府將轉移產業具體落地提供空間規劃指導,防止項目違規、違法、盲目建設,優化產業用地空間布局,促進土地節約集約利用,提高土地產出效益;另一方面,動態的空間協調評估方法能夠全程實現數據的更新,提高日常土地資源管理的效率。
2動態修正的空間協調評估模型
“協調”指的是系統之間或系統組成要素之間在發展演化過程中彼此的和諧一致,系統之間或系統組成要素之間在發展演化過程中彼此的和諧程度稱為協調度。協調度模型已經應用于科技—經濟系統評估、區域經濟社會發展評估、土地集約利用評價和新型城鎮化協調思想分析等方面;歐雄、馮長春將協調度模型運用到土地利用潛力評價中,考察了土地利用的經濟、社會和生態系統的協調程度與發展潛力。
協調度模型是由一組函數構成的對系統協調程度進行測算的一種數量模型,其反映并取決于系統實際狀態與理想協調狀態的距離,這使得系統序參量上下限值的選取對于模型至關重要。傳統的土地利用協調度模型選取序參量限值時,上限值α選擇同類地區的相應指標,而下限值β選擇歷史平均值。然而這種方法并不能完整地表述出某些區域的實際上下限值范圍。尤其對中部地區,顯著的空間集聚效應往往使得區域中心經濟增長迅速而外圍地區逐漸衰退,呈現出“中心—外圍”結構,這是序參量指標超出傳統功效函數的上下限值區間的重要原因,如地均勞動力人數跌至歷史平均值以下時,其功效函數值為負,導致協調度也可能出現負數,無法解釋其意義。為了更好地處理上下限值以保證現有數據為其區間子集,同時能夠體現出區域的動態極化過程,本文對模型的上下限值設定進行了動態修正。endprint
為描述不同地區的經濟空間分異水平,本文引入薩繆爾森“冰山運輸”的概念,其原始思想是產品在運輸過程中,各種隱性的運輸成本“融入”價格之中,避免了單獨為運輸成本建模分析,同時簡潔地描述空間差異的經濟距離。設離岸價格為ps,到岸價格為pr,運輸成本為T,則“冰山運輸”過程可表示為
pr=psTrs=pseτd
其中,d表示地區s與地區r之間的距離,τ為差異系數,從而兩地區同產品的價格差異就可以衡量出區域分異的程度。基于這種思想,我們將量化后的空間分異程度反映在協調度模型的原始上下限值α和β上,即修正后的上下限值可表示為
ai=αiekDbi=βie-kD(1)
D=nσi∑ni=1xi(2)
其中,xi (i=1,2,…,n)為序參量指標,σ為xi的標準差,D定義為系統離差系數,ai、bi為新的上下限值,k為調節系數,則功效函數可以改寫為
ui=(xi-bi)/(ai-bi),當ui為正功效時(3)
ui=(xi-ai)/(bi-ai),當ui為負功效時(4)
ui為指標i對該子系統i (i=1,2,…, n)的功效。可以發現,調節系數k的變化可以改變上下限值的范圍區間,同時保持離差系數不變,即在準確描述空間分異的情況下,適當的設置調節系數完全可以保證所有指標位于限值區間之內。在進行多次空間協調評估時,只需設置適當的調節系數k即可,這樣的動態修正一方面節省了數據整理和評估時間成本,一方面空間集聚效應依然能夠在協調度模型中體現。由于集聚效應多出現在社會經濟方面,而在城市公共服務和生態保護等方面并不顯著,故修正模型主要應用于經濟子系統和社會子系統中的部分指標。序參量指標趨近于合理值大小的功效函數表示為:
ui=1-xi-c0/c0(5)
其中,c0為序參量的合理值,則子系統協調度可以表示為
c=(∏ni=1ui)1n(6)
由于不同產業類型對應的同類指標差異較大,故選取產業轉移協調度時,功效函數的限值需要依據不同產業類型分別設定。在研究區域承接企業轉移的空間匹配程度時,需要考察目標轉移企業與地區產業之間的耦合程度,許多學者使用耦合度的概念闡述了區域產業轉移與承接地產業集群的耦合關系。本文定義企業轉移耦合度為
cE=(ueuj)/(ue+uj2)2k(7)
其中,cE表示轉移企業E的綜合指標e (e=1,2,…,n)與地區j (j=1,2,…,m)內對應產業類型協調度的耦合程度,耦合程度越高表明企業E越接近該地區所屬產業類型的企業平均水平。k為調節系數,當k≥2時,c取值范圍在(0,1)內。區域土地利用協調度cL與分類產業協調度cI使用(6)式計算,而企業轉移協調度cE使用(7)式計算。為避免人為主觀確定指標權重的不穩定因素和個別極值偏離過大的情況,使用幾何平均值法替代特爾斐法、熵值法確定權重等線性加權法,綜合空間協調度可表示為:
Cx=(cLcIcE)13(8)
其中,Cx表示從屬于產業I的某企業x在地區L的綜合空間協調度,cL表示為土地利用系統協調度,其余為產業轉移協調度cI,和企業轉移耦合度cE,Cx∈(0,1)。考慮到我國土地制度特點、中部地區社會經濟現狀等因素,本文認為協調度值在0.7以上已足夠表明空間高度協調的狀態,表1顯示了綜合空間協調度的分類,及對應協調狀態的說明。
3承接產業轉移與區域土地利用空間協調評估指標體系
3.1承接產業轉移空間協調評估指標體系
不同類型的產業對區域土地利用、社會經濟以及政府政策的要求存在顯著差異,如裝備制造、原材料等類型產業由于技術、固定成本等因素占地面積較大,容積率較低,承接這類產業的地區對政府提供的土地指標需求較大;高新技術、商貿物流等類型產業占地面積較小,對外交通頻繁,容易產生規模經濟,承接這類產業的地區對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設施水平要求較高。因此,在協調度模型中選擇承接產業轉移功效函數的上下限值時,經濟水平、空間需求等序參量指標也需根據不同類型產業的特點選取。
我們首先對各項序參量指標判斷功效性。其中,產業圖斑面積、建筑系數等指標均選擇趨近于合理值的功效函數,這是因為各承接產業園區對入駐企業存在最低標準,要對轉移企業的畝均固定資產投入、容積率、建筑系數等進行限制;考慮到園區土地利用強度和對轉移企業每年畝均稅收的要求,園區建成面積、綠地率等選取上限值型功效函數。表2給出了一套承接產業轉移空間協調度的評價指標體系。
3.2區域土地利用協調評估指標體系
區域土地利用評價指標體系需要準確地反映區域土地的投入產出、土地利用結構等現狀,以及其帶來的經濟、生態等效益。由于評價結果必須為產業轉移提供微觀的空間配置方案,本文綜合協調度評價的最小單元設為區縣一級。考慮到區縣數據的可獲得性,本文將城市土地利用系統劃分為經濟系統、社會系統和生態系統三類,每個系統中又細分為多個序參量指標。工業用地占建設用地比例等指標參考《工業項目建設用地控制指標》、《城市用地分類與規劃建設用地標準GBJ137- 90》等選取合理值,建筑系數、容積率等合理值參考以往的相關研究。表3給出了一套土地利用系統協調度的評價指標體系。
4實證分析
4.1皖江城市帶與滁州市區域背景
皖江城市帶是實施促進中部地區崛起戰略的國家級示范區域,是長三角地區產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和輻射最近的地區,包括合肥、蕪湖、馬鞍山、銅陵、安慶、池州、滁州、宣城、六安(金安區、舒城縣)共59個縣(市、區),輻射
安徽全省。2012年安徽省級以上開發區億元以上投資項
目1 521個,皖江城市帶實際利用省外資金達3 538.8億元,占全省的70%。2010年《皖江城市帶承接產業轉移示范區規劃》將裝備制造業、原材料產業、輕工紡織業、高新技術產業、現代服務業和現代農業作為重點承接產業。endprint
滁州市地處安徽省最東部,屬長三角合作核心區、“南京都市圈”核心層、國家級“皖江城市帶承接產業轉移示范區”第一站,區位優勢明顯,在承接產業轉移與產業發展升級方面具有典型的代表性。2012年滁州市生產總值970.7億元,增長14%,居全省第5位,地方財政收入153.2億元,列全省第5位。
4.2數據來源與參數選取
本文土地利用相關數據來源于《滁州統計年鑒》(2001-2013)、安徽省統計年鑒(2000-2013)、安徽省建設統計年鑒(2001-2013),同時收集到皖江城市帶與滁州市縣級及以上經濟技術開發區至2012年的產業目錄資料,包括園區企業經濟效益、土地利用現狀、建設運營等數據。由于鄉鎮級工業集中區基本不承接轉移企業,本文設定產業園區數據選取對象為省級以上產業園區共13個(1個國家級產業開發園區,12個省級產業開發園區)。考慮到不同年份指標解釋差異和數據可獲得性,本文將滁州市瑯琊區與南譙區郊區統稱為市轄區處理。
在選擇區域土地利用協調度模型的上下限值時,本文將下限值選擇了2000、2005與2010年三年對應指標的平均值,上限值選擇皖江城市帶所有區縣相應指標中的最大值;本文根據《皖江城市帶承接產業轉移示范區規劃》承接產業類型規劃和產業園區目錄資料,將研究對象分為裝備制造、原材料、輕工紡織與高新技術四類產業。在進行協調評估時,經濟子系統的上下限值分別為皖江城市帶所有市區縣中相應指標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園區企業容積率、建筑系數等限值參考各園區轉移企業入駐審批標準和《工業項目建設用地控制指標》(國土資[2004]232號)中相應類型產業指標的平均值。樣本描述性統計見表4。
為實際模擬滁州市承接具體轉移企業的項目落地評估過程,假設某汽車制造企業x要轉移至滁州市,通過計算綜合空間協調度為該企業選址。考慮到滁州市各項現狀數據統計情況,本文設定土地利用協調度模型的調節系數kL=1.55,承接產業轉移協調度模型的調節系數kI=0.1,計算企業轉移耦合度的調節系數設為kE=2,以保證耦合度區間在(0,1)之內。本文計算企業轉移耦合度時,考慮到產業園區目錄資料內容與企業數據可獲得性,將指標體系分為企業效益、運營情況與用地情況三部分,表5給出了企業轉移耦合度的指標體系與模擬企業x的對應參數。
4.3評估結果
度評估結果。滁州市適合承接轉移的產業為裝備制造和高新技術,不適合承接原材料和輕工紡織等產業;從滁州市內部來看,市轄區郊區比起其他區縣更適合承接產業轉移,其次是全椒縣(裝備制造類)、天長市(原材料類)、明光市(輕工紡織)和全椒縣(高新技術)。這是因為每個產業園區規劃承接產業的類型有所差異,一旦同類產業入駐企業數量增加,專業化生產帶來的規模外部性使得承接同類產業轉移更具有成本優勢,同時也促使園區與當地政府提供對應產業類型的配套設施和入駐優惠政策以提高生產率,促使綜合協調程度進一步提高。
表7和圖1顯示了2012年模擬企業x轉移至滁州市的企業轉移耦合度和綜合空間協調度評估結果。可以看出,土地利用協調度與裝備制造業轉移協調度最高的地區均為市轄區郊區,其次為全椒縣和天長市。兩者基本同步變化,這是因為土地利用狀態高效的地區對產業轉移更有吸引力,而同類產業集群帶來的規模外部性又帶動當地經濟發展,提高土地的投入產出。汽車制造企業x轉移耦合度最高的地區為定遠縣(0.681),其次為明光市(0.634)和天長市(0.624)。機械制造類產業在這三個地區中均為規劃承接產業,因此產業園區的相關配套和稅收政策都向該類產業傾斜,使得轉移企業與產業園區的耦合關系更加緊密。綜合空間協調度最高地區為滁州市轄區郊區(0.455),其次為全椒縣(0.381),天長市(0.339)排名第三。滁州市大部分產業園區都集中在這三個地區,市轄區與相鄰的全椒縣形成了市域經濟增長極,天長市區位緊鄰于東南部的南京市,屬于南京都市圈的經濟輻射范圍,對于產業轉移與要素流動都具有較強的吸引力。從皖江城市帶尺度來看,綜合空間協調度均未達到0.5以上,僅處于中度協調水平,相較于合肥、池州和銅陵,滁州市的裝備制造類產業相對落后于作為主導產業的合肥和蕪湖,不過隨著南京與滁州交通條件的逐步改善,未來滁州承接產業轉移還有很大的潛力。
產業園區提供了資源綜合協調配置的空間平臺,因此不能以城市土地利用現狀作為承接產業轉移落地的評價標準,應當考慮園區土地利用效率和土地指標供給的特點,深入挖掘承接產業轉移的潛力;另外,政府應針對不同類型的產業特點與規劃承接產業類型,綜合本地產品市場、要素流動和交通環境現狀,制定分類產業扶持政策與土地資源配置方案,吸引更符合本地發展特征的企業入駐。
5結語
本文通過建立動態修正的空間協調評估模型,以皖江城市帶為研究區域,對滁州市進行了綜合空間協調評估,模擬了承接轉移企業項目落地的空間引導過程,為承接產業轉移和區域土地利用的空間配置提供了一種有效的技術支撐。各類產業園區在綜合協調配置產業轉移與區域土地利用中提供了空間平臺和政策平臺,一方面承接產業轉移規劃與相應的園區優惠政策吸引了同類企業數量不斷增加,規模外部性使得本地區對該類型企業更有吸引力;另一方面,每年新增的土地指標通常會被優先分配給產業園區,配合土地和稅收政策,使集聚效應帶動了土地利用狀態的進一步優化,這種空間協調實質上是本地規模效應與土地利用效率的累積循環機制。
中部城市每年建設用地指標較少、用地緊張導致轉移企業遲遲不能入駐的現狀,是地方政府與學者未來需要重點研究的問題,由于數據限制,本文在評估中并未直接加入相關指標,未來可以加入描述土地指標供給等具體序參量進行完善。
基于上述研究結論,本文提出兩點政策性建議:第一,根據本地區優勢產業發展現狀與產業園區相關招商引資政策,針對性地承接適合本地的產業類型,配合差異化的稅收優惠政策,促進落地產業與本地產業的價值鏈融合,完善產業垂直分工體系;第二,根據本地區土地資源存量與本地土地供給指標,主動承接價值鏈高端產業,引導產業園區形成規模經濟效應,帶動承接產業用地的集約節約利用,優化承接產業園區的空間規劃與轉移企業的空間引導方案。endprint
(編輯:劉照勝)
參考文獻(References)
[1]賀清云, 蔣菁, 何海兵. 中國中部地區承接產業轉移的行業選擇[J]. 經濟地理, 2010, 30(6): 960-964. [He Qingyun, Jiang Jing, He Haibing. Research on Choices of Undertaking Industrial Transfer in China [J]. Economic Geography, 2010, 30(6): 960-964.]
[2]魏后凱, 白玫, 王業強. 中國區域經濟的微觀透析:企業遷移的視角[M]. 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 2010: 140-144. [Wei Houkai, Bai Mei, Wang Yeqiang. The MicroPerspective of Regional Economy in China: A View of Firm Relocation [M].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2010: 140-144.]
[3]劉紅光, 王云平, 季璐. 中國區域間產業轉移特征、機理與模式研究[J]. 經濟地理, 2014, 34(1): 102-107. [Liu Hongguang, Wang Yunping, Ji Lu. Characteristics, Mechanism and Pattern of InterRegional Industry Transfers in China [J]. Economic Geography, 2014, 34(1): 102-107.]
[4]歐陽朝旭. 基于產業集聚下的安徽承接產業轉移的產業定位研究[J]. 科技與產業, 2009, 9(12): 13-17.[Ouyang Zhaoxu. A Study on the Industrial Orientation about Anhui Undertakes the Transfer of Industries Based on the Industrial Cluster [J].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2009, 9(12): 13-17.]
[5]韓峰, 馮萍, 陽立高. 中國城市的空間集聚效應與工業能源效率[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14, 24(5): 72-79. [Han Feng, Feng Ping, Yang Ligao. Spatial Agglomeration Effects of Chinas Cities and Industrial Energy Efficiency [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4, 24(5): 72-79.]
[6]丁建軍. 產業轉移的新經濟地理學解釋[J]. 財經科學, 2011, 274(1): 35-42. [Ding Jianjun.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Explanations on Industrial Transfer [J]. Finance & Economics, 2011, 274(1): 35-42.]
[7]方勁松. 跨越式發展視角下的安徽承接長三角產業轉移研究[D]. 合肥:安徽大學, 2010. [Fang Jinsong. Research of Anhuis undertaking the transfer of industr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apforward development strategy [J]. Hefei: University of Anhui, 2010.]
[8]豆建民, 沈艷兵. 產業轉移對中國中部地區的環境影響研究[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14, 24(11): 96-102. [Dou Jianmin, Shen Yanbing.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Industrial Transfer on the Environment in the Central Region of China [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4, 24(11): 96-102.]
[9]江霈. 中國區域產業轉移動力機制及影響因素分析[D]. 天津:南開大學, 2009. [Jiang Pei. An Analysis on the dynamic mechanisms and external influential factors of regional industrial transfer of China [D].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2009.]
[10]馮根福, 劉志勇, 蔣文定. 我國東中西部地區間工業產業轉移的趨勢、特征及形成原因分析[J]. 當代經濟科學, 2010, 32(2): 1-10. [Feng Fugen, Liu Zhiyong, Jiang Wending. An Analysis on the Trends, Features and Causes of Industrial Transfer among Chinas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J]. Modern Economics in Science, 2010, 32(2): 1-10.]endprint
[11]馮長春, 曹敏政, 甘霖. 皖江城市帶承接產業轉移的空間適宜性研究[J]. 經濟地理, 2014, 34(10): 91-92. [Feng Changchun, Cao Minzheng, Gan Lin. The Research of Spatial Suitability for Undertaking Industrial Transfer of Wanjiang City Belt [J]. Economic Geography, 2014, 34(10): 91-92.]
[12]趙建吉, 茹樂峰, 段小微, 等. 產業轉移的經濟地理學研究: 進展與展望[J]. 經濟地理, 2014, 34(1): 1-6. [Zhao Jianji, Ru Lefeng, Duan Xiaowei, et al. Industrial Transfer Study in Economic Geography: Progress and Prospect [J]. Economic Geography, 2014, 34(1): 1-6.]
[13]毛琦梁, 董鎖成, 王菲, 等. 我國產業轉移的研究進展評述與展望[J]. 區域經濟評論, 2014, (2): 138-147. [Mao Qiliang, Dong Suocheng, Wang Fei, et al. [J]. Regional Economic Review, 2014, (2): 138-147.]
[14]李植斌. 區域可持續發展評價指標體系與方法的初步研究[J]. 人文地理, 1998, 13(4): 70-74. [Li Zhibin. On the Index System and Method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valuation [J]. Human Geography, 1998, 13(4): 70-74.]
[15]孟慶松, 科技—經濟系統協調模型研究[J]. 天津師大學報, 1998, 18(4): 8-12. [Meng Qingsong. Study of the Coordinating Model for the Cosyste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Economy [J]. Journal of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1998, 18(4): 8-12.]
[16]周嫻, 李文軍. 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協調度評估: 模型與案例[J].探索, 2006, 2: 90-97. [Zhou Xian, Li Wenjun. Coordinating Evalua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J]. Probe, 2006, 2: 90-97.]
[17]樊敏, 劉耀林, 王漢花. 基于協調度模型的城市土地集約利用評價研究[J]. 測繪科學, 2009, 34(1): 144-146. [Fan Min, Liu Yaolin, Wang Hanhua. A Study on Intensified Utilization and Evaluation of Urban Land based on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J]. Science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2009, 34(1): 144-146.]
[18]李小建, 羅慶. 新型城鎮化中的協調思想分析[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14, 24(2): 47-53. [Li Xiaojian, Luo Qing. The Coordinating Ideas of Newform Urbanization [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4, 24(2): 47-53.]
[19]歐雄, 馮長春, 沈青云. 協調度模型在城市土地利用潛力評價中的應用[J]. 地理與地理信息科學, 2007, 23(1): 42-45. [Ou Xiong, Feng Changchun, Shen Qingyun. Application of Synergisticity Model in Urban LandUse Potential Appraisal [J]. Geography and GeoInformation Science, 2007, 23(1): 42-45.]
[20]孟慶松, 韓文秀. 復合系統整體協調度模型研究[J]. 河北師范大學學報, 1999, 23(2): 177-187. [Meng Qingsong, Han Wenxiu. Study on the Whole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of NonLine Composite Systems [J]. Journal of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1999, 23(2): 177-187.]
[21]湯鈴, 李建平, 余樂安, 等. 基于距離協調度模型的系統協調發展定量評價方法[J].系統工程理論與實踐, 2010, 4(30): 594-602. [Tang ling, Li Jianping, Yu Lean, et al.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Methodology for System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based on Distance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J]. System Engineering—Theory & Practice, 2010,4(30): 594-602.]endprint
[22]Krugman P.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1, 99:483-499.
[23]Fujita M, Krugman P R,Venables A J. The Spatial Economy: Cities, 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M].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9.
[24]Paul A S. The Transfer Problem and Transport Costs, II: Analysis of Effects of Trade Impediments [J].The Economic Journal, 1954, 64:264-289.
[25]汪婷, 汪時珍. 皖江城市帶開發區與承接產業轉移示范區耦合研究:基于馬蕪銅宜主要開發區的樣本分析[J]. 安慶師范學院學報, 2010, 29(7): 13-16. [Wang Ting, Wang Shizhen. Study on the Coupling between Development Zones and Demonstration Zones of Undertaking Industrial Transfer of Wanjiang City Belt [J]. Journal of Anqing Teachers College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0, 29(7): 13-16.]
[26]毛廣雄. 區域產業轉移與承接地產業集群的耦合關系[D]. 上海:華東師范大學, 2011. [Mao Guangxiong. The Coupling between Regional Industrial Transfer and Industrial Cluster in Undertake Area [D].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2011.]
[27]宋啟林. 從宏觀調控出發解決容積率定量問題[J]. 城市規劃, 1996, 20(2): 21- 24. [Song Qilin. Solving the FAR Quantity by Overall Control [J]. Urban Planning, 1996, 20(2): 21- 24.]
[28]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皖江城市帶承接產業轉移示范區規劃[EB/OL]. [2011-12-09]. http://news.hexun.com/upload/W0201003243481 60529291.pdf.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Demonstration Zone Planning of Undertaking Industrial Transfer of Wanjiang City Belt [EB/OL]. [2011-12-09]. http://news.hexun.com/upload/W0201003243481 60529291.pdf.]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