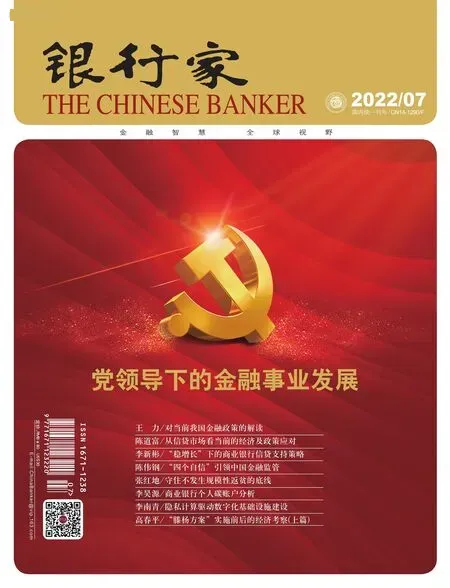農村金融深化有賴于農民組織化
陳林
供銷社辦金融:必要性與可行性
2015年4月,《關于深化供銷合作社綜合改革的決定》正式公布。這個文件包羅甚廣,較為引起關注的論述多集中于金融部分,如“允許符合條件的供銷合作社企業依照法定程序開展發起設立中小型銀行試點”;“鼓勵有條件的供銷合作社設立融資租賃公司、小額貸款公司、融資性擔保公司,與地方財政共同出資設立擔保公司”。近來,有關供銷社辦金融、甚至辦銀行的議論多了起來。
在質疑者看來,供銷社系統堅持“縣以上參照公務員管理”,至于縣以下,早已一潰千里,僅存的一些所謂基層社,不少是名存實亡,還有一些維持運轉的,大都是承包、租賃、掛靠的松散關系了,其行為模式和利益訴求與農村私營商販難有區別(如果不是更糟的話)。供銷社現在干的事情,國企民企都能干,甚至干得更好。供銷社既缺乏國企所受到的監管,也少有民企的生機與活力,更已喪失合作制的精神。所以一些觀點認為供銷社辦金融應當慎之又慎。
本文則認為,從金融業開放競爭的角度來說,既然國企、民企理論上都可以申請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的牌照,也沒有理由將供銷社所屬企業排除在外。但對供銷社來說,除了自身體制機制上的局限,現在辦銀行未必是一個好時機。隨著金融改革的深化,產業結構的調整,以及經濟周期下行的因素,過去躺在金融牌照上,就可以輕輕松松賺大錢的時代,恐怕已經過去了。何況一些人對于金融的認識,還片面停留在吸儲放貸上,一定要把錢緊緊抓在自己手里才過癮,焉知這樣的“資金池”就是步步驚心的“炸藥庫”呢。所以供銷社辦金融,值得歡迎,但是也要轉變觀念,引入農村金融新思維。
多年來金融界的主流興趣偏向于商業化、股份制、做大做強、全球化和互聯網、大數據之類貌似“高大上”的時髦詞匯,一些有意涉足金融業的投資者也受此影響。但是金融的終極本質,即人與人之間的信用關系,并沒有改變。這在農村金融領域表現得更為直觀生動。對于農村金融的特殊性,特別是發展合作金融的迫切性與可行性,過去是重視不夠的。
農民并非沒有信用,包括農村的中下層農民也有他們的信用。但是現有的銀行體系難以掌握農民的信用,因為信息的不對稱,管理半徑過長,單位成本過高。要充分發揮乃至放大農村和農民的信用,就必須降低農民與銀行之間的信息不對稱。農村金融中的信用與信息問題、從而風險與控制問題,需要借助農民組織化特別是新型合作化加以解決,從而促進農村金融深化,并在農村金融深化中有效維護農民的利益。從這個意思上說,農村最缺的不是錢,而是組織資源。這從存貸差來看很明顯,農村資金的大量外流是一個持續現象。好比在一個嚴重水土流失的地方,最缺的不是水,而是植被。
團結和組織農民,引導和幫助農民,本來是供銷社最該干的事情。供銷社本姓“農”,源于農民的集資和結社,要真正深化改革,回歸合作,回歸三農,而不是葉公好龍。只有真正落實廣大農民的主體地位,供銷社才能發揮自己的應有作用,而不是把一味向黨和政府要項目、要資源、要地位,在自身改革上原地踏步。如果不能建立與廣大農民的利益一致性,縱其取得商業成功繼續膨脹為一個“巨無霸”,亦非農民之福、?國家之幸。
金融回哺“三農”:結構與路徑
2015年3月,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原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吳曉靈在博鰲論壇的演講指出,把以家庭聯產承包制為基礎的小農組織起來,真正走上“三位一體”的合作道路,是未來的發展方向。中國銀行董事長田國立,早在2005年擔任中國信達資產管理公司總裁時,亦曾敏銳地發現和支持了浙江首創的農民專業合作、供銷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體”改革探索。
歐美、東亞一些國家和地區的農村金融,都是合作制主導的。歐美是專業化的合作銀行自成體系,東亞的成功模式則是綜合農協下設銀行,但中國都不能簡單照搬,而要采取符合自己國情的結構和路徑。
“三位一體”不是“三‘社一體”、“歸大堆”,也不是現有各種真真假假的合作社形式上的“松散聯合”。“三位一體”好比是個聯立方程,有唯一解、均衡解、穩定解!“三位”的公倍數是“農村”,公約數是“合作”,一體在于“農村合作協會”(新型農協)。
經過試點縣市的實踐驗證,在“三位一體”合作組織的基本構架下,轄區農民和各級各類合作社普遍進入農村合作協會(農協),原有農民專業合作社得以規范、充實和提升,同時推動基層供銷社開放改組融入合作協會,從根本上實現供銷社回歸“三農”與合作制;信用聯社(合作銀行)的原有社員(小額股東)也進入合作協會,并通過合作協會托管持股合作銀行,形成產權紐帶;合作銀行(以及其他銀行、保險機構)又可依托合作協會、合作社發展信用評級、小組聯保、反擔保等金融創新,拓展營銷網絡,既控制了金融風險,又放大了農村信用。這一設計是與孟加拉鄉村銀行異曲同工的。
當年浙江瑞安率先試點“三位一體”,是政府與民間深入互動,涉農部門共襄盛舉,金融單位更發揮了積極開拓的作用。由于金融專家的參與,試點之初就巧妙避開法律禁區和市場壁壘,提出的口號是:“沒有真金白銀,也可以搞信用合作”。銀行里的錢有的是,現有銀行的網點也不少,何必搞重復建設或者存款競爭,農村合作組織完全可以揚長避短,充分利用銀行的結算網絡、內部控制和風險管理體系,發揮自身植根鄉土、信息充分、管理簡便的獨特優勢。
無獨有偶,山東省2015年開展新型農村合作金融試點,也是不設“資金池”,存貸款由托管銀行來運作。這樣錢不經手合作社,保證安全。走了銀行的賬,也便于交易的計量和分紅。由于錢保持在銀行體系內部流轉,避免了農村金融的惡性競爭。這項改革,大約是山東有位“金融家”省長——郭樹清的緣故;要其最終成功,還需要一大批基層干部以及農民帶頭人的積極參與。
知所進退:供銷社前途在于“三位一體”
當年浙江的農村合作“三位一體”改革,本來是農業、金融和供銷社系統共同參與的。在瑞安試點成功、全省現場會召開之后,一些涉農部門的新舊矛盾加劇,有的采取了消極旁觀、甚至暗中抵制的態度,某些地方黨委政府領導無力駕馭改革局面、干脆是撒手不管。幾年下來,“三位一體”幾乎變成了供銷社一家的“獨角戲”,更加深了其他涉農部門的疑慮。一些地方的農辦、農業局或者供銷社,各自拉扯一個什么“合作社聯合會”或者“農合聯”,附屬于本部門,自己都不肯真心實意投入,主要想著套取政府資源,怎么可能取信于人呢?又怎么可能產生合作經濟的活力呢?
其實,“三位一體”進程的主導權,不能是自封的,也不是欽定的。涉農部門相互掣肘的阻力,也可以轉化為相互競爭的動力。從黨委政府的角度來說,駕馭改革,有如賽馬,要有共同目標,但不能事先規定名次。改革的目標模式和頂層設計力求清晰而堅定,改革的依靠力量和推動力量不能搞畫地為牢。
站在供銷社的角度,其行政優勢不如農業局,資金優勢不如銀行。但是,農業行政部門屬于公務員體制,沒有經營職能;農村合作銀行(信用社)作為金融機構也不允許混業經營。供銷社系統畢竟有現成的網絡體系、資產設施和人才隊伍,完全可以在“三位一體”進程中發揮重要的作用。但是,要其通過基層社在所有縣鄉都來主導這個進程,恐怕是勉為其難的。縣鄉基礎薄弱的供銷社,固然無能為力。那些經濟實力貌似雄厚的縣鄉供銷社,恰恰囿于商業上的既得利益,可能造成的阻力更大一些。
未來“三位一體”新型農協的實體重心,在縣鄉。縣鄉供銷社所能做的,是積極融入新型農協,從內部發揮影響乃至骨干、主導作用。“三位一體”新型農協必須超部門、跨部門。縣鄉供銷社只有把自己包容進去,才可能借助農協包容更多。這對于供銷社既是機遇,也是挑戰。供銷社要有脫胎換骨的決心,否則面臨生死存亡的考驗。
如果原來的基層社做不到這些,甚至連自身的生存都難以保證,那也無關宏旨,不要勞民傷財地按照舊有模式去重建什么基層社了,退一步海闊天空。各種“貼牌”的基層社,實際上是供銷社系統的巨大負擔,圖虛名而招實禍。
全國總社和省級聯社在架構上可以維持穩定,并展現開放姿態。對于新生的縣市級新型農協,一律吸收為成員。這就叫“有退有進、吐故納新、置換發展”。并在這個過程中,可以適當加強縱向的、垂直的領導或指導關系。照此下來,供銷社系統的版圖不會縮小、只會擴大。至于招牌字號,是否還叫供銷社,并不是最重要的。
總之,供銷社涉足金融的努力值得肯定,但是與其他銀行正面競爭并無優勢。我們給供銷社的建議是,積極參與、乃至化身于“三位一體”的農村合作組織,通過“三位一體”對接和引入金融資源和其他方面的資源,這樣有可能全盤皆活。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學法學院研究員,中央編譯局中國現實問題研究中心副主任、首席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