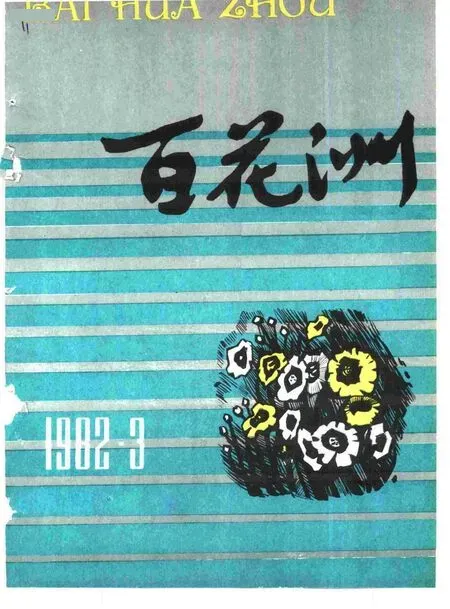甑子場(chǎng)寫意(四篇)
甑子場(chǎng)寫意(四篇)
踏著小說(shuō)的大道入場(chǎng)
邱華棟
從臺(tái)島返京待了兩天就到了洛帶古鎮(zhèn)。
說(shuō)是一路乘飛機(jī)、坐汽車幾千里到的,我卻認(rèn)為是踏著小說(shuō)的康莊大道一路走進(jìn)古鎮(zhèn)的。
這部小說(shuō)叫《甑子場(chǎng)》。
沿著一本小說(shuō)的文字走到一個(gè)去處去的經(jīng)歷我是有過(guò)的:沿著《喧嘩與騷動(dòng)》到過(guò)美國(guó)密西西比州北部“郵票般大小的故土”,沿著《巴黎圣母院》到過(guò)法國(guó)西堤島,沿著《日瓦戈醫(yī)生》到過(guò)莫斯科紅場(chǎng),沿著《老人與海》到過(guò)古巴海明威故址,沿著《紅高粱》到過(guò)膠東高密東北方向的幾處鎮(zhèn)街……
說(shuō)是到這些地方,實(shí)際上到的卻是虛構(gòu)與真實(shí)的模糊地帶、可疑地帯。模糊與可疑,正是策動(dòng)我腳步的理由。
據(jù)詩(shī)人凸凹講,他的長(zhǎng)篇小說(shuō)《甑子場(chǎng)》是以洛帶鎮(zhèn)的歷史地標(biāo)場(chǎng)景、傳奇故事和過(guò)去人物為原型創(chuàng)作的。因?yàn)檫@個(gè)原型的原因吧,洛帶鎮(zhèn)的街場(chǎng)甑子場(chǎng)就成為《甑子場(chǎng)》學(xué)術(shù)研討會(huì)的落地會(huì)址。
作為與會(huì)嘉賓,我們住進(jìn)了場(chǎng)鎮(zhèn)上的藝庫(kù)酒店,住了倆晚上。待在甑子場(chǎng)的兩三天時(shí)光里,我除了主持《甑子場(chǎng)》學(xué)術(shù)研討會(huì)這樁正事,大部分時(shí)間干的都是閑事:逛了清代遺物廣東會(huì)館、江西會(huì)館,空氣都帶水的濕地公園,各派建筑交集一處的博客小鎮(zhèn),客家博物館,川劇博物館,掛歷博物館,弘陶書院,人眾擠人眾店鋪連店鋪的老街,文軒連鎖書店;看了恍若天外之物的巨大無(wú)朋的客家土圍子,惜字如金的字庫(kù)塔,玻璃藝術(shù)展,女子龍舞,客家民俗歌舞,幽默搞笑的川戲;吃了供銷社飯店、藝庫(kù)伙食團(tuán)、哲學(xué)故事酒館等處的煙熏鴨、油燙鵝、雞樅菌、烏魚片、九斗碗、傷心涼粉等。
不想再敲鍵盤把這些雜七雜八林林總總的吃喝玩樂一一錄敘了,否則,成流水賬了。
別說(shuō),洛帶的多元文化還真有點(diǎn)流水賬的味道。聽凸凹講,洛帶有三國(guó)文化、古道文化、宗教文化、移民文化、碼頭文化、文人文化、山地文化、客家文化、建筑文化,以及囊括各地外來(lái)文化的“大客家文化”。除了詩(shī)人、小說(shuō)家、編劇,凸凹的身份辨識(shí)系統(tǒng)里還有本土文化專家一說(shuō)。
不管這文化那文化,在甑子場(chǎng),最能抓我身體官能和精神的,總是客家文化那部分,連街鋪上那些很民間的豆豉、豆瓣、豆腐乳、咸菜等客家吃食都讓我隨時(shí)生出買一大堆帶回北京的沖動(dòng)。
流連在甑子場(chǎng),眼睛東瞅西望,沒人知道我在看啥,其實(shí)我在滿街的游客縫里尤其老屋檐下尋找那些身著本地衣飾、吐納異族般口音的客家人,具體來(lái)說(shuō),就是尋找扣兒、安、魚兒、禾、蛋、象、烏、珍、雪兒、指導(dǎo)員、瞎眼算命人、師爺……對(duì)了,還有葉開喜歡的菜,還有至今失聯(lián)的馬。他們都是《甑子場(chǎng)》里的人物,都是在《甑子場(chǎng)》那個(gè)客家小鎮(zhèn)上出得氣、扒得飯、喝得酒,活得有生氣有故事的主兒。他們都去了,但他們的足印還應(yīng)留在場(chǎng)子上的,他們的聲音還應(yīng)走在空氣中的,他們的氣血還應(yīng)團(tuán)在光陰里的。
在甑子場(chǎng),我只與他們是熟人。踏上洛帶的土地,當(dāng)然要見他們。
遺憾的是,沒能見到。那天,我專門去叩訪他們。我冷得發(fā)抖,便返回酒店房間裹了厚衣,再行前往。但很快,紅日乍現(xiàn),陽(yáng)光抖擻起來(lái),燦燦爛爛。這是蜀犬吠日的地方少見的好天氣。但正因?yàn)檫@個(gè)無(wú)遮無(wú)攔一目千里的好天氣,那些行走在時(shí)間深處的氤氳隔面的人物,哪里還有他們的影兒呢?見這樣的角色,據(jù)說(shuō)要等到雨天,有輕風(fēng)、有薄霧的傍晚的雨天。
那天是圣誕節(jié)前夕。再過(guò)幾天,是洛帶的“解放日”12月27日。六十五年前的那天,洛帶還沒解放,還沒解放的洛帶居民真如《甑子場(chǎng)》描寫的那般一點(diǎn)感覺不到變天已然來(lái)臨?
在甑子場(chǎng),也沒見到女子茶社、六月茶社、鳳梧書院,也沒刨到要了安的命蛋的命的那兩粒“花生米”。誰(shuí)把它們收了去藏了起來(lái)?
看來(lái),還得來(lái)。
甑子場(chǎng)活動(dòng)結(jié)束,就該返京城的,但卻改簽了機(jī)票,飛去了西安。臨時(shí)接到的西安一個(gè)帶國(guó)際字眼的活動(dòng)邀約,改變了既定行程。這樣,甑子場(chǎng)之行,就變成了我打馬在兩個(gè)著名帝都之間的一次轉(zhuǎn)場(chǎng)、一回喂馬、一夜下榻。
去了甑子場(chǎng),再去,就不可能迷路了。甑子場(chǎng)就半臥在成都平原與龍泉山脈的交割線上。從山脈的這頭馳馬山脈的那頭,或從山脈的那頭縱馬山脈的這頭,都能一頭闖進(jìn)洛帶的場(chǎng)子里,讓安鋪設(shè)的青石板路,響起嘚嘚馬蹄聲。
之所以有馬的聯(lián)想,乃因?yàn)槿龂?guó)時(shí)期的甑子場(chǎng)外,是蜀權(quán)政權(quán)放牧軍馬的草場(chǎng)和生產(chǎn)皮革制品的基地。“男兒要當(dāng)死于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臥床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后漢書·馬援傳》)行走在“文出洛帶”這個(gè)地方,卻有一股子武烈的英雄氣浮升于周遭的氣場(chǎng)中,恐怕出處在這里了。
“一個(gè)作家能寫多少,能寫到什么高度,大致是有定數(shù)的。因?yàn)槊總€(gè)作家的寫作資源是有限的,不是無(wú)限的。凸凹這次是將自己的寫作資源用到了極致,寫出來(lái)了他的代表作—《甑子場(chǎng)》。我就是在看《甑子場(chǎng)》的時(shí)候,在腦子里浮現(xiàn)出‘四川小說(shuō)’的概念來(lái)的。阿來(lái)的小說(shuō),自然是一種‘四川小說(shuō)’。而《甑子場(chǎng)》,我看,也是典型的一種‘四川小說(shuō)’,也就說(shuō),小說(shuō)里天然地有擺龍門陣的味道,有豪俠氣、傳奇性,有歷史感,有一股子野氣,人物的命運(yùn)在歷史的深處起伏,這是一個(gè)江湖世界,人來(lái)人往,在演出一種活劇。這活劇中人物的命運(yùn)是最重要的。”這是我合上《甑子場(chǎng)》后,說(shuō)的幾句話。
甑子場(chǎng)到底有幾多資源,到底能提供給《甑子場(chǎng)》幾多資源,不實(shí)地勘察,我是懵然而無(wú)數(shù)的。
在旅游古鎮(zhèn)一夜間轟轟隆隆突然冒出遍布神州大地的今天,我是難得為一個(gè)鎮(zhèn)子寫字吆喝的,今天寫下的這兩千字,依然不是寫給旅游鎮(zhèn)的,而是寫給鄉(xiāng)野上的一處集鎮(zhèn)、一爿街場(chǎng),寫給《甑子場(chǎng)》與甑子場(chǎng)嚴(yán)絲合縫扣疊的那一部分。
終生為客
顧建平
最早知道“客家人”這個(gè)名詞,和“湖廣填四川”這段歷史,還是在中國(guó)的紅司令朱德《我的母親》一文中。
我家是佃農(nóng)。祖籍廣東韶關(guān),客籍人,在“湖廣填四川”時(shí)遷移四川儀隴縣馬鞍場(chǎng)。
為何要填四川?有史料記載是張獻(xiàn)忠在四川殺人如麻,婦孺不留,也有人說(shuō)是清兵鎮(zhèn)壓所致,清初統(tǒng)治者夸大其詞栽贓給張獻(xiàn)忠。但張獻(xiàn)忠在四川濫殺無(wú)辜,史籍記載在在皆是,肯定不是憑空捏造。近些年,四川屢屢發(fā)現(xiàn)新的萬(wàn)人坑,張獻(xiàn)忠屠四川又引起了歷史學(xué)家的研究興趣。
在成都近郊龍泉驛區(qū)洛帶古鎮(zhèn),我第一次感受到客家文化在四川的巨大存在。此前我對(duì)洛帶鎮(zhèn)的全部認(rèn)識(shí),都來(lái)自詩(shī)人成都凸凹的長(zhǎng)篇小說(shuō)《甑子場(chǎng)》,小說(shuō)中屢屢提到的會(huì)館,如今依然坐落在洛帶古鎮(zhèn)上。這里共有廣東會(huì)館、江西會(huì)館、湖廣會(huì)館、川北會(huì)館四大外地會(huì)館,還有客家博物館、客家公園,這里婚喪嫁娶的禮儀是客家風(fēng)格的,美味佳肴尤其豆腐菜是客家風(fēng)味的,說(shuō)的話依然是客家的詞匯和語(yǔ)音。
在洛帶鎮(zhèn)的廣東會(huì)館,東西墻上寫著一位名叫笑秋的人的兩首詩(shī):
豫閩粵川皆吾家,
勤耕苦讀勇開發(fā)。
鄉(xiāng)音無(wú)改東山下,
百里桃林香客茶。
這首是丘壑題壁的。另一首笑秋自撰自書:
嶺南尊我客,
客本中原根。
根育成材樹,
樹逢盛世春。
兩首詩(shī)言簡(jiǎn)意賅地記錄了客家人的歷史。細(xì)看兩邊墻上的字,書法相近,“丘壑”或許正是笑秋,這位笑秋本身也是居于西蜀東山下的客家人。
會(huì)館內(nèi)的柱子上的對(duì)聯(lián)也寓意頗深。我兼任著《中華辭賦》的總編輯,對(duì)詩(shī)詞楹聯(lián)有著本能的關(guān)注:
云水蒼茫,異地久棲巴子國(guó);
鄉(xiāng)關(guān)迢遞,歸舟欲上粵王臺(tái)。
另一幅:
江漢幾時(shí)清,且向新宮傾竹葉;
羅浮何處是,但逢明月問梅花。
家國(guó)之憂,故土之思,盡在這些文辭之中了。
我在北京讀書求學(xué)然后工作、娶妻生子,至今居京已經(jīng)三十一年了。前些年我跟父母開玩笑說(shuō),我現(xiàn)在在哪兒都是客人。在北京,因?yàn)槭堑谝淮本┤耍l(xiāng)音未改,行為做派跟北京“土著”或者第二、第三代北京人有明顯的區(qū)別。因?yàn)楸本┑陌菪裕卤本┤送耆梢圆还懿活櫪媳本┑娘L(fēng)俗禮節(jié),因此也不可能從內(nèi)心對(duì)北京產(chǎn)生歸屬感,美學(xué)上的故土詩(shī)意只是在瞬間涌現(xiàn)又瞬間消失。在我的家鄉(xiāng),雖然父母、兄姐、親朋居住在此,但父母已經(jīng)把偶爾回鄉(xiāng)的你當(dāng)作客人一樣對(duì)待。或許我今后的生活始終游離于我所居住的地域,在每一個(gè)地方都是客人,終生作客,終生都心系遠(yuǎn)方。
客家人本來(lái)居住在中原,后來(lái)遷徙到閩粵,再在明清之際填四川。起初視中原為故土,現(xiàn)在嶺南又成了鄉(xiāng)關(guān)。
一首著名的唐詩(shī),一直歸在賈島名下,也有人說(shuō)是貞元間詩(shī)人劉皂所作,詩(shī)句道出了人心中鄉(xiāng)情的微妙變化:
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yáng)。
無(wú)端更渡桑干水,卻望并州是故鄉(xiāng)。
其實(shí),我們從人類寄居于地球這一角度看,故土之思都是相對(duì)的。航天員在太空第一眼回看地球,對(duì)這個(gè)飄浮于太空中的藍(lán)色星球便會(huì)產(chǎn)生無(wú)限眷戀,對(duì)于人生困擾頓時(shí)釋然、達(dá)觀。李白《春夜宴從弟桃花園序》起句便說(shuō):
夫天地者萬(wàn)物之逆旅也,光陰者百代之過(guò)客也。
人生不過(guò)百年,安居不動(dòng)無(wú)以了解世界,飄浮無(wú)根則如云如絮不知所之。客家人千百年來(lái)從中原到東南,到西南,到東南亞,到世界各地,為了生存不停遷徙,但是語(yǔ)言習(xí)俗是客家人文化的根,走到哪里帶到哪里。客家人對(duì)自身傳統(tǒng)的珍視,也是對(duì)中華文化的珍視。我在洛帶感受到了歷史的厚重。
初冬時(shí)節(jié),洛帶的空氣中有四川盆地常見的潮濕清冷,早晨坐著電瓶車游覽洛帶濕地公園,看得到周圍忽聚忽散的薄霧,草地和樹葉上、水邊的蘆葦上,覆蓋著薄薄一層白色的霜。我在江南水鄉(xiāng)長(zhǎng)大,長(zhǎng)期羈旅京城,這薄霧這白霜已經(jīng)久違了,忍不住驚奇贊嘆。陪同我們游覽的一洛帶人隨口吟出詩(shī)句:“這就是《詩(shī)經(jīng)》里所說(shuō)的‘蒹葭蒼蒼,白露為霜’。”確實(shí),我已經(jīng)許久沒見過(guò)覆蓋著白霜的蘆葦了,為生計(jì)忙于奔走,離詩(shī)的世界越來(lái)越遠(yuǎn)。
新年初,中華辭賦雜志社在京主辦迎新春詩(shī)賦詠誦會(huì),我把《詩(shī)經(jīng)·國(guó)風(fēng)·秦風(fēng)》里的這首《蒹葭》選為詠誦篇目的第一首,潛意識(shí)中可能因?yàn)槟翘煸绯克姷降穆鍘竦兀驗(yàn)槲难棚L(fēng)趣隨口吟出詩(shī)句的那位洛帶人,因?yàn)榭图椅幕S盈的甑子場(chǎng),讓我重新體驗(yàn)到悠然思遠(yuǎn)的詩(shī)意情懷。
帶著晴天去洛帶
葉 開
2010年秋第一次來(lái)洛帶,就有一種親近感,那時(shí)不知是什么原因。
在古街上走,看人看風(fēng)景,吃一碗傷心米粉,是美好的記憶。傷心粉讓我額頭冒汗,貌似傷心,實(shí)際幸福。看天很藍(lán),看風(fēng)很軟,看女子很可人。洛帶女子溫和,不翻白眼,不扭捏,自然大方。這種分寸感,只有本鄉(xiāng)本土的悠久傳統(tǒng)才能孕養(yǎng)。她們是洛帶土地長(zhǎng)出來(lái)的,如那滿山的桃花,和山間的流水,不是很特意,但令人溫暖。
朋友們都說(shuō),成都很少能見到晴天。可是我兩次來(lái),天空都很干凈,能看出去很遠(yuǎn)。第一次淺嘗輒止,未嘗不好;這一次隨《甑子場(chǎng)》而來(lái),深入了解,更增添幾分好意。我跟朋友說(shuō),我到哪里都帶著晴天,這是天氣的好意,但也跟心情有關(guān)。在洛帶,適合開開心心、慢慢悠悠地閑逛。不要思慮太多,也不要太出世。在洛帶,要隨意,要平和。人世間的溫暖,并不需要做出一副猛烈的態(tài)度。為此,我寫了一首詩(shī)《帶著晴天去洛帶》:
來(lái)洛帶一定要帶著晴天
帶著一個(gè)人的夜晚
在驛路途中邂逅
十五年前的少年
來(lái)洛帶一定要有好心情
在江西會(huì)館喝茶
去龍泉山看看桃花
一遍遍開過(guò)了
又一層層地落下
來(lái)洛帶一定要成為詩(shī)人
吃一碗傷心米粉
涼拌千年歲月的火辣辣愛情
唐朝少女成長(zhǎng)在山旁水邊
客家兄弟兒女忽然成行
后來(lái)我明白為何有如此感受了,原來(lái)洛帶是客家人的聚居區(qū)。
我也是客家人。客家人與客家人天然相親,千百年來(lái)的漫長(zhǎng)遷徙歷史已進(jìn)入我們的血液,成為我們的基因,還因?yàn)槲覀冇泄餐恼Z(yǔ)言。在英文中,客家人、客家話叫作Hakka。客家人走到哪里都是客家人。據(jù)說(shuō)我們?cè)亲罴冋脑瓭h民,但這種最純正,因?yàn)闅v朝歷代避亂的遷徙,變成了一種非正宗,反而是五胡亂華之后的異族夷族,變成了那些地方的主流了。就這樣,客家人在自己的故鄉(xiāng)流浪。
這樣的遷徙,是為了躲避戰(zhàn)亂。另一方面也是主動(dòng)的,是客家人主動(dòng)尋找更安定、更美好生活的一種熱望在驅(qū)動(dòng)我們前行。在一百年前,甚至更早,客家人就漂洋過(guò)海,來(lái)到了世界的各個(gè)角落。客家人隨身帶著故鄉(xiāng),在哪里都能落地生根,在哪里都是原鄉(xiāng)人,又都是客家人。客家文化是洛帶的秘密之一,這種特殊的文化,讓洛帶具有特殊氣質(zhì)。我也因此知道洛帶女子大氣的原因了。客家女子不是密守閨閣的千金,她們是行走在土地上的精靈。
洛帶古鎮(zhèn)有一座廣東會(huì)館,是來(lái)自廣東的客家人建造的。要從一條中等寬度的巷子走進(jìn)去,在古色蒼蒼的墻頭上看到洛帶的天空。廣東會(huì)館保護(hù)完整,有宏大而沉靜的風(fēng)格,比一般的建筑也更疏朗、更大氣。不遠(yuǎn)處的江西會(huì)館,又是另一種風(fēng)格,磚瓦縝密、回廊安靜。
洛帶古鎮(zhèn)的客家博物館是一座福建土樓式建筑,里面收藏了很多珍貴的資料。近現(xiàn)代很多改變歷史走向的人物都是客家人。在近現(xiàn)代幾乎每一個(gè)關(guān)鍵的時(shí)刻,都有一個(gè)客家人出現(xiàn),力挽狂瀾。如鄧小平,也是客家人。他以特殊敏銳和寬闊的視野,打開國(guó)門,讓封閉三十年的中國(guó)出現(xiàn)在全世界面前,讓我們知道圍墻之外,還有如此廣大的世界。
客家人不僅有闖蕩的勇氣,有寬闊的視野,還有包容的心胸。
這是行走在中國(guó)大地的一個(gè)奇特的族群,他們的故土不斷搬遷,他們的文化一直蔓延。歐洲也有一個(gè)遷徙的民族,猶太人。可以說(shuō),猶太人就是歐洲的客家人。
客家人沒有自己的經(jīng)典,不像猶太人那么文化集中地體現(xiàn)在自己的經(jīng)書里。但客家人有對(duì)文化的特殊敬重。在洛帶古鎮(zhèn)的中樞,你可以看到重新修復(fù)的磚塔。不知道的會(huì)以為是小型浮屠,但這卻是一座客家人特有的字庫(kù)塔。洛帶朋友介紹說(shuō),客家人敬重文化,尊重文字,過(guò)去,他們會(huì)把所有寫著文字的紙張都搜集起來(lái),投于字庫(kù)塔里焚燒。
這種態(tài)度,讓客家人心目中的文化,成為一種類乎宗教般的情感。
從洛帶鎮(zhèn)到甑子場(chǎng)
蔣 藍(lán)
1999年,我結(jié)束了在成都幾個(gè)地方的租房歲月,終于在東郊十陵鎮(zhèn)買了一套住房,別人覺得距離市區(qū)偏遠(yuǎn),我慶幸這里清凈,只有蝴蝶、蟬和蜜蜂會(huì)打擾我,阿門。
我經(jīng)常出沒于菜市,與滿口客家方言的農(nóng)民討價(jià)還價(jià),一來(lái)二去,我才知道我居住的位置,就是客家東山五場(chǎng)的區(qū)域。東山五場(chǎng)為石板灘仁和場(chǎng)、清泉鎮(zhèn)廖家場(chǎng)、洛帶鎮(zhèn)甑子場(chǎng)、龍?zhí)端侣∨d場(chǎng)和西河場(chǎng),方言如包谷酒燒刀子一般凜冽、辛辣、回甘。一天因?yàn)槭虑榈R了,直到晚上八點(diǎn)才去菜市,還有兩個(gè)人守著菜攤子。他們說(shuō),我一直沒來(lái),所以他們等著。進(jìn)入初冬了,我想買生姜,農(nóng)民干脆讓我自己到地里去挖,價(jià)錢很公道。客家人的耿直,可見一斑。一來(lái)二去,我漸漸熟悉這個(gè)地名源自明太祖朱元璋之皇室家族陵墓群的地方。一條小河將社區(qū)隔開,水面的房影被電纜線維系,如同泡漲的風(fēng)箏。從樓頂遙望,我逐漸知道晚稻與玉米,陽(yáng)光下那厚薄不一的金黃。有時(shí),也有野鴨從水底竄出,從油菜花叢突然展翅騰空。
一天黃昏,我騎摩托車走老路來(lái)到洛帶鎮(zhèn)。那時(shí)的洛帶就像一個(gè)矗立在霧氣里的孤零零的舊夢(mèng)。無(wú)邊的小青瓦房、木頭門板,凸凹不平的石板路,就像進(jìn)入歷史的甬道。這里擁有蜀漢王族遺跡的宿地,團(tuán)聚四散的風(fēng)水,青草沾滿露水,蓬蔽了小道。我推想那時(shí)王侯的模樣,以及王妃曳地的衣裙,估計(jì)他們也將埋怨這淫濕的季候,難以頻繁踏春。將捂藏了很久的情事,不散熱地,在對(duì)方的身體上鋪開……
外面飄起了毛毛細(xì)雨,我坐在鎮(zhèn)門口的小酒館里喝羊肉湯,看那些一邊吃油炸胡豆一邊打紙牌的人。他們對(duì)桌子外的世界毫不關(guān)心,無(wú)論是呼嘯的中巴,還是女人甩牌時(shí),蕩過(guò)來(lái)的香氣。穿過(guò)石板路的腳印,總是一層又一層地覆蓋。各有各的心事,或者出走,或者買醉歸來(lái),但雨水改變著泥土的塑性。
我走到鎮(zhèn)口之外的夜幕里。自西而來(lái)的東風(fēng)渠,送來(lái)的卻是雪山的冷意,可以看見逆風(fēng)的柳樹,將那銀子的頭發(fā)高高拋直。細(xì)雨之后,夜空被洗亮了。龍泉山的高空,有干凈的星座,我聽見有人在嚶嚶哭泣,也聽見魚蹦躍的破水聲……
在這之后,我來(lái)洛帶的次數(shù),就像它的大規(guī)模翻修與轉(zhuǎn)身,頻率越來(lái)越高。洛帶鎮(zhèn)越來(lái)越現(xiàn)代化景觀化,甑子場(chǎng)越來(lái)越遙遠(yuǎn)和古舊,宛如一個(gè)沒來(lái)得及拆除的孑遺。一個(gè)地名的陰面與陽(yáng)面,似乎被一層石板隔開了。
2014年年底,我來(lái)洛帶參加作家凸凹長(zhǎng)篇小說(shuō)《甑子場(chǎng)》研討會(huì),凸凹是一個(gè)讓甑子場(chǎng)的石頭說(shuō)話的作家。在漢語(yǔ)詩(shī)界,詩(shī)人凸凹實(shí)至名歸。凸凹在外的名氣要大大高于在成都的魏平。凸凹數(shù)十年浸淫于詩(shī)歌,詩(shī)集連續(xù)出版,尤其是他詩(shī)作標(biāo)題里均帶有“或”字的命名,有棱有角,有點(diǎn)桀驁不馴、一峰獨(dú)立的意思。他的命名學(xué)里具有一個(gè)木工墨線式的向度:魏平—未平—凸凹。這容易理解。其實(shí),這當(dāng)中隱含了另外一個(gè)命名“偽平”—假裝平和、裝好好先生,他內(nèi)心裝滿了來(lái)自故土大巴山脈的石頭、巖鷹與塊壘,不用詩(shī)歌與燒酒猛力沖刷,就不容易露出崢嶸的頭角。
如果說(shuō)駕馭著“凸凹詩(shī)體”的凸凹,以大器晚成的淬煉和大氣,在圓熟的技法之上展示了詩(shī)者的獨(dú)立、自由向度,以及永無(wú)休止逼近事物本質(zhì)的勇氣,那么,著手于小說(shuō)的凸凹,還會(huì)變嗎?幾年前我注意到凸凹開始寫影視劇本、中短篇小說(shuō),比如詩(shī)事小說(shuō)《顏色》,他保持了一個(gè)詩(shī)人對(duì)文字的敬畏,更可貴之處還在于他把那些存留在記憶里的史料、往事、哀痛、血淚,毫無(wú)保留地交給了敘事。他試圖用超越現(xiàn)實(shí)的敘事方式,在對(duì)歷史經(jīng)驗(yàn)的提煉中,以嘲諷、暗喻來(lái)面對(duì)歷史、現(xiàn)實(shí)及未來(lái)世界的不可知和不確定。針對(duì)他新近推出的《甑子場(chǎng)》《大三線》兩部共近70萬(wàn)字的長(zhǎng)篇小說(shuō),著名作家、《人民文學(xué)》雜志副主編邱華棟認(rèn)為:“《甑子場(chǎng)》可以說(shuō)是一種帶有某種非虛構(gòu)色彩的新歷史小說(shuō)。在對(duì)歷史的撥云見日的探尋中,在對(duì)個(gè)體生命價(jià)值的追尋中,我看到了歷史的溫度和心跳。這樣的小說(shuō)是不多見的,屬于‘四川小說(shuō)’那宏大文脈的系統(tǒng),并拓展了這一文脈的空間,成為最新的一個(gè)收獲。”
我感興趣的還在于,小說(shuō)名字為什么不用洛帶鎮(zhèn),而是用甑子場(chǎng)。
“甑子”之名并非蜀地俗稱,而是古意盎然。用甑作炊具在黃帝時(shí)代就開始了。《廣韻·古史考》曰:“黃帝始作甑。”到戰(zhàn)國(guó)秦漢時(shí)期,甑子已遍及民間。《史記·項(xiàng)羽本紀(jì)》記述項(xiàng)羽的軍隊(duì)破釜沉舟之舉:“皆沉船,破釜甑,燒廬舍。”表明軍隊(duì)是用釜與甑作為炊具,不過(guò)最初的甑應(yīng)該是土陶制品,甑字的偏旁為“瓦”,可以為證。至于土陶甑的樣子,近年成都平原大舉出土的瓦器、陶器里,應(yīng)該有。
甑子場(chǎng)也作甄子場(chǎng)、鎮(zhèn)子場(chǎng),訛音所致。洛帶鎮(zhèn)在晚清時(shí)節(jié)就被稱作甑子場(chǎng),凸凹使用這個(gè)地名,目的在于彰顯小說(shuō)的場(chǎng)域,更靠近這一地緣。當(dāng)然,這個(gè)地名的來(lái)歷卻早在千年之前。我推測(cè),那一定是場(chǎng)口有幾家制作甑子出售的商販,為洛帶掙來(lái)了這個(gè)手藝的名頭。其實(shí),洛帶古鎮(zhèn)名字的由來(lái)有三個(gè)傳說(shuō),其中一個(gè)是:
洛帶鎮(zhèn)早名甑子場(chǎng)。場(chǎng)內(nèi)有一池塘,塘中有一八角井為海眼。井水為龍王口中所吐,味極甘甜,泡茶最好。井通東海,有鯉魚出沒,據(jù)說(shuō)肉味鮮美,食之可益壽延年。蜀漢太子阿斗聽說(shuō)了,擇一黃道吉日,率眾太監(jiān)來(lái)到甑子場(chǎng)八角井旁。但見一條條金色鯉魚穿石洞于水井和池塘間游進(jìn)游出,煞是可愛。太監(jiān)脫靴下得池來(lái),撲騰半日,終無(wú)斬獲,急煞阿斗。卻聞身后一聲叫好,一尺長(zhǎng)的大魚隨一白發(fā)老者釣竿甩動(dòng),劃一弧線,飛出井來(lái)。阿斗眼紅,老翁卻不賣。太監(jiān)動(dòng)手強(qiáng)搶。魚落阿斗手中而不甘,奮力擺尾,阿斗連人帶魚跌入池塘。魚兒穿石洞又游進(jìn)了八角井。阿斗得而復(fù)失,和衣跳入井中。那魚卻鉆進(jìn)海眼,回東海去也。阿斗被眾太監(jiān)拖起,忙亂中腰帶卻掉入井底。回頭欲找老翁算賬,已無(wú)人影,老翁坐釣處僅余一白綢帕,上書一詩(shī):“不思創(chuàng)業(yè)苦,孺子太荒唐。帶落八角井,帝運(yùn)終不昌。”阿斗臉色鐵青,揉亂綢帕擲于井中,堵住了海眼,井水從此變渾、變苦。后人遂改甑子場(chǎng)名為落帶鎮(zhèn),后來(lái)又嫌“落”不吉利,演變?yōu)槁鍘ф?zhèn)。
傳說(shuō)雖然附會(huì)極多,但洛帶鎮(zhèn)的“洛”,似乎也并沒有帶來(lái)多少好兆頭。甑子場(chǎng)的名頭并未消失,它在風(fēng)雨飄搖的晚清“咸魚大翻身”,紅燈閃爍揚(yáng)名立萬(wàn),這不是偶然的。
1902年年底,因?yàn)榕淹匠鲑u,來(lái)自石板灘的紅燈教女壇主廖觀音在甑子場(chǎng)不幸被威遠(yuǎn)前軍幫帶段方成抓獲,被急急解送成都,四川提督岑春煊感到終于除去了心頭大患。后來(lái)在提督衙門提審,1903年1月15日,才有了轟動(dòng)朝野的裸體斬首。隆冬時(shí)節(jié),那個(gè)在成都下蓮池出現(xiàn)的粉藕一般的身體,身首異處了。血,是那妖嬈的紅蓮花么?如果這樣的血尚沒能將甑子場(chǎng)的名頭凝固,那么凸凹的小說(shuō)《甑子場(chǎng)》,則讓民國(guó)時(shí)代一個(gè)女人與四個(gè)男人的糾葛,轟然讓甑子場(chǎng)的甑子,蒸煮出了一籠熱氣騰騰的人血饅頭。1950年7月,國(guó)民黨軍統(tǒng)特務(wù)、少將廖宗澤利用客家身份在甑子場(chǎng)糾集土匪劉幺胡子、一度向解放軍投誠(chéng)的劉倉(cāng)林等,成立成都、華陽(yáng)、新都、金堂、簡(jiǎn)陽(yáng)五縣反共救國(guó)委員會(huì)。月底,川西反共救國(guó)軍第六兵團(tuán)與劉倉(cāng)林部在石板灘暴亂,被人民政府鎮(zhèn)壓。1951年3月6日,廖宗澤被俘虜。值得注意的是,廖宗澤也是華陽(yáng)縣石板灘人氏(參見辛智:《廖宗澤其人》,《新都文史》第三輯,中國(guó)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huì)議四川省新都縣委員會(huì)文史資料委員會(huì),1986年版,第102—109頁(yè))。凸凹的《甑子場(chǎng)》,恰恰著眼于這一段刀鋒與火藥淬煉人性的歷史。
這讓我漸漸感到,這個(gè)甑子場(chǎng),分明就是一個(gè)祭壇。
2014年12月21日,即《甑子場(chǎng)》討論會(huì)當(dāng)天上午,我和與會(huì)作家們參觀了位于“中國(guó)藝庫(kù)”的系列博物館。在昔日青瓦白墻的洛帶鎮(zhèn)糧站倉(cāng)庫(kù),如今已改造成了博物館場(chǎng)地,成都?xì)v史上規(guī)模最大的一次掛歷展恰好在這里舉行。從最久遠(yuǎn)的來(lái)自1915年的掛歷,到難得一見的月份牌……題材涉及人文歷史、武俠文化、自然風(fēng)情等等,各式各樣的掛歷讓大家一飽眼福。洛帶鎮(zhèn)鎮(zhèn)長(zhǎng)雍峰對(duì)我說(shuō),這次掛歷展既是為中華武俠文化節(jié)而舉辦,更主要的是豐富成都市民的文化生活,展出的掛歷多達(dá)110個(gè)專題,1200多件。
掛歷博物館的水泥地面上,尚可看到巨大的美術(shù)字體的白色油漆標(biāo)語(yǔ):“積極行動(dòng)起來(lái),開展全力打擊黑惡勢(shì)力的專項(xiàng)斗爭(zhēng)!!!”“全區(qū)人民共同努力,建設(shè)和諧的……”從標(biāo)語(yǔ)成分來(lái)看,時(shí)間并不久遠(yuǎn)。但寫在水泥地板上,縱列十幾米長(zhǎng),昭示了昔日公家糧站的高昂斗志與激情,但是否起到了“避鼠”“鎮(zhèn)邪”“祛惡”的作用,就不得而知了。參觀的人流站在水泥地板上指點(diǎn)江山,我看到了收藏家宋廣福,他正在為參觀者講解外國(guó)掛歷的來(lái)歷與故事。“這次帶到成都來(lái)的掛歷,是從我收藏的2萬(wàn)多幅掛歷中精選出來(lái)的。”宋廣福一邊忙著整理掛歷,一邊告訴我,此次展出的掛歷包括祖國(guó)風(fēng)光、工藝美術(shù)、名家書畫等,為了助興武俠文化節(jié),武俠掛歷是其中的重點(diǎn),隨后他向我們展示了“水滸故事”、“中國(guó)功夫明星”的掛歷。
如果說(shuō),掛歷收藏就是收藏時(shí)光的形象,那么在洛帶鎮(zhèn),我逐漸感覺到,古鎮(zhèn)不像從西洋舶來(lái)的掛歷,它其實(shí)是一個(gè)老皇歷,要用一種外道者聽不懂的方言,才可能讀得懂它的滄桑與妙曼蜂腰。
從糧站博物館出來(lái),新開工的建筑工地翻出的土地一如凝血。我看見墻后有幾株楓樹,按理說(shuō)早應(yīng)凋零了,奇怪的是它們的樹葉依然火紅,微風(fēng)一起,抱成一團(tuán)。紅楓是美麗的觀葉樹種,其葉形優(yōu)美,紅色鮮艷持久,枝序整齊,層次分明,錯(cuò)落有致,樹姿美觀,宜布置在草坪中央,高大建筑物前后、角隅等地,紅葉綠樹相映成趣。幾個(gè)攝影家在拼命搶鏡頭,就像在抓拍接吻的美女。我想,嶺南人多數(shù)都要敬九黎族的首領(lǐng)蚩尤,或吹牛角,或敬楓神。楓神來(lái)源于蚩尤被殺,他的木枷丟在自己的地界上,長(zhǎng)出大片楓樹……
美目盼兮的人置身這樣的土地,自然要落帶。我的確感受到甑子場(chǎng)的蒸騰血?dú)狻?/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