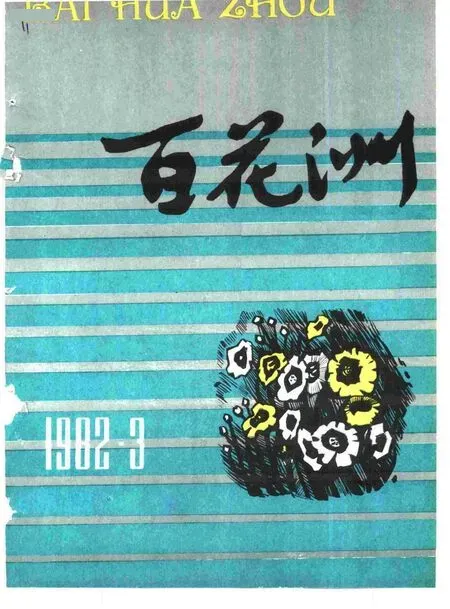終生為客
顧建平
最早知道“客家人”這個名詞,和“湖廣填四川”這段歷史,還是在中國的紅司令朱德《我的母親》一文中。
我家是佃農。祖籍廣東韶關,客籍人,在“湖廣填四川”時遷移四川儀隴縣馬鞍場。
為何要填四川?有史料記載是張獻忠在四川殺人如麻,婦孺不留,也有人說是清兵鎮壓所致,清初統治者夸大其詞栽贓給張獻忠。但張獻忠在四川濫殺無辜,史籍記載在在皆是,肯定不是憑空捏造。近些年,四川屢屢發現新的萬人坑,張獻忠屠四川又引起了歷史學家的研究興趣。
在成都近郊龍泉驛區洛帶古鎮,我第一次感受到客家文化在四川的巨大存在。此前我對洛帶鎮的全部認識,都來自詩人成都凸凹的長篇小說《甑子場》,小說中屢屢提到的會館,如今依然坐落在洛帶古鎮上。這里共有廣東會館、江西會館、湖廣會館、川北會館四大外地會館,還有客家博物館、客家公園,這里婚喪嫁娶的禮儀是客家風格的,美味佳肴尤其豆腐菜是客家風味的,說的話依然是客家的詞匯和語音。
在洛帶鎮的廣東會館,東西墻上寫著一位名叫笑秋的人的兩首詩:
豫閩粵川皆吾家,
勤耕苦讀勇開發。
鄉音無改東山下,
百里桃林香客茶。
這首是丘壑題壁的。另一首笑秋自撰自書:
嶺南尊我客,
客本中原根。
根育成材樹,
樹逢盛世春。
兩首詩言簡意賅地記錄了客家人的歷史。細看兩邊墻上的字,書法相近,“丘壑”或許正是笑秋,這位笑秋本身也是居于西蜀東山下的客家人。
會館內的柱子上的對聯也寓意頗深。我兼任著《中華辭賦》的總編輯,對詩詞楹聯有著本能的關注:
云水蒼茫,異地久棲巴子國;
鄉關迢遞,歸舟欲上粵王臺。
另一幅:
江漢幾時清,且向新宮傾竹葉;
羅浮何處是,但逢明月問梅花。
家國之憂,故土之思,盡在這些文辭之中了。
我在北京讀書求學然后工作、娶妻生子,至今居京已經三十一年了。前些年我跟父母開玩笑說,我現在在哪兒都是客人。在北京,因為是第一代北京人,鄉音未改,行為做派跟北京“土著”或者第二、第三代北京人有明顯的區別。因為北京的包容性,新北京人完全可以不管不顧老北京的風俗禮節,因此也不可能從內心對北京產生歸屬感,美學上的故土詩意只是在瞬間涌現又瞬間消失。在我的家鄉,雖然父母、兄姐、親朋居住在此,但父母已經把偶爾回鄉的你當作客人一樣對待。或許我今后的生活始終游離于我所居住的地域,在每一個地方都是客人,終生作客,終生都心系遠方。
客家人本來居住在中原,后來遷徙到閩粵,再在明清之際填四川。起初視中原為故土,現在嶺南又成了鄉關。
一首著名的唐詩,一直歸在賈島名下,也有人說是貞元間詩人劉皂所作,詩句道出了人心中鄉情的微妙變化:
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
無端更渡桑干水,卻望并州是故鄉。
其實,我們從人類寄居于地球這一角度看,故土之思都是相對的。航天員在太空第一眼回看地球,對這個飄浮于太空中的藍色星球便會產生無限眷戀,對于人生困擾頓時釋然、達觀。李白《春夜宴從弟桃花園序》起句便說: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也,光陰者百代之過客也。
人生不過百年,安居不動無以了解世界,飄浮無根則如云如絮不知所之。客家人千百年來從中原到東南,到西南,到東南亞,到世界各地,為了生存不停遷徙,但是語言習俗是客家人文化的根,走到哪里帶到哪里。客家人對自身傳統的珍視,也是對中華文化的珍視。我在洛帶感受到了歷史的厚重。
初冬時節,洛帶的空氣中有四川盆地常見的潮濕清冷,早晨坐著電瓶車游覽洛帶濕地公園,看得到周圍忽聚忽散的薄霧,草地和樹葉上、水邊的蘆葦上,覆蓋著薄薄一層白色的霜。我在江南水鄉長大,長期羈旅京城,這薄霧這白霜已經久違了,忍不住驚奇贊嘆。陪同我們游覽的一洛帶人隨口吟出詩句:“這就是《詩經》里所說的‘蒹葭蒼蒼,白露為霜’。”確實,我已經許久沒見過覆蓋著白霜的蘆葦了,為生計忙于奔走,離詩的世界越來越遠。
新年初,中華辭賦雜志社在京主辦迎新春詩賦詠誦會,我把《詩經·國風·秦風》里的這首《蒹葭》選為詠誦篇目的第一首,潛意識中可能因為那天早晨所見到的洛帶濕地,因為文雅風趣隨口吟出詩句的那位洛帶人,因為客家文化豐盈的甑子場,讓我重新體驗到悠然思遠的詩意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