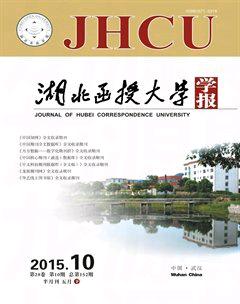一首現代悲劇的挽歌——論《逃離》的悲劇美
王敏
[摘要]愛麗絲·門羅的短篇小說集《逃離》,所寫的八篇小說旨在述說著女性的故事,反映的內容是小地方的普通女性,折射著她們在平凡生活中的悲劇命運。本文主要從審美的悲劇性角度探析《逃離》中表征的女性形象的悲劇意味,特點以及背后的形成機制,進而更深刻理解門羅的思想情懷。
[關鍵詞]《逃離》;愛麗絲·門羅;悲劇性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5918(2015)10-0176-02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5.10-083
[本刊網址]http://www.hbxb.net
一、逃離束縛——悲劇性的表現
按照舍勒對悲劇性的界定:“‘悲劇性首先是我們在各種事件、命運和性格等等本身察覺到的一種特征,這些事件、命運和性格的意義就是其存在。”《逃離》中的那些平凡瑣碎的事件以及在女性身上所體現的命運和性格的意義匯集成悲劇性的表現,體現著審美的悲劇性。
這株暗淡的微光,常常在讓人難以察覺之際便已滲入人心。正如門羅所言:“現實生活本身是太平凡了,普通人在普通地方過著普通生活,從來沒有驚心動魄的意外發生,也沒有緊張曲折的事件發展。”但這就是生活所傳達的真諦,通過八篇小說的書寫賦予全書濃濃地悲劇氣息,流溢在那些女性周身的內在性格以及冥冥之中的命運,全部外化為一種想要逃離束縛的悲劇性沖動。
《逃離》的八篇故事均以女性為第一主人公,在這部合集中,門羅以極其細膩的筆觸描繪出一群帶著無限的猶豫、無奈、惆悵的女性,因對現實生活不滿而想要逃離的愿望,展現出女性特有的思維方式與精神狀態。在這一過程中,悲劇性以其特有的模態展現出來。開篇的第一個小故事《逃離》主要講述女主人公卡拉沒有選擇讀大學反而和一個男人——克拉克離家出走,以教馬術為生,因克拉克脾氣火爆,卡拉萌生逃離克拉克的想法,在鄰居賈米森太太的幫助下出逃,然而,在大巴車上,卡拉突然覺得她的生活已然和克拉克連在一起,跳下大巴重新奔回克拉克的懷抱。卡拉在此所做地逃離到頭來竟是一種悲劇性的回歸。
這次頗為滑稽的逃離事件在最初卡拉的意識中化為羊水,用盡全力仍誕生不出健全的新生活。因此,在悲劇性事件中直接地——不假思索,未作任何抽象的或其他方式的“說明”——和某種世界性質迎面相遇。這就注定卡拉無法逃離,被一種無形的悲劇性裹挾渾渾噩噩只能如此。
二、人性之美——悲劇性的特點
在愛麗絲·門羅的這八篇小說中,體現出女性生存的悲劇。正是悲劇性特點的共在支撐著女性生存的意義。其共在體現為悲劇性事件的本質特征:示范性和不可避免性。
(一)示范性
示范性,既是個體的,拘囿于自身的悲劇性事件小中見大地體現了我們世界的一種本質特征。在《逃離》中具體表現為人物生存的空間及人物自身的性格。
1.人物生存的空間
在門羅的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她筆下的空間既是神奇變換的而又充滿著流動地生命力。“在1973年,門羅告訴吉爾·格爾迪納在她最初開始寫作的時候,她認為場景比人物更重要”。在《逃離》的八篇小說中,開篇均將女主人公拋入一定的空間場景中,然后隨著不同空間的轉換,整個故事舒展開來。開篇的第一個小故事《逃離》中,“在汽車還沒有翻過小山——附近的人都把這稍稍隆起的土堆稱為小山——的頂部時,卡拉就已經聽到聲音了。”對女主人公卡拉出場的空間,并沒有進行夸大或特殊性處理,讀者旋即被帶入故事的空間中。伴隨著與卡拉有親密關系的人物克拉克與賈米森太太悉數登場時,均帶著各自的生活空間,以人物為載體的空間多維的揭示了卡拉最后選擇“逃離”的悲劇性。“這些看似支離破碎的敘述其實是通過不同的空間,如‘網絡、‘商店等被牢固地捆在一起,結構平穩,使讀者感受到整體的空間視角。”卡拉生活在這樣一個單調乏味的空間中,加之生活的平淡如水,加劇了她想要逃離的美好愿景,然而也正因為這樣使她慘烈地與“悲劇性”迎面相撞。
福柯曾指出,“空間被當作是死寂的、固定的、非辯證的、不動的。相反地,時間是豐富的、多產、生命、辯證的。”因此時空的二元對立關系就映射了男/女的二元對立關系,女性通常被定義為是空間性的,“空間則被編碼為具有女性氣質的、女人的。”5門羅的小說移動是核心,在她的小說中空間不停地轉變刻畫出一個個多面的女性角色,她們的生命體驗在空間中朝著不同的面向而展開,因此拘囿于自身的悲劇性在各異的空間中,小中見大的呈現出悲劇性的“示范性”特點。
2.人物自身性格
《逃離》中的八篇小說,其中三篇有關聯共享一個女主人公以外,一共出現六位女性。彰顯出門羅在刻畫人物之時的文筆細膩,對人物的精心雕琢使形象深入人心。不同于以往的“性格決定命運”的悲劇觀,門羅筆下的不同女性,雖然性格不同命運各異,但在其中卻有著相通的性格內核——沖動。在性格所帶有的“瑕疵”中這些女性的命運注定具有悲劇色彩。
《機緣》、《匆匆》、《沉寂》三個短篇故事講述一個名為朱麗葉的女子因沖動而離家出走,在一所學校任代課教師期滿之后,出于某種莫名的沖動搭乘火車去多倫多看望一個男人,而這個男人就是日后與之一起生活的漁夫埃里克。朱麗葉性格中的沖動成分牽引著她的行為,在一步步的驅使之下,使她走向悲劇性的深淵。在尋求自己的感情時,她甚至都沒有想好漁夫埃里克是否是自己與之共度一生的男人,就糊里糊涂地生活著,包括女兒的出生。而這個女兒簡直就是朱麗葉的寫照,表征出朱麗葉從小與父母關系的不和諧。女兒即是翻版的朱麗葉,她遭到同樣的對待,與女兒之間的不睦,導致女兒逃離她的束縛,遠走他鄉另嫁他人。
性格中的“沖動”是正常的一種成分,它會讓我們思考做事更加積極而富有激情,但是這種沖動必須在合理適度的范圍之內,而不能僭越成為性格中的主導,當這種“沖動”達到一定程度,并且宰制一切之時,必然具有悲劇色彩。endprint
(二)不可避免性
“悲劇性事件始終以一種世界結構為基礎。無論事件起因多么特殊,無論因果序列多么偶然,這種世界結構總是不斷地‘窺伺機會,準備從自身繁衍出新的‘此類事件來。因此,悲劇性事件就具有了它的另一本質特征“不可避免性”,盡管上述的“窺伺機會”可以被直覺預感。”
在第六篇小說《侵犯》中,勞蓮是艾琳和哈里的親生女兒,卻因一個女人德爾芬的闖入,而開始懷疑自己是否為父母的親生。原來艾琳和哈里曾經以為自己不可以再生育,從德爾芬那里領養了一個嬰兒,不久艾琳竟然也懷孕了,在一次吵架中,艾琳的莽撞,將領養來的嬰兒摔出車筐后當場死亡,艾琳生下自己的孩子勞蓮。那個領養孩子的母親德爾芬多年之后尋找自己的孩子,以為勞蓮就是自己曾經放棄的孩子。整個故事具有悲劇性色彩,故事中即使沒有德爾芬的出現,還會有其它別人出現,尋找曾經丟棄的孩子。因為艾琳與哈里領養了一個孩子,這是一個不可避免的事實。無辜的嬰兒即使不是被摔死,也會為別的原因而死,故事中只能有一個孩子,勞蓮頂替了領養的孩子,后者只有唯一的一條宿命——死亡,這同樣也不可避免。
三、內外兼具——悲劇性的成因
門羅所熟悉的全部,她的安大略西南部猶如福克納的約克納帕塔法,在其中作品里的人物,一個個鮮活地躍然紙上,正因為地區的局限,得以使思考的深入,對小鎮女子的關注滲入到每一個毛孔之下,探析《逃離》所產生悲劇性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兩點:
(一)“女性”身份的焦慮
生于1931年的安大略省,長期居住于荒僻寧靜之地,逐漸形成以城郊小鎮平凡女子的生活為主題,那些主人公是我們身邊所熟悉的人物,她們經歷出生與死亡、結婚與離異,滲透著泥土芳香的文字背后,是門羅對女性成長的疼痛的熱切關注與女性這一特殊身份的深深焦慮。
尤其在早期的作品中,“女主人公的經歷往往就是她自身體驗的投射:一個出身貧寒的鄉下少女,以偏遠的安大略西南部小鎮為起點,懷揣著夢想和抱負,一心勇往直前,到頭來卻發現自己并不清楚目標是什么,所謂的堅強在迷惘中幻化為焦慮和失落。”《逃離》中的卡拉以及《激情》中的格雷絲,她們都是淳樸的女孩,在她們的身上門羅投去了無以復加地關注。無論是門羅還是她作品中的女性都生活在一定的社會權力關系之中,作為女性對立面的男性,在西方傳統的以男性為主導的控制下,大多數的作品站在男性的視角,俯瞰女性及其周圍的一切。在作品中,伴隨女主人公出場的總是有那么一位或幾位男性。男性并不是門羅關注的重點,她將全部的恩寵給予女性。這是她借以逃離男性注視之下的必由之路,然而這些人物的悲劇性在她的思索中就早已注定。
拉斯帕里克在《性別之舞》中認為,門羅“以女性主義者的探究方式操縱了地域空間,從而成功地展現了一個虛構的女性世界”。相比較而言,門羅作品中女性的內心世界更加豐富而敏感,她們經常會孤獨地生活在自己的內心世界里,被自己的幻覺激動和迷惑,甚至忘掉現實和幻覺之間的距離,把現實當作幻覺,用幻覺來對待現實。
(二)背景環境的影響
二十世紀60年代,國際政治形勢和加拿大本國的形式都出現了有利于婦女運動發生、發展的趨勢。隨著歐美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進入經濟高速發展的“黃金時期”加拿大的經濟也出現高漲的局面,為婦女提供了更多的就業機會。但婦女的社會地位提高沒有提高,仍然受到兩性不平等的待遇和性別歧視。婦女內心隱秘的狀況仍無法公開在大庭廣眾之下,因此門羅對婦女投去了深切關注的目光。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