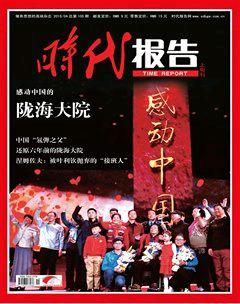李克強總理興允添把柴的“創客”
邱楊


2015年1月4日,李克強總理考察了深圳柴火創客空間,在體驗了年輕“創客”們的創意產品后,稱贊他們說,你們的奇思妙想和豐富成果,充分展示了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活力。這種活力和創造,將會成為中國經濟未來增長的不熄引擎。創客們希望總理能成為柴火創客的榮譽會員,李克強欣然應答:“好,我再為你們添把柴!”
在那幾天播放的電視畫面中,一個為總理比劃著進行介紹的年輕人很引人注目。他就是矽遞科技(Seeed Studio)和柴火創客空間的創始人潘昊。
展覽的啟示
站在華強北路和深南中路的交匯路口向北看去,高高低低鱗次櫛比的商場沿著街道密集地向遠方延伸,商場間的狹窄縫隙被并肩接踵的人流填滿。20多家大型電子商場和30萬~50萬人次的日客流量匯集在這里,形成了中國最大的電子市場——華強北。走進任意一家商場,密密匝匝不規則排列的玻璃柜臺就像迷宮般涌入視野,展示著各種型號各式規格的電子元器件。人們在狹窄的過道里忙著打包裝箱,憋悶的空氣里彌漫著電子器件特有的淡淡焦臭味。
電子元器件是智能硬件產品的標準配件,無論一部手機、一款掃地機器人、一副智能眼睛,乃至一輛電動汽車,都離不開一個東西——電路板,所有的指令在這里匯集,所有的信息依靠這個傳輸。傳統制造業中,一款產品往往需要從零做起。但現在,有了互聯網和開源技術的支撐,一款產品的誕生已經不再需要從零起步,只要你有一個好的創意,來到中國制造業前沿的華強北,你需要的電路板都能夠在一天時間內找到。潘昊抓住了這個機會,與其讓每一個創客費勁從元器件做起,不如干脆給他們提供標準元器件,由此大大節省了創客們制造一款產品的時間和成本。
看到華強北的第一眼,潘昊就決定留在深圳。他立刻給北京的朋友打電話:“把我的行李寄過來。”在這里,電子市場的規模、人們做事的效率和市場里烏煙瘴氣熙熙攘攘的一切都讓他震驚。“就像狂熱的廚師來到超級市場,這里有全世界的食材,唯一限制你的就是你的想象力。”如今已經是矽遞科技公司總裁的潘昊,回憶起7年前的這一幕,眼睛仍會發光。2008年6月18日,改變他人生軌跡的這一天,恰好是他的25歲生日。
彼時的潘昊,剛剛掙扎著熬過他人生中最彷徨苦悶的一段時光。“當時最大的痛苦是沒有方向,不知道接下來要做什么。”在潘昊看來,自己過去25年的履歷太雜,不像是一個有邏輯的職場人。
出生在四川雅安的一個大學職工家庭,父母給了潘昊極其寬松的成長環境。“我從小就喜歡拆東西,他們不會阻止我,只要求我拆完一定要裝回去。”在有機可乘時,潘昊開始壯著膽子去拆更大的機器,成功修好后父母的表揚是極大的鼓勵。初中時,雅安城里開始流行起電腦吧,雖然沒有聯網,但電腦強大的功能和神秘的程序依然激起了少年狂熱的好奇心。“沒有足夠的零花錢,就看別人玩,一看就是一個通宵。”1997年,潘昊擁有了屬于自己的第一臺電腦。“嘗試各種軟件,使勁琢磨升級和改裝,甚至還嘗試做過一個電腦點歌系統。如果有小伙伴裝電腦不找我,我就覺得他瞧不起我。”高中時互聯網開始普及,潘昊在網絡的世界里盡情“撒野”。“家里寬帶網用量特別高,網絡中心甚至找到我爸,問你家孩子是在上傳病毒嗎?”
當所有人都以為潘昊必然會報計算機專業時,他卻鬼使神差地去了重慶大學電子系。“我對電腦屏幕背后的東西更感興趣,特別想知道這些電路板意味著什么,怎樣用零件把它做出來。”當年極為熱門的計算機專業,在有個性的潘昊看來不夠有意思。“現在回想起來,這是一個很幸運的選擇,大學是真正把我塑造成一個Maker(創客)的過程。”因為在這里,潘昊有足夠多的機會參加各種學科競賽,嘗試新事物。“機器人比賽、電子設計競賽……全年級幾乎一半的獎都被我們班拿了,而我們班一半的獎都被我拿了。”
正是在準備各種競賽的過程中,潘昊第一次接觸到電子元器件市場。“那時候還沒有淘寶,我們只能去重慶電子市場買,但規模很小,很多零件只能直接打電話給工廠,但對方一聽是學生想買一兩個做實驗用就立馬把電話掛了。”更讓潘昊郁悶的是,辛苦做出來的成果,或者被當成展覽品在展室里積灰,或者被拆除只為了重復利用某些零部件。“沒有積淀和分享的過程,更不要說產品化。”
大學畢業時潘昊有機會保送浙江大學讀研究生,但他卻一心想去英特爾公司做研發。本科生的學歷加上電子專業,在那一年招聘中并沒有合適的職位,他最終沒能如愿。“面試官說成都有一個新開的芯片組工廠,問我愿不愿意去試一下。”學的是研發,卻要去做更傳統、更后端的制造工作,此時的潘昊不是不糾結,但最終還是妥協了,成為英特爾成都工廠的產品工程師,負責CPU芯片組硅片半導體的封端和測試。
這份在很多人看來體面的工作,卻很快讓潘昊感到無聊。“半年后我就開始掙扎,腦海里反復出現‘溫水煮青蛙這句話。公司里做到經理職位最快需要7年,這條路徑是可以預期的,一步一步熬年頭獲得你期許的東西。”在潘昊眼里這種生活讓人絕望。“沒有驚喜,沒有自由探索的空間。我想如果現在不出去,以后就更出不去了。”事實上,此時的潘昊已經在公司里帶十幾人的團隊,也是同批入職者中唯一一個獲得“exceed excellence”(超優)評價的人。
辭職后的潘昊來到北京中關村尋找機會。“這里幾乎滿地都是互聯網公司,而我的背景很奇怪,學電子,又去做制造,以至于大公司不想要我,小公司我不想去。”陰差陽錯,潘昊去了一家蒙古國的貿易公司當“大中華區總裁”。“因為全中國只有我一個員工,從公司注冊到采購物流甚至搬運都是我一個人做。”剛到北京時,潘昊住在東王莊朋友家,后來搬去朝陽區,為了節省房費,還住過半年辦公室。“在北京的生活很孤獨,連送水、送包裹的人來了我都使勁想跟人家多聊兩句。”在24歲本命年時,潘昊離開了這家公司。
接下來的兩三個月,潘昊過得特別壓抑。“從小到大父母老師告訴我的都是從A點到B點,考一個好大學,去一個好公司,工作買房結婚,讓你的孩子再循環這樣的路。但我的這條路斷了,沒有人告訴我該干什么。”
從義烏批發小商品去賣以維持生計的同時,潘昊一直在尋找創業機會。機緣巧合下在中國美術館看到的全國第一屆新媒體展覽,就像一根火柴,照亮了潘昊那段混沌晦暗的人生。“藝術家們用自動控制微處理器做出很多裝置,讓電子成為藝術。過去我認為電子技術是很專業的,要經過很多年才能做出產品。但這些甚至根本不懂單片機工作原理的藝術家們都能夠做出電子藝術品,我想其實我們的門檻應該更低,我們的技術本來就應該是平民化的。”
華強北的機會
這場不期而遇的展覽引導潘昊從此進入了一個全新的世界:創客、開源硬件和Arduino論壇。“創客是一個努力把各種創意轉變為現實的群體,而開源硬件則是他們實現創意的方式。在Arduino論壇上,創客們可以找到與發明相關的一切圖紙、設計文件和Arduino電路板配套軟件。”這一切讓潘昊感到興奮。“這意味著任何人都可以依葫蘆畫瓢。對于開發者來說,無需再從零開始,接著開源內容改進即可。而對于使用者來說,缺乏專業背景的人也可以擺脫束縛,更直接地造物,滿足自己的需求。”
在接觸創客和開源硬件的過程中,潘昊敏銳地嗅到了其中的商機。“創客們造物的過程中需要很多個性化的電子元器件設備,但在國外買很貴,或者根本買不到。”潘昊開始嘗試在論壇上發帖,為創客們搜羅這些小眾的電子元器件,并通過開源硬件的方式進行升級改造。“沒想到訂單一個接著一個。”潘昊驚訝于原來有那么多創客的造物需求得不到滿足,而這恰恰成就了他的生存空間。
2008年6月18日,當潘昊第一次站在華強北的地界上,他更強烈地意識到:“創客這個人群的開源硬件需求,在華強北可以做成。”揣著轉租得來的幾千塊錢,潘昊從北京南下深圳,開始成為最早將電子技術市場與創客世界對接的人。跟著他一起創業的還有大學同學的弟弟繆建國,兩人在深圳前海金岸租了一間70平方米的“高級農民房”,開啟創業模式。
“雖然我是學電子出身,但剛來華強北時,這里90%的電子元器件我都不認識。”這對潘昊來說是很大的打擊。每天上午在租住的房子里處理完訂單后,他就拿著筆記本背起背包,坐半小時的公交車來到華強北熟悉市場,弄清楚這里出售的每一個元件。“剛開始大家都不理我,一看就不像是大客戶,到后來我就穿著襯衣去提貨。剛開始砍價時底氣不足,后來就變得很霸氣,兩句話對方就知道你懂行。”
潘昊花了將近3個月才漸漸摸清華強北的門道。“這里絕大多數都是所謂的二道販子,你必須學會如何跟他們打交道。如果你使勁壓價,他們給你的貨肯定是假的,只有仔細拿捏給他們合適的利潤,才能在低價的同時保證貨品質量,慢慢找到好的供應商長期合作。”
“由于深圳靠近香港物流便利,華強北絕大多數都是現貨交易。談好價格,說明數量,貨銀兩訖,生意就做成了。”潘昊對這里簡單直接的交易風格印象深刻。“不像在北京,買一兩個元器件往往還要和店主聊上半天,才能在一兩天后調到貨品。”潘昊始終認為,開源電子元件的市場能迅速開拓,與深圳所處的地利有極深的淵源。
“事實上,最開始對于這個小眾市場的前景,我并沒有什么判斷,完全是興趣加生存促使我們開始進入這個跨界的領域,只要能持續獲得訂單讓我們能夠活下去就夠了。”在潘昊眼里,創業初期雖然艱辛,但至少心里是踏實的。他詼諧地把自己比作灰姑娘:“下午5點華強北市場關門的時間是道坎,如果5點回不來就只能等到8點。因為我們經常有很多貨物,需要等著包車,有時候還下著大雨,你只能等著。”回家的路上,潘昊常常順道把菜買了,繆建國做飯他洗碗,飯后繼續工作。“那時候算是最艱難的時期,累得實在不行了就在沙發上歪一會兒,有時甚至眼前一黑暈過去,被急忙送往醫院。”
2009年注冊公司時,潘昊為公司取名為Seeed Studio(矽遞科技有限公司)。“就像是一顆象征著電子器件(Electronics)的種子(Seed),矽遞扮演著促進這顆種子生長的角色。”潘昊和小伙伴也從前海金岸70平方米的“蝸居”搬到了山東大廈110平方米的“辦公室”。“5個人擠在一個大房間里,直到有第一個女員工前,我們幾個大老爺們都是穿著內褲辦公。”大家做好了艱苦奮斗三五年的心理準備,但由于踩準了一個空白的市場機會點,矽遞的發展出乎意料地順利。“我們的訂單一直都在波動上升,這個市場跟著我們一起在成長。第一年每個月的業務都在增長,到第二、三、四年,業務增長率基本維持在200%~300%,甚至更高。”
傳統產業鏈的活水
深圳南山區的新圍石嶺工業區8棟,坐著唯一一部貨運電梯上到5樓,便來到了矽遞科技有限公司現在的辦公場所。前臺墻面上鋪滿了用電路板做成的展示牌,并不寬敞的辦公平臺上錯落有致地分布著各大部門,一張張年輕的臉上朝氣蓬勃。如今的矽遞已經是國內最大、全球前三的開源硬件制造商,為全世界5萬多創客和發明家提供傳感器、控制、通信等超過700種開源硬件模塊。
開源硬件模塊仍然是矽遞最核心的業務。去年矽遞的營業額達到將近一個億,但接到的訂單仍有大部分是小訂單。穿戴好特制的防靜電服,下到4樓,便來到了矽遞專門針對小規模、小批量生產需求的敏捷制造中心。在這里,最常見的訂單量就在20至100片之間。“對于傳統的工業供應鏈來說,這樣少的訂單量幾乎無法完成,因為開模具的成本太高。但是現在,依靠3D打印機和標準配件的組合,生產50片中心模塊,是一件既省時又省力的工作。”在潘昊看來,未來的工業生產,應該是去中心化的,偏向定制化與個性化。“傳統的大規模生產,依賴于前期的設計、制模、生產線,是一種自上而下的生產方式,智慧的源頭在前端,越往后技術含量就越低。未來的供應鏈應該變短、變小,技術含量是平均分配的。”
除了開源硬件模塊外,矽遞現在還提供產品化和小批量生產服務,幫創客們把產品賣到全世界。潘昊將矽遞定位為“為創客服務的創客”,最早通過產業鏈的整合,讓創客在這里一站式把所有事情搞定。“我們既是創客的上游,也是他們的下游。我們就像一個超級市場,創客就像來這里買菜的廚師,他們不必因為想吃牛肉就去養一頭牛,只需要把配方交給我們,由我們來幫他炒菜。”潘昊透露,硬件項目以前從概念到成熟,為期7至8年,而實現開源后,平均在2至3年內即可商業化。
“這幾年產品化和小批量生產服務的比重越來越高。但我們的客戶一直以國外居多,國內客戶前幾年不到1%,前年5%,去年不超過10%。”潘昊不無遺憾地說,“比起硅谷的團隊,國內的創客們還是慢,談得多、做得少,做出硬件的就更少。大家太渴望如同互聯網那樣的成功,以至于總是觀望,等著國外創客成功后才開始做。”“柴火空間”是矽遞創辦的創客俱樂部,供創客們“折騰”和“嘚瑟”。“我們在這個市場里太孤獨了。”潘昊希望通過柴火空間把創客精神和生態系統聚集起來,“今年1月李克強總理來參觀后,柴火空間本身形成的馬太效應更加明顯。”
事實上,隨著創客群體的不斷壯大,矽遞就像一汪活水注入傳統電子制造業市場,進而深刻改變著傳統工業生產的供應鏈。“創客不是一個獨立的產業,甚至不是一個產業,它其實是一種跨界的方法。”在潘昊看來,“創客市場容量持續增大,每一個增量都與傳統產業的對接密切相關。”矽遞的上游是各類電子技術公司,如因特爾、MTK、聯發科等,他們的傳統是將技術和關鍵零部件服務于諸如蘋果、TCL這樣的大公司。而矽遞實際上是在大型電子公司和創客間架起了一座橋梁,把原廠的新鮮技術更快地轉化成開源硬件提供給創客。“很多大公司主動找上門來想跟我們合作。”這是潘昊沒想到的,“富士康公司以前連1KK的訂單都不做,現在卻愿意接10K左右的訂單。”越來越多的模仿者和競爭者也在涌入這片藍海。“目前在行業內,我們尚沒有一個旗鼓相當的對手,最大的競爭者還是我們自己。”潘昊自信,“這個市場本身非常開放,合作大于競爭,現在每一家為創客服務的公司我們都傾向于把它看成合作者,我們一起服務于這個行業才能圓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