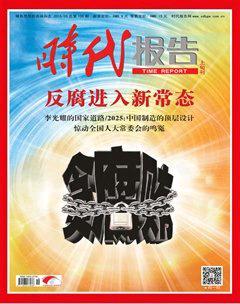“新文化之子”帶給我們什么
董海燕
“他完全秉承了百年新文化運動的神脈,發揚光大了民主與科學精神。在這兩個領域,以其自覺的領承,不僅忠實繼承了新文化運動的初始精神,而且將之融入了中國歷史變遷過程,從而以自己的理念與行動,成為新文化頗具標志意義的當代傳人。”在對《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一書的脈絡梳理中,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任劍濤寫下這樣的文字。
建國初期,文字改革被提上日程。這一天,毛主席到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問:為啥不能用漢字筆畫式的字母?一片寂靜,沒人敢犯顏直諫。毛主席又問:周先生怎么看待這個問題?周有光嘴上沉默,卻筆耕不輟,先后發表了《字母的故事》《什么是民族形式》等作品,不斷“科普”拉丁字母,隨之,拼音逐漸被人們接受,并在周有光的推介下走向世界。
2015年,時間走到了“新文化運動”發軔百年這個重大節點上,這一年年初,漢語拼音之父周有光度過了他人生的第110個年頭。
作為一場偉大的思想、文化和社會變革,新文化運動引發了關于中國現代化的思想、道路和理論的激烈爭論。百年之際,新文化運動對國人的精神世界帶來了怎樣的撼動,“新文化運動當初提倡的種種目標到底實現了沒有?”……成為人們愈加關心的話題。
在不斷的反思與回望中,一個人的身影從歷史深處清晰起來。
在任劍濤看來,《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一書所記載的,遠不止一個人的瑣屑經歷與心路歷程。近百年中國轉型跌宕起伏、波詭云譎的歷史,才是這部書的大內涵所在。正是這樣的內涵,引導人們看到書外去,看到作者所處的大歷史位置:周有光乃“新文化之子”。
在任劍濤《百年新文化脈絡中的周有光》一文中,他將周有光一生做出的兩大貢獻做出了獨有的判斷:“他以自己對現代語文的精深研究和語文改革的實際參與,讓科學精神落定在社會生活之中,模范實踐了新文化運動凸顯的科學精神;他以自己晚近階段對民主政治的不懈吁求,讓人們清醒地意識到現代民主對中國政治發展的不可廢弛與推進必要。這兩個重要貢獻,也只有在百年新文化脈絡中才能得到深刻理解。”
從1949年中國文字改革協會成立,到1958年方案正式公布,漢語拼音方案經過了近10年的反復論證。“國際化”還是“民族形式”?一部分人認為,民族形式就要根據漢字形式創造的、與漢字有一定聯系的拼音字母。但周有光和絕大部分人主張采用拉丁字母作為漢語拼音字母,他在《什么是民族形式》一文指出,民族形式主要表現在語言上,文字形式是另一回事。改革文字并非改革語言,如果新的書寫符號體系能更好地服務于漢語,那只會鞏固民族形式,而無損于民族形式。
周有光思路的延展過程被學者們評價為閃爍著“世界公民”的思想,然而追根溯源,在他波瀾壯闊的人生際遇中,對民主與科學的執著應是他精神世界的奠基。
85歲那年,這位“現代漢語拼音之父”離開辦公室,回到家中,遠離專業的“深井”之后,周有光的目光再次聚焦在對歷史、文化的反思以及對民主與科學精神的追求上。周有光《百歲新稿》的特聘編輯張森根在《周有光和他的精神世界》一文中,將晚年周有光的思想追求做了剖解:“科學的一元性”,即科學是世界性的,一元的,沒有東西方之分的。任何科學,都是全人類長時間共同積累起來的智慧結晶,經得起公開論證、公開實驗、公開查核,要用“實踐”“實驗”“實證”來測定,不服從“強權即公理”的指令。“雙文化論”,即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傳統文化,但是,任何民族都無法離開、取代、覆蓋全世界的現代文化。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長期并存,互有消長,彼此不可能把對方吃掉。傳統文化都在自動適應,自我完善,自我代謝。“三分法”,即文化從神學思維到玄學思維到科學思維,經濟從農業化到工業化到資訊化;政治從神權統治到君權統治(專制)到民權統治(民主)。“世界各國都在這同一條歷史跑道上競走,中國不是例外。審視中國在這條跑道上已經達到什么程度,是每一個知識分子的歷史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