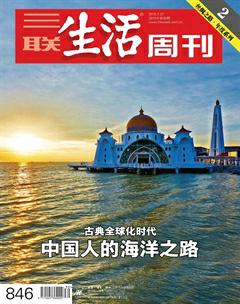從廣州出發,中國人駕船出海
朱步沖

太古倉碼頭,是廣州近現代對外貿易和港口運輸的重要歷史遺跡

南海神廟碼頭遺址
南海神廟:從蕃鬼到神祇
7月初的廣州天氣暑熱難當,雖然黃浦區穗東街已經算是郊區,但氣溫與市中心相比基本一樣,并不算寬敞的珠江航道從此流過,江邊是熱鬧非凡的黃埔電廠工地。站在南海神廟那塊歲月斑駁的“海波不揚”的正門石牌坊下,很難想象1400年前,這里海天一線、百舸爭流的壯觀場景。工作人員告訴我們,自從宋代之后,圩田開墾,海岸線因淤積而不斷南移,進出廣州的船只逐漸改行琶洲一帶水面。不過就在正門石牌坊前,還保留著一處清代碼頭考古遺址,證明昔日此處曾經船行魚貫的繁榮。
在神廟正門附近,是數株樹齡在百年以上的老榕樹,樹丫上滿是當地人祈福的愿簽與金箔元寶,樹下還有幾名當地退休老人,以粵劇清唱自娛自樂。不過南海神廟本身的歷史,比這幾株垂垂老矣的榕樹還要悠久得多,最早可以追溯到隋代開皇十四年(594),時年隋文帝下旨,于浙江會稽縣建東海神廟;廣州南海建南海神廟,南海神,其實即為祝融,祝融本為火神,而古人認為“火之本在水”,故祝融兼水、火神于一體。廟址所在,為古扶胥鎮,位于珠江北岸,面臨扶胥江,東連獅子洋,下接虎門,背靠廣州:“去海不過百步,向來風濤萬頃,岸臨不測之淵。”
“唐朝天寶十年,玄宗還特地派使節前來冊封南海之神為‘南海廣利洪圣昭順威顯王,把南海神的地位不斷提高,排在東海神前面,在海神河伯之上,反映了隋唐以來,海上絲綢之路貿易的繁盛,以及各朝代政府對于海路經濟貿易的倚重。”廣州文物博物館學會會長程存潔告訴我們,到了唐代中期,這條始自漢武帝的南海道,被正式冠名為“廣州通夷海道”,包括頭門東側的碑亭內唐代使持節袁州諸軍事、袁州刺史韓愈撰文的《南海神廣利王廟碑》在內的諸多碑刻,都賦予了南海神作為海上絲綢之路貿易庇護之神的重要作用。

廣州文物博物館學會會長程存潔
唐代以廣州為起點的海上絲路,在賈耽的《廣州通夷海道》中記載得最為詳細,他把從廣州起航前往今日波斯灣港口巴士拉的航線稱為東線,這一旅程要經過大約3個月的海上航行,并詳細記錄了途經的港口與國家,包括環王國(占城,越南中部)、門毒(越南歸仁)、羅越國(馬來半島南端)、佛逝國(印尼蘇門答臘東南部)、獅子國(斯里蘭卡)、天竺(印度南部),最終抵達未羅(巴士拉)。隨后又以倒敘法,詳細記載了自東非經紅海,繞過阿拉伯半島至巴士拉的西線航路,途徑三蘭國(坦桑尼亞)、設國(也門席赫爾)等地,按照航行時間來看,唐代航海技術較之兩漢魏晉之際,有了顯著提高,昔日從雷州半島至黃支國的海上航路需要一年之久,而在唐代則只需要大約51天。
唐宋之際,正是廣州作為海上絲路最重要的始發港與貿易集散地的黃金時代。文獻形容其繁榮程度可謂“舶交海中,不知其數”,“蠻聲喧野史,海邑潤朝臺”。曾多次因商貿旅行訪問廣州的阿拉伯商人蘇萊曼·丹吉爾曾在其游記中說,寓居在廣州的阿拉伯、波斯以及東南亞各國商人總計達到12萬人。在當地人口中,南海神廟被俗稱為“波羅廟”。清人屈大均在《廣東新語》里記載說:“舟往來者,必祗謁祝融,酹酒波羅之樹,乃敢揚風鼓舵以涉不測。”根據工作人員介紹說,“波羅”一名的來源為民間傳說,據說唐朝時,古波羅國(婆羅門)有個來華朝貢使,當其海舶抵達廣州扶胥江時,登岸拜謁南海神,并將其從國內帶來的兩顆波羅樹種子種在廟內,因其十分迷戀廟中的景致,流連忘返,以致耽誤了回去的海船,于是他只能望海悲傷。今日,不僅寺廟內外遍布著樹齡古老、果實累累的菠蘿蜜樹,而且在在神廟儀門廊下的東側,我們也見到了這尊俗名“番鬼望波羅”、被敕封為“助利侯達奚司空”的神像。他面部黝黑,深目高鼻,有絡腮胡須,身穿宋代官府璞頭,舉左手于額前做遙望之態,傳說其自成神之后,在海上經常輔助遠渡重洋的外國商人船舶免于風濤之害,每當海上“裂風雷雨之變”,誦念其名,天氣就會驟然轉為晴霽,“舟行萬里如過席上”。
而在南海神廟大殿里,南海神像兩廂的“六侯”中,除了這位助利侯達奚司空,出身化外而又被本土民眾神化供奉的還有一位順應侯巡海蒲提點使,雖然衣袍容顏已經完全漢化,但據傳其民間形象最早出于北宋元祐五年(1090),為一名僑居廣州的阿拉伯蒲姓商人。
從史籍中我們得知,蒲氏,原為居住在占城國的阿拉伯人,后入籍中國,客居廣州,12世紀末遷居泉州。蒲氏在廣州富甲一時,飲食起居可謂富比王侯,極盡奢侈,每日進餐開筵時,室內必用沉香、冰腦、薔露水等名貴香料熏香。堂屋中有四棵大柱,是由名貴沉香木雕成,其后蒲氏有一支舉家遷往泉州,蒲壽庚于景炎元年(1276)得以升任泉州市舶司,以亦官亦商的身份“擅蕃舶利者三十年”。直至今日,泉州等地蒲氏子孫亦有部分從事制香業,開有“玉蘭堂香室”等老字號。
出南海神廟正門西北方向不到百米,就是章丘崗,上有一座亭臺名為浴日亭。宋時浴日亭所在的章丘崗三面環水,江水直拍小崗腳,是羊城觀日出之最佳位置。小丘四周尚有海蝕遺跡,在浴日亭章丘崗的山腳下,環繞矗立著十幾座形制古拙的明代神道石人石獸,歲月的侵蝕讓它們的外表已經斑駁不堪,青苔遍布,工作人員告訴我們,這批石人石獸原本并非在此,而是移自上世紀70年代在廣州姚家崗東山寺附近發掘的明代市舶司太監韋眷墓地。
根據《番禹縣志》和殘存的永泰寺碑記可知,成化十二年到弘治元年,韋眷曾任廣東市舶司的監督太監。市舶司,是中國自唐代至明代,中央政府于東南沿海港口城市設立的海外貿易管理官僚機構。明代的市舶司,不僅要查驗各海外屬國前來朝貢貿易的“勘合”證明,也要對進口私人貿易貨物抽取進口稅。
明代正德年間之后,由于政府持續的財政危機,不得不對海外貿易進行“弛禁”,力圖將其變為財政收入的正常組成部分,從中漁利。正如兩廣巡撫林富于嘉靖八年七月在《請通市舶疏》中指出的那樣,對番舶朝貢之外的私人貿易貨物進行抽稅有數種好處,包括兩廣“用兵連年”,可以借此籌餉,發放官員俸祿,也可以藏富于民,興旺經濟(輾轉交易,可以自肥)。到了萬歷年間,廣東市舶提舉司每年征收的進口商品稅收已經達到銀4萬余兩。
除了士大夫官僚出身的市舶司提舉使,明廷在這個機構中照例安插了宦官,擔任市舶提舉太監,進行監督,實際攫取了市舶司的絕對權力,“內官總貨,提舉官吏唯領簿而已”。因身為明憲宗寵妃萬貴妃倚重的宦官梁芳的黨羽,韋眷獲得了這樣一個位高權重的“肥缺”,中飽私囊,濫收中外貢使私商賄賂甚至侵吞他人財物。
韋眷墓室,后在清初三藩之亂中被盜掘,上世紀70年代,考古人員在被洗劫一空的墓室發現了一枚威尼斯銀幣以及兩枚孟加拉銀幣,分別為15世紀中葉威尼斯總督帕斯夸爾·馬利皮埃羅所督鑄,以及同期孟加拉國培克巴沙所制。根據《明史·天方傳》記載,成化二十三年,阿拉伯使者阿立從滿剌加行至廣州,攜帶“巨寶數萬”,試圖入京朝貢,然而這批價值不菲的財物引起了韋眷的覬覦,他先是設計侵奪了阿立所攜帶的巨額財物,然后又行賄至北京內廷,顛倒黑白,指認阿立為間諜,圖謀不軌,將其逐出廣州,這三枚銀幣,亦可能來自韋氏侵吞阿立進貢的珍奇。
南越王朝——富庶的背影
廣東人說起本省水運與航海之便利,便有八字諺語,所謂“一江來水,八門出海”。這里兼有優良的季風氣候,自3月至8月,自西向南的風向在南海海面上占據60%以上,來自阿拉伯半島乃至東南亞的風帆船舶,每年夏季借助西南季風駛來廣東,進而北上前往寧波、泉州,以及日本琉球、長崎等地,冬季又借助西北季風原路返回,北宋人朱彧在《萍州可談》中,就談道:“舶船去以十一月,十二月,就北風,來五月,六月,就南風。”并指出廣東當地百姓與海上船戶,稱季風為“舶趠風”,蘇軾即以此為名賦詩,有“三時已斷黃梅雨,萬里初來舶趠風”之句。作為省會所在與東西北三江匯集之地,廣州更是得天獨厚:閩西、贛南的外銷陶瓷、絲貨、茶葉沿東江而來,湖湘之地的絲茶沿北江運至,滇黔川桂等地的錦繡、糧食、木材則順西江,匯集至廣州。
有了如此天時地利,廣州作為中外海上交通貿易樞紐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漢時代。在市中心中山四路的車水馬龍之間,香火繚繞的城隍廟之旁,靜靜地坐落著南越王宮署遺址博物館,自1974年首次發掘以來,在此先后發現了宮殿基址、園林廊道、宮城城墻、園林池渠等遺址。博物館一層,即為開放性參觀的園林遺址。
“從出土的南越王宮園林遺址的形制和文物來看,可以證明廣州早在公元前2世紀,就跟東南亞等國家地區通過海上溝通,有了頻繁的商業和貿易往來。”博物館館長全洪告訴我們,首先,這片王宮園林的建筑方法,就與中原核心地區的宮室院落截然不同。“這種石構水池和曲流石渠整體皆為石構的建筑方法,在我國秦漢時期的王家苑囿中尚屬首見。兩處遺跡中還有不少以石為材的造景,如石構水池的池壁用石板呈冰裂紋狀密縫鋪砌,疊石柱和八棱石柱也能在古埃及、兩河流域和古希臘的不少遺址中見到,這就不排除建筑形制是受海外影響的可能。”
在博物館二層的文物陳列室里,我們還看到了幾塊出土的帶釉磚和筒瓦,釉彩為青灰色,有細碎的開片,在燈光下散發出一種宛如玻璃的質感與光彩,全洪說,根據中國科學院上海硅酸鹽研究所古陶瓷研究中心的鑒定,這種釉被稱為“堿釉”,也來自同時代的中亞與波斯地區。而在距離這些磚瓦不遠的陳列柜里,還有十余件于遺址南漢文化層中出土的藍釉器殘片。藍釉,又被稱為孔雀釉或者波斯藍釉,從藍釉器殘片的造型、花紋、釉色和陶質等看,都與在福州市五代十國閩國王延鈞妻劉華墓中出土的施孔雀藍釉大陶瓶相似。

左:南越王宮署遺址博物館一層展出的開放性參觀的園林遺址右上:廣州南越王墓出土的波斯銀盒(上)和紅梅乳香右下:南越王宮署遺址博物館展出的波斯藍釉陶片
這些出自遙遠國度的珍寶,是如何漂洋過海,輾轉來到廣州的?在宮署博物館一側,還有一方不起眼的回填考古探坑,在這座規模宏大的宮室發現之前,考古工作人員在此找到了一處時代綿延秦漢兩朝的造船設施遺跡,若按照遺址所出土造船臺的尺寸,并參考其他漢代陶船模的比例,可推算當時所造船只的長度可達20米左右,載重約25~30噸。其形制,根據廣州其他西漢墓葬出土的陶制船模推測,可能已經擁有多個艙室,上有甲板與帆、櫓、舵、瞭望臺等設施,具備了在內河乃至近海長期航行的能力。嶺南地區造船業的發達,在兩漢之后也依舊存在:三國孫吳政權黃武五年(265),孫權將合浦、蒼梧、南海、郁林四郡為廣州,“以舟楫為輿馬,以海島為夷瘐”,專門負責督造船舶的官位“建安典船校尉”,最大船名“舡”舶,萬震在《南州異物志》中記載,這種大型船舶可能長達二三十丈,船體建筑最高距離水面兩三丈,最多可乘坐六七百人,載重量達到“萬斛”,前后擁有4張可以活動的巨帆,以適應來自不同方向的風力。
根據史籍記載,南越國由于三面臨海,坐擁海運交通之利,加之嶺南地區物產豐富,所以迅速富甲一方,《晉書·吳隱傳》即稱廣州“負山帶海,珍異所出,一筐之物,可資數世”。距離南越王宮遺址不到10分鐘車程,就是解放北路。1983年,在這里的象崗山發現了南越第二代國王,文帝趙昧的陵墓。在這個占地100平方米的“早”字形大墓中,考古工作人員曾發現了多件價值連城的舶來隨葬珍品,包括焊珠金花泡掛飾以及一件銀盒。掛飾為半圓形,焊有金絲圖案和小型珠,而銀盒表面有錘揲而成的蒜頭式紋樣,以及鎏金的穗狀紋帶,帶有濃郁的波斯藝術風格,與漢代中原流行的金屬器物迥然相異。
與這件銀盒一同出土的,還有4件銅質熏爐。博物館館長吳凌云告訴我們,當時在一件豆形熏爐中,考古工作人員還發現了一堆灰粒與碳狀香料殘存,而在另一件漆盒內,發現了大約26克乳香。乳香,為乳香樹滲出的樹膠與樹脂凝結而成,可用于熏香,也可入藥,亦被稱為“薰陸”,譯自梵語“Kunduru”,意為“香”,在《三國志·魏志》、《后漢書·西域傳》曾被提到。這一批乳香遺存的發現,證明產自中亞、阿拉伯的外國香料與熏香風俗在西漢時,就經過海路,從今日蘇門答臘中轉,進入我國。
隨著海路運輸進入廣州的,不僅有來自各國的珍寶與其他獨特物產:新中國成立以來,在廣州農林下路、三育路等兩漢墓葬中,考古工作人員不斷出土了形態各異的“托燈胡俑”,在今日廣東省與廣州市博物館中,就可看到這些陶俑的原件或者復制品,他們頭頂或手托燈盤,造型深目高鼻,寬鼻厚唇,胡須濃密,赤腳纏頭,與其他各地漢墓出土的陶俑截然不同,即通過海上絲綢之路由南海道輾轉販運至此的外族奴婢,可能為中亞與波斯人。東漢人楊孚曾在《異物志》中記載,嶺南之地富豪權貴家中即以豢養“瓷人”以為炫富,這些外來人“齒及目甚鮮白”,面部與皮膚“異黑若漆”,“為奴婢,強勞力”。
海上絲綢之路,在唐宋之際,逐漸演化為陶瓷與絲綢并行輸出,部分原因即是因為拜占庭帝國終于通過中亞陸路絲路習得養蠶制絲技術。在廣東省博物館三層的陶瓷館中,展示有數量豐富的外銷瓷器。迄今為止,發現的廣東唐代陶瓷窯址共有28處,包括廣州西村窯、湛江雷州窯以及新會官沖窯等。程存潔告訴我們,在瓷器變為大宗出口海外產品之后,需求劇增,然而瓷器脆弱易碎,從嶺北、中原運至廣州,數量受限,損耗極高。于是唐宋以降,廣東外銷瓷生產業逐漸興旺,制造水平亦逐漸與中原平齊,以西村窯為例,在中后期已能仿制眾多名窯的典型瓷器,如越窯青瓷、耀州窯青釉雕花、景德鎮白瓷、磁州窯彩繪瓷等。
1556年,葡萄牙傳教士克魯士曾經來中國游歷,于其游記《中國志》中提及,廣州“市場上形形色色琳瑯滿目的瓷器有些極粗糙,有些極細致,有些公開出售是非法的,比如紅色、綠色、涂金和黃色的,因為它們只能供官員們使用,出售瓷器最大的市場在城門附近,兩旁是兩層樓的木質建筑,有帶頂的通道,每家商鋪都在門口有一張巨大的牌子,詳細寫明他們出售的貨物種類”。

廣州伊斯蘭教協會副會長、懷圣寺負責人王官雪阿訇

矗立在蕃坊中心的懷圣寺光塔
西來的信仰——佛寺與光塔
兩漢魏晉南北朝期間,隨著海上絲路的開通,佛教信仰傳入中國,不少海外高僧取道海路來到中國弘法,而中國佛教僧人亦西行求法,絡繹不絕。位于越秀區光孝路上的光孝寺,就是這一段歷史的見證,根據寺志記載,這里最早是南越國第五代王趙建德王府,三國時又為騎都尉、江東名士虞翻講學的“虞苑”,后改建為佛寺。寺院中迄今可見訶子、菩提等參天古木,廣州民間有諺語“未有廣州,先有光孝”,光孝寺大殿據說為罽賓國僧人曇摩耶舍來到廣州傳教時所建,后歷代都有重修,清代更擴建至七開間,但依舊保持了南宋時期建筑抬梁與穿斗式結合梁架、三跳華拱、出檐夸張的風格。直至唐代,在該寺傳教譯經的有印度高僧求那羅跋陀三藏、智藥三藏、達摩禪師、波羅末陀三藏、般剌密諦三藏等,《金剛般若經》、《楞嚴經》等著名佛教經典的譯文,皆始于光孝寺,唐儀鳳元年(676),禪宗六祖慧能在此削發受戒,開創佛教禪宗南派。
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港與東亞海運貿易的中心港口,廣州亦是各種文化與宗教信仰交融的中心,據說早在唐代貞觀初年,伊斯蘭教創始人穆罕默德即派遣使節前往唐朝傳教。這段軼聞史事,在中國古代文獻中缺乏明確記載,但有阿拉伯文獻指出,628年,一批阿拉伯人從麥地那城港口乘船出發,由海道來到廣州,給當時的中國皇帝呈上了來自穆罕默德的信件,中國皇帝“很友好地接待了他們,表示對他們的神學觀點很感興趣,還幫助他們為僑居廣州的阿拉伯商人建立了一座清真寺”。
直至今日,許多廣州本地穆斯林都相信,這座清真寺,就是今日位于越秀區光塔路上的懷圣寺。寺中有一座高達36.3米的光塔,這座宣禮塔用青磚砌筑,表層涂抹灰沙,南北各開一門,塔內有兩道螺旋狀樓梯,繞塔心盤旋而上,直通塔頂。廣州伊斯蘭教協會副會長、懷圣寺負責人王官雪阿訇告訴我們,近年來文物考古單位對光塔年代進行過勘測,根據從塔身上部磚塊取樣進行年代測定,斷代可以追溯到唐代。
根據文獻記載,在唐宋兩代的農歷四五月,蕃舶乘季風而來的貿易旺季,塔上每天有蕃客專人定時登塔:“嘀晰號呼,以祈南風。”光塔的修建,一則便于宣禮,二則便于導航,歷史上光塔頂部曾建有用于測定風向的風信金雞,可惜在1387年被颶風吹毀,以后塔頂改用銅鑄葫蘆,但不久又墜于風,加上隨著珠江航道南移,以及水羅盤等導航技術的普遍,其后再無重裝,日漸失去導航作用,則專注于禮拜宣禮。
今日的光塔路,除了懷圣寺周圍的一些清真飲食商店之外,只是一條外表毫無異常之處的街巷。在唐宋時期,這里卻是繁華富麗、外國蕃客聚集的蕃坊。程存潔告訴我們,唐代蕃坊的大概疆域,即是以今日光塔為中心,南至惠福路,東至米市路,朝天路為界,西至人民中路,北至中山六路,根據遺存至今少數文獻資料,蕃坊的建筑形制與唐宋時期其他大城市別無二致,每個坊四周都設有正方形或者長方形的垣墻,建筑樣式也應該傾向于阿拉伯與波斯風格,貨棧店鋪靡集,所謂“戎頭龍腦鋪,關口象牙堆”,為了便于管理外國居民,唐宋蕃坊內還建制了蕃坊司,在外僑中選舉“蕃長”,負責處理各種事務和邀請外商貿易。《萍洲可談》中記載了大量廣州蕃坊及穆斯林活動的情況。“廣州蕃坊,蕃人衣裝與華異,飲食與華同。或云其先波巡嘗事瞿曇氏,受戒勿食豬肉。至今蕃人但不食豬肉而已。”

清真寺內眾多國內外穆斯林前來禱告
阿拉伯學者麥斯歐迪在《黃金草原和珠璣寶藏》中這樣描繪廣州:“廣府是一座大城市,位于一條大河的岸上,這條大河是流入中國海的。城與海之間,相距六七日的途程。”從巴士拉、西拉夫、阿曼、印度各城市、桑夫群島和其他國家的船只,載運各種商品開進這條大河,一直開到廣府附近。廣府城人煙稠密,僅僅統計伊斯蘭教人、基督教人、猶太教人和祆教徒就有20萬人。在麇集此地的蕃客中,信奉伊斯蘭教的阿拉伯商人居多,正如《嶺外代答》中所述:“諸蕃國之富盛多寶貨者,莫若大食國。”前來廣州的海舶蕃商遠較唐朝為多,其強大可以從稅收方面體現出來。1077年,廣州所收購的乳香,占杭州、明州、廣州三市舶司收購總數的98%。稅收“唯廣最盛”、“課入倍于他路”。
雖然在1300年后,昔日盛唐時期的繁華已經蕩然無存,但光塔寺周邊的許多街巷名卻還保存了珍貴的歷史信息,帶有古老的廣州蕃坊留下的痕跡:諸如古老的甜水巷,“甜水”即阿拉伯語“中國山岡”的音譯。附近的海珠路,原名鮮洋街,即阿拉伯語“送別”之意,朝南可直達古珠江的岸邊,是唐宋時送別商船的一條主要干道。從這些殘留的街巷名中,我們還可以獲知當時商業行為的種類及具體地點,如瑪瑙巷、玳瑁巷(疑為今崔府巷)等。這與歷史記載中阿拉伯穆斯林商人擅長從事的珠寶珍奇貿易一一印證。
懷圣寺光塔究竟建于何時?尚無定論。上世紀40年代,著名歷史學家羅香林認為,懷圣寺光塔,即為客居廣州、信仰伊斯蘭教的蒲姓阿拉伯商人所建,其根據在于蒲氏族人保留的《南海甘蕉蒲氏家譜》中記載:“叔祖嗎哈珠,嗎哈嗼兩公倡筑羊城光塔,晝則懸旗,夜則舉火,以便市舶之往來”,進而得出結論,光塔始建于南宋嘉定年間。
根據其家譜記載,蒲世的故宅,在鄰近瑪瑙巷、朝天路西側的玳瑁巷,根據考證,可能就是今日的崔府街一帶。光塔寺附近的普寧里,原名“蒲宜人巷”,在華居住的阿拉伯人,若名字帶有“Abu”前綴者,則常常會擇“蒲”字為漢姓。

珠江邊的外國人(攝于2009年)
作為佐證,南宋著名文學家,名將岳飛之孫岳珂在《桯史》中,記載廣州蒲姓貴人之堂,“后有萃堵波,高入云表”,“式度不比它塔,環以璧為大址,余而增之,外圓而加灰飾,望之如銀筆”。文中提到的萃堵波,即是懷圣寺光塔,北宋神宗、哲宗朝詩人郭祥正在《廣州越王臺呈蔣帥待制》一詩中,也稱頌了光塔的雄偉景觀:“番禺城北越王臺,登臨下瞰何壯哉!……蕃坊翠塔卓椽筆,欲蘸河漢濡煙煤。”
盡管如此,學界主流意見依舊是懷圣寺與光塔皆為唐代所建,蒲氏家族之“倡筑”僅是修葺,而非建造。蒲氏家族二三代墓地,即在今日廣州越秀公園內。距離此不遠,就是廣州先賢墓清真寺。其中心就是古稱“回回墳”或“大人墳”的賽義德·艾比·宛葛素陵墓。相傳賽義德·艾比·宛葛素為伊斯蘭教創始人穆罕默德的母舅,于唐初來華傳教,懷圣寺與光塔即為其親手創建。
當我們趕到位于越秀區蘭埔附近的先賢墓清真寺時,門口的道路上已經人山人海,許多頭戴白帽的本地穆斯林與外國商販已經支起了攤位,販賣從波斯風格地毯,到阿拉伯水煙,以及南亞精油等形形色色的商品。清真寺負責人魏國標阿訇告訴我們,今天是星期五,是伊斯蘭教傳統的主麻日,在下午13點左右,通常有兩三千名本地與寓居廣州的穆斯林匯聚在此,在這里進行禮拜活動,自明清以來,這里就被各國穆斯林視為“小圣地”,許多信徒不遠千里從中亞、西亞專程來廣州朝覲,這個傳統一直保持至今。

一家茶葉出口商店門前正待運往歐洲的貨品(約攝于1900年)
雖然時間還沒有到中午,但在寺院中心位置,圓頂方室的宛葛素墓室中已經有幾位虔誠的非裔和阿拉伯穆斯林在頂禮誦經。這種穹形圓頂墓室結構,在阿拉伯和波斯被稱為“拱拜爾”,由于墓室內空,圓頂穹窿,頌經的聲音回響洪亮,余音不絕。在宛葛素墓室周圍的樹木之間,還有12方自元代至民國初年的穆斯林先賢墓碑,石制墓碑都被信徒們供奉的綠色錦緞所罩住,其中一位逝世于乾隆十八年(1753)的土耳其汗志·馬罕默德,就是從土耳其東部專程來廣州瞻仰宛葛素陵墓的虔誠教徒,后逝世于廣州,特遺囑懇求將自己葬在先賢古墓之側。不多時,墓室周邊與大禮拜堂中,以及寺院內的綠地內,已經擠滿了膚色衣著各異的各國穆斯林,在盛夏的驕陽之下,隨著禮拜堂中的宣禮之聲,齊齊跪倒。——在一剎那之間,1300年間的歲月仿佛驟然回流,盛唐時期的廣州蕃坊,似乎就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