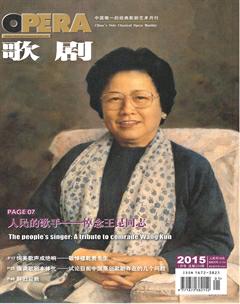絢美歌聲成絕響
蔣力



2014年11月23日,我從上海回到北京當晚,接到劇院同事、樓乾貴先生的弟子王海民發來的短信,告知樓先生去世的消息(與歌唱家王昆同日)。立刻給王海民去電,問了樓先生的近況。通話之后,心情波動,次日即去劇院協助籌備樓先生后事,還建議院報當期增補了悼念樓先生的內容。是夜燈下,勉強寫成一副挽聯。自知甚不工整,也無暇再作推敲,自以為這挽聯對樓先生的一生做了一個簡約的概括。淺釋如下:
男高音歌唱家樓乾貴先生,上世紀40年代在上海震旦大學學醫,兼在上海國立音專學聲樂。因接觸進步組織,在八仙橋的青年會等地演唱進步歌曲,曾被當局以演唱“反動歌曲”為由,判了死罪,并擬押至海上行刑。時近上海解放,解放軍逼近上海,碼頭工人已罷工,無船出海,便又押回監禁地。轉瞬間看守倉皇逃走,樓乾貴得以從獄中還家,繼而攜女友一起北上。50年代初期,以博士學位的資格在協和醫院公共醫學系工作。以中國青年藝術團合唱隊員的身份,赴歐參加世界青年聯歡節。臨時被指定改唱獨唱,經指揮家李德倫指導,練就歌劇詠嘆調“偷灑一滴淚”,在聯歡節上演唱,獲得銀獎。次年訪問蘇聯時,專門錄制了唱片,其中既有中國歌曲《在那遙遠的地方》,也有俄羅斯歌劇《葉甫蓋尼·奧涅金》中連斯基的詠嘆調,獲得極高評價。回國后調入中央歌劇院,擔任獨唱演員兼聲樂指導。曾無端被打成右派,而后又指定他扮演《蝴蝶夫人》中的男主角平克爾頓,他也不計較,從而成為戴帽右派登臺主演歌劇的一個特殊之例。在歌劇舞臺上,他演過主角、配角,還演了不少小角色,正反面的都有。《洪湖赤衛隊》中的男壯年,是上不了節目單的群眾演員,樓先生也曾是其中的一個,這是我的同事戴大輝最近從劇院上演該劇時的場記記錄中發現的。“文革”后,樓先生以音樂會演唱為主,從男聲四重唱到獨唱,兼任聲樂指導,歌聲曾傳遍千家萬戶。他的聲音,干凈、通透、純美、抒情、講究。我撰寫的評介樓先生的文章在自己的博客上刊載后,得到不少反饋,很多人想起聽他演唱《鴿子》《小板凳》《為一塊牛排出賣巴黎》《遙遠,遙遠》《教我如何不想他》等中外歌曲時獲得的藝術感受。他在中央歌劇院擔任聲樂指導的重要作品是中文版的歌劇《卡門》。晚年撰寫了不少淺談聲樂藝術的普及類文章,主要發表在《天津青年報》,還有一篇應我之約寫的《淺談歌唱藝術》,收入我編的《談美小札》一書。80年代歌劇在中國極不景氣的那些年,他退而不休,與劇院幾位老藝術家一起,創辦了首都歌劇培訓學校,在簡陋的環境中,以一架鋼琴為主,排演了《唐帕斯夸萊》等6部外國劇目,戴玉強、孫秀葦、袁晨野等人都曾獲益于該校。樓先生終生為歌劇藝術、為聲樂藝術、為培育青年一代無私奉獻,樂在其中。人品藝德皆高,永遠值得我們學習!
每個劇院都有自己的名角兒,在我看來,中央歌劇院歷史上最有名的角兒,一是女高音張權,一是男高音樓乾貴和李光羲。我把他們視為劇院的院寶,其實,稱為國寶也不為過。如果不是連續不斷的“運動”,他們都完全可以在歌劇舞臺上塑造更多的藝術形象。我生也晚,沒看過樓先生主演的《奧涅金》等外國歌劇,倒是家父家母年輕時一起看過這個戲。但家父愛京劇愛話劇,不大愛歌劇,所以看完以后沒留下什么印象。我第一次,大概也是唯一一次聽樓先生演唱外國歌劇詠嘆調,是在1993年。那年是柴科夫斯基逝世100周年,北京五六家院團都上演了紀念音樂會,中央歌劇院的音樂會是在海淀劇院演出的,湯沐海指揮。我那時年輕,干的是記者職業,只要有好演出,不管遠近我都要去,有我喜愛的樓先生登臺,我更要去。那天,樓先生的演唱不能說很精彩,但于70歲的人來說,已屬不易。他演唱的是連斯基的詠嘆調“青春,青春,你遠遠地飄向哪里”,是一首難度較大、于當今的男高音來說已偏生僻的詠嘆調。1954年,樓乾貴在蘇聯用俄語演唱這首詠嘆調后,蘇聯的音樂家鮑·亞歷山德洛夫曾在《真理報》撰文予以高度評價:“樓乾貴是出色的抒情男高音,其聲音輕快而純凈。在演唱歌劇《奧涅金》中難的連斯基的詠嘆調時,以異乎尋常、深入角色的情感,刻畫了人物詩一般的真實形象。”我很欣賞他那天細膩的、戲劇性的藝術處理,為此還與同去的某女士記者小有爭議。女記那時青睞湯大師,專去劇院看了合樂,她說,合樂到樓先生時,樓先生是半面向樂隊坐著唱的,唱了一句,湯大師就叫停。說樓先生麻煩您站起來唱吧,不然聲音出不來。樓先生沒有解釋,站起來直到合樂完畢。湯大師未再表示什么不滿。女記講述此事時的口吻,顯然站在湯大師一邊,我則說樓先生年事已高,體重也超過常人,說不準那天身體狀況怎樣,最后的呈現還是在臺上。我們這個年齡的人,能聽到他演唱外國歌劇詠嘆調,相當難得了。即便因為某種原因,不得不在臺上坐著唱,我也樂于欣賞。女記說我抬杠,我未再爭,但我們后來都目睹過李德倫先生坐指交響音樂會的別一番風采,甚至看到李大爺揮著揮著竟奇跡般地由坐而站,站到一曲奏畢。事實上,樓先生晚年身上多病的兩處,一是心臟,另一處就是腿。網上能看到的一段視頻,是他來劇院指導老藝術家合唱團,從始至終都坐在輪椅上沒下來。他家的沙發都是留給別人坐的,他必須坐高些的椅子,我去他家時也是這樣。
我本來希望王海民作為樓先生的弟子,能多談談樓先生演唱上的特長,可惜他的文章雖不算短,卻沒有在這方面展開和深入,可能他還處在先生病逝的悲痛之中,一時難以自拔,無法深入探討。最近讀到南昌航空大學音樂學院副教授張建國的一篇文章,他采訪過的幾位音樂界前輩,談到樓乾貴的演唱時,都提到,樓乾貴特別注重歌唱中的Legato(連貫),聲樂教育家蔣英教授甚至這樣評價:“在當今中國真正能做到Legato歌唱的還只有樓乾貴一人。”細想一下,確是這樣,說樓先生的歌聲有魅力,音色華美是一大特點,氣息長是又一大特點。他的呼吸很講究,幾乎聽不出他在哪里換氣。我原來只認為他肺活量大、氣息長,沒意識到這就是Legato。舉例來說,“村莊,我的小村莊,你那迷人的黃昏,曾引起我懷念,我不能忘記你”、“我永遠懷念那櫻桃紅艷的美好時節”都很能體現出他的Legato。張建國對樓先生聲樂特色的歸納是:音色明亮而親和、咬字親切而清晰、呼吸悠長而自如、歌聲抒情而感人。
1979年,劇院組織的包括樓先生在內的藝術家小組赴上海演出,得到上海音樂界的一致好評。上海音樂學院周小燕、王品素、譚冰若3位教授聯名,以“周品若”的筆名,在《文匯報》發表了題為《北京來的春風》的評論。這或許是樓先生最后一次親近他早年求學并走上歌唱之路的城市了。
2014年11月27日,樓乾貴先生遺體告別儀式在北京八寶山殯儀館竹廳舉行,先播放的是一首彌撒類的作品,然后播放的是樓先生演唱《櫻桃時節》的錄音。這是1871年巴黎公社之后一位作曲家寫的,悼念一位同樣參加了巴黎公社而為之獻出了年輕生命的女護士。歌詞貌似平淡,旋律更是舒緩。“我永遠懷念那櫻桃紅艷的美好時節,為逝去的年華我心傷痛欲絕。”樓先生的演唱,也很平緩,但隱隱的憂傷,止不住地穿透人們的心房,也撞擊著我的心。現場的抽泣聲,此起彼亦未伏。我閉上雙眼,心里想的是最后一次接到樓先生電話時的情景:我寫他的文章見了報,我給他寄去了幾份。電話中他的聲音位置還是那么高、那么亮、那么透。他一連說了幾聲謝謝,說有老同事先于我送了一份樣報給他,他看了很高興,復印了幾份,寄送給幾位要好的老朋友。他還說,搬到城里來住了,離劇院不算太遠,有時間來玩兒。這最后的話,此時想起來,仍令我愧赧!
李光羲老師與樓先生同事多年,也在《奧涅金》中扮演過連斯基。一年多前,光羲老師收到一位老攝影家的影集,里面有那位攝影家為李、樓二位拍攝的照片。攝影家請光羲老師轉送樓先生一冊,也是從我這里轉手的。寫此文時,我特意邀請光羲老師講幾句,他說:20世紀50年代中國聲樂藝術大發展,奠定了中國聲樂學派的基礎,樓先生是當時的重要人物,在廣大聲樂愛好者中享有極高聲譽,表現細膩、熱情、高雅,獨樹一幟。可惜由于歷史原因,未能發揮更大的應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