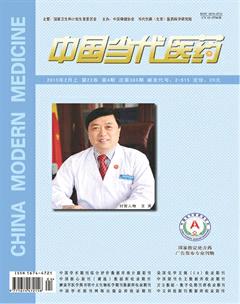法古追今,在中西醫(yī)結(jié)合之路上執(zhí)著前行
凌寒
王英的身份很“復(fù)雜”,稍微對(duì)他了解得深一些,就無法定位他的社會(huì)角色:醫(yī)學(xué)專家、醫(yī)療事故鑒定專家、醫(yī)療機(jī)構(gòu)管理者、散文作家、科普作家、詩人、旅行家等等。在其50余年的人生路途中,他涉獵的的領(lǐng)域太多了,并且在多個(gè)領(lǐng)域都有成就、斬獲,并最終變成了一部部專著或者一篇篇學(xué)術(shù)論文,呈獻(xiàn)給世人。
“中學(xué)為體,西學(xué)為用”,是清末洋務(wù)派領(lǐng)袖張之洞在100多年前提出的治學(xué)理念,但沉淀到王英身上時(shí),他說他無論是在中西醫(yī)結(jié)合的學(xué)術(shù)上,還是在醫(yī)院管理、文學(xué)創(chuàng)作等其他領(lǐng)域的一切探索和收獲,都離不開這八個(gè)字所鋪陳的脈略,只不過他所認(rèn)識(shí)的“中學(xué)”,不是張之洞當(dāng)年為了推行洋務(wù)理念及實(shí)踐而框定的以孔孟之道為核心的儒家學(xué)說,而是以中醫(yī)學(xué)為代表的、全面而又立體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他所認(rèn)識(shí)的“西學(xué)”,則是以西醫(yī)學(xué)為代表的一切現(xiàn)代人類文明催生的文化內(nèi)涵及科技成就。他的“中西結(jié)合”,既是醫(yī)學(xué)范疇的,也是文學(xué)范疇的,更是50余年的人生歷程中,其法古追今、兼收并蓄的漫長過程……
鄉(xiāng)村到軍營,雜糅中西醫(yī)學(xué)養(yǎng)
“我最初的中醫(yī)學(xué)基礎(chǔ),來自于鄉(xiāng)村;而我最初的西醫(yī)學(xué)歷練,則來自于軍營。”三句話不離本行。盡管王英的社會(huì)身份較多,但一開口,他還是先談及了他的“主業(yè)”:醫(yī)學(xué)學(xué)術(shù)修養(yǎng)最早的根基。
隨后,王英以他充滿文人氣質(zhì)的語言回憶說:“我的童年和少年與其他農(nóng)家子弟無異。我之所以與醫(yī)學(xué)結(jié)緣,與我小時(shí)候周圍的親屬和所處的社會(huì)背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我的外祖父是遠(yuǎn)近聞名的老中醫(yī),我自小耳濡目染、潛移默化,受到了中醫(yī)學(xué)的熏陶;上了高中后,讀的‘雜書越來越多,其中就包括當(dāng)時(shí)很普遍的《赤腳醫(yī)生教材》——這是在縣醫(yī)院工作的姑姑和姑夫給我推薦的。他們和父母還極力推薦我去當(dāng)時(shí)很讓人羨慕的縣里的赤腳醫(yī)生學(xué)習(xí)班接受培訓(xùn),所以,我一直認(rèn)姑姑和姑夫是我后來從事醫(yī)學(xué)的引路人。”
和很多那個(gè)時(shí)代的同齡人一樣幸運(yùn),王英憑著“家學(xué)”淵源和專業(yè)學(xué)習(xí)的“雙重功底”,最后被留在了縣醫(yī)院,成了一名真正的醫(yī)生。在那期間,王英還系統(tǒng)研讀了《傷寒雜病論》《金匱要略》《醫(yī)宗金鑒》等中醫(yī)典籍,從而奠定了扎實(shí)的中醫(yī)理論基礎(chǔ)。到了1977年,又一個(gè)人生的轉(zhuǎn)機(jī)降臨了——他應(yīng)征入伍,成了一名解放軍戰(zhàn)士。在軍營里,由于他入伍前的“履歷”得天獨(dú)厚,很幸運(yùn)地成了一名連隊(duì)衛(wèi)生員,繼而又升任師醫(yī)院衛(wèi)生班班長。
王英談及這段經(jīng)歷時(shí)感慨地說:“那個(gè)時(shí)候,我根本沒有‘中學(xué)、‘西學(xué)的意識(shí),比如說赤腳醫(yī)生教材,其實(shí)就是在毛主席的‘中西醫(yī)結(jié)合的指示下編纂的。其內(nèi)容雜糅了中西醫(yī)的治療知識(shí),而且在那個(gè)倡導(dǎo)‘一把草藥一根針的年代,更多的內(nèi)容側(cè)重于中醫(yī)診療。也就是說,在那時(shí),我就已經(jīng)蒙目龍地奠定了中西醫(yī)學(xué)的基礎(chǔ)——盡管這些基礎(chǔ)很薄弱,但卻讓我受益一生。而且,無論我在老家當(dāng)醫(yī)生還是在部隊(duì)當(dāng)衛(wèi)生員,我對(duì)當(dāng)時(shí)占據(jù)城鄉(xiāng)醫(yī)療主流力量的老中醫(yī)都心存敬仰,并抓住一切機(jī)會(huì)向他們學(xué)習(xí)——我先后拜師縣醫(yī)院醫(yī)師李清香、民間老中醫(yī)陳秀、成都軍區(qū)衛(wèi)訓(xùn)大隊(duì)大隊(duì)長余萬江和岔河集衛(wèi)生院院長郭志學(xué)為師,不斷學(xué)習(xí)鉆研中西醫(yī)理論知識(shí)。”
1978年,王英在部隊(duì)院校又系統(tǒng)地學(xué)習(xí)了西醫(yī)基礎(chǔ)理論,畢業(yè)后分到成都軍區(qū)某部隊(duì)醫(yī)院工作,開始從事中西醫(yī)結(jié)合治療類風(fēng)濕病的臨床實(shí)踐與理論研究。“‘寧治十個(gè)貼骨瘡,不治一條老寒腿。這是以前的老中醫(yī)常說的一句話,可見風(fēng)濕及類風(fēng)濕病的治療從古至今都屬于較為棘手的學(xué)科。也許是年輕氣盛吧,從那時(shí)開始,我便把‘中西醫(yī)結(jié)合治療類風(fēng)濕病當(dāng)成了主要專業(yè)研究方向。”王英在采訪中這樣闡述他選擇專業(yè)學(xué)術(shù)研究之路的動(dòng)機(jī)。
王英轉(zhuǎn)業(yè)回到家鄉(xiāng)后不久,又考取了成都中醫(yī)藥學(xué)院(今成都中醫(yī)藥大學(xué)),并在1985年學(xué)成畢業(yè)。他對(duì)此階段的醫(yī)學(xué)學(xué)習(xí)生涯歸結(jié)說:“在這期間,我的醫(yī)學(xué)理論與實(shí)踐得到明顯提高。在部隊(duì)時(shí),我就利用中醫(yī)中藥外加注射針灸治愈了多名戰(zhàn)士的腰椎、腿疼、鼻子出血、強(qiáng)直性脊柱炎和斑禿病癥,為此,軍區(qū)《戰(zhàn)旗報(bào)》多次報(bào)道。在成都軍區(qū)服役的7年間,我連年受到每年兩項(xiàng)嘉獎(jiǎng),三次榮立個(gè)人三等功,還被評(píng)為成都軍區(qū)先進(jìn)個(gè)人……感謝中西醫(yī)學(xué),它讓我在最好的年華獲得了諸多令我珍視一生的榮譽(yù)……”
探索與突破,
打通中西醫(yī)難以交融的障礙
選定研究方向后,經(jīng)過幾十年的中西并重、融會(huì)貫通的探求,王英憑借自己深厚的理論修養(yǎng)、豐富的臨床經(jīng)驗(yàn),突破了中西醫(yī)間難以溝通交融的障礙,突破了傳統(tǒng)醫(yī)學(xué)在某些方面的束縛,在宏觀上運(yùn)用中醫(yī)整體觀念,在微觀上應(yīng)用當(dāng)代科學(xué)手段進(jìn)行剖析,針對(duì)類風(fēng)濕疾病,從病因上引入了我國中醫(yī)寒涼派醫(yī)學(xué)創(chuàng)始人、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劉守真在《素問病機(jī)原病式》和《宣明論方》中提出的“天令火化”之理,大膽地從類風(fēng)濕病的病因、機(jī)理、治療等方面提出了“類風(fēng)濕病多起因于內(nèi)火,在表現(xiàn)上則南北有別。南方氣候濕潤,多發(fā)于肌表;北方氣候寒冷,多發(fā)于筋骨,所以在治療上應(yīng)予以辨證施治,區(qū)別對(duì)待”的獨(dú)到見解。
采訪時(shí)王英站在專業(yè)的角度介紹說,風(fēng)濕類疾病是一種范圍廣泛、致病因素多樣、病變部位不一、病理變化復(fù)雜的疾病。它不是特指某一種疾病,而是一組疾病的統(tǒng)稱。風(fēng)濕類疾病簡稱“風(fēng)濕病”。提到風(fēng)濕病,人們常常誤認(rèn)為是關(guān)節(jié)炎及受風(fēng)或受潮濕、寒冷影響而引起的肌肉、關(guān)節(jié)痛,其實(shí)不然。“風(fēng)濕”一詞來自古希臘語Rheuma,該詞本身并沒有“風(fēng)”和“濕”的含義,其意是流動(dòng)的意思,來源于2000多年前的液體病理學(xué)說。西醫(yī)學(xué)最初認(rèn)為風(fēng)濕病是黏液由腦流向關(guān)節(jié)和身體其他各部位時(shí)引起的游走性疼痛,但隨著醫(yī)學(xué)的發(fā)展,人們不再相信液體病理學(xué)說,風(fēng)濕病學(xué)有了迅速發(fā)展。近年來風(fēng)濕病學(xué)已逐漸發(fā)展為一門正式的跨學(xué)科的專門學(xué)科。它概括的范圍相當(dāng)廣泛,其發(fā)病原因包括受風(fēng)、潮濕、寒冷等環(huán)境因素,也包括感染因素如化膿性關(guān)節(jié)炎、風(fēng)濕性關(guān)節(jié)炎;免疫學(xué)因素如類風(fēng)濕關(guān)節(jié)炎;內(nèi)分泌性因素如糖尿病、甲狀腺功能亢進(jìn);退行性病變因素如骨關(guān)節(jié)炎;代謝性因素如痛風(fēng)、假痛風(fēng);甚至包括一些遺傳性疾病、腫瘤等。到目前為止,已知具有不同名稱的風(fēng)濕類疾病達(dá)100多種。
王英進(jìn)一步闡述說,風(fēng)濕類疾病在祖國醫(yī)學(xué)中屬“痹證”范疇。我國最早的醫(yī)學(xué)經(jīng)典《素問·痹論篇》指出:“風(fēng)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為痹也,其風(fēng)氣勝者為行痹,寒氣勝者為痛痹,濕氣勝者為著痹。”這是最早對(duì)痹證發(fā)病原因及分型、分類的記載。后來隨著歷代醫(yī)家對(duì)風(fēng)濕痹證的深入研究,在以往對(duì)本病病因病機(jī)認(rèn)識(shí)的基礎(chǔ)上,除強(qiáng)調(diào)“風(fēng)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為痹”的外邪說外,許多醫(yī)家陸續(xù)重視正氣虛弱、衛(wèi)表不固、氣血不足、肝腎虧損等在本病中的作用,如當(dāng)代大醫(yī)朱良春認(rèn)為:先有陽虛,病邪遂乘虛襲踞經(jīng)隧,氣血被阻,壅滯經(jīng)脈,深入骨髓,膠著不去,痰瘀互結(jié),凝滯經(jīng)脈而成頑痹;我國另一位中醫(yī)學(xué)者焦樹德認(rèn)為:腎虛寒邪入骨,復(fù)感三邪內(nèi)舍肝腎而致本病。
“西醫(yī)對(duì)于類風(fēng)濕疾病的認(rèn)識(shí)和治療大多重在消炎、止痛等的對(duì)癥治療上,其治療藥物大致有四個(gè)方面。”王英把話題由中醫(yī)學(xué)轉(zhuǎn)入西醫(yī)學(xué)范疇時(shí)歸結(jié)說:“首先是非甾體抗炎藥。非甾體抗炎藥雖然會(huì)引起諸多不良反應(yīng),但絕大多數(shù)患者在短期服用該類藥物時(shí)出現(xiàn)的不良反應(yīng)較輕微,能耐受,而且停藥后不良反應(yīng)即可消失,不會(huì)對(duì)該類藥物發(fā)揮療效產(chǎn)生影響。其次是一些藥效較慢的治療選擇,或者叫‘慢作用藥。慢作用藥還被稱為改善病情的抗風(fēng)濕藥,這類藥物能抑制組織和關(guān)節(jié)的進(jìn)行性損傷,延緩和阻止病情發(fā)展,但顯效慢,常需數(shù)月方能見療效。第三就是糖皮質(zhì)激素。此類藥物具有消炎、免疫抑制、抗毒、退熱四方面的作用,但如果長期大量應(yīng)用糖皮質(zhì)激素可引起物質(zhì)代謝和水鹽代謝紊亂,出現(xiàn)類腎上腺皮質(zhì)功能亢進(jìn)綜合征,如水腫、高血壓、向心性肥胖、肌無力和肌萎縮等癥狀。第四類就是免疫抑制劑。免疫抑制劑是一類非特異性抑制免疫功能的藥物,既抑制正常免疫,也抑制異常免疫。免疫抑制劑對(duì)免疫系統(tǒng)以及免疫細(xì)胞缺乏選擇性和特異性,因而往往全面抑制機(jī)體的免疫功能,應(yīng)用時(shí)須嚴(yán)格掌握適應(yīng)證。
王英認(rèn)為,由于風(fēng)濕類疾病是一組病因復(fù)雜,癥狀變化多樣的疾病,參與的細(xì)胞和細(xì)胞因子很多,單用任何一種藥都難以阻斷這種多過程、多因素所致的疾病,所以特別需要廣泛貫徹中西醫(yī)結(jié)合理念,聯(lián)合用藥給予治療,方能達(dá)到提高療效和減輕毒性的目的。在類風(fēng)濕疾病的治療原則上,王英強(qiáng)調(diào)“應(yīng)在補(bǔ)腎堅(jiān)骨、固本培元的基礎(chǔ)上,用辛涼解表、瀉熱養(yǎng)陰之藥”;在具體方法上則根據(jù)不同患者的情況分別以對(duì)癥口服海馬補(bǔ)腎壯骨散、龍蛇散、麻黃濕痹散、除痹勝濕丸、芪己茯黃散等多種中成藥制劑為主,以西藥、針灸、按摩及外敷痹痛靈散等其他方法為輔,從而形成“中西醫(yī)結(jié)合、標(biāo)本兼攻、綜合調(diào)理、立體治療”的診療模式。這種模式的創(chuàng)立已經(jīng)成為當(dāng)今類風(fēng)濕疾病的臨床研究的突破性進(jìn)展。
在強(qiáng)調(diào)“聯(lián)合用藥”的重要性時(shí),王英提出:“聯(lián)合用藥,就是發(fā)揮西藥的治療作用,同時(shí)最大限度地抑制其毒副反應(yīng),這一直是這些年來我悉心研究的課題。我們應(yīng)用益氣養(yǎng)血、健脾化濕、活血通絡(luò)中藥聯(lián)合西藥,辨證分型治療風(fēng)濕類疾病,不但取得了滿意的臨床療效,而且上述毒副作用的出現(xiàn)率也明顯降低。”
“在實(shí)施中醫(yī)整體治療時(shí),還必須注意分期和分型。”王英說,經(jīng)過幾十年的臨床研究,他們總結(jié)出了“抓住早期治愈,控制中期發(fā)展,改善晚期癥狀”的中西醫(yī)結(jié)合治療類風(fēng)濕疾病的綱領(lǐng)性原則,“只有這樣,才能打通中西醫(yī)難以交融的障礙,并且從疾病的全局出發(fā),給患者帶來治愈的希望。實(shí)踐證明,這確實(shí)是一條極其珍貴的經(jīng)驗(yàn)!”
醫(yī)學(xué)和文學(xué),
兼收并蓄的人生收獲
1992年6月,在醫(yī)學(xué)學(xué)術(shù)方面已經(jīng)有了豐厚積淀的王英,信心滿滿地離開原工作單位,在霸州市衛(wèi)生局的鼎力支持下,篳路藍(lán)縷地創(chuàng)辦了霸州市類風(fēng)濕醫(yī)院。20多年過去了,當(dāng)年的專科醫(yī)院如今已經(jīng)升格為廊坊紅十字霸州開發(fā)區(qū)醫(yī)院,但他并不止于過往的成就,年過半百,仍孜孜于學(xué),在香港國際中醫(yī)藥研究院研究生部系統(tǒng)修完了傳統(tǒng)醫(yī)學(xué)(中醫(yī)學(xué))博士學(xué)位的全部課程,通過了論文答辯,經(jīng)該院學(xué)位委員會(huì)評(píng)審?fù)ㄟ^,被授予“傳統(tǒng)醫(yī)學(xué)博士”學(xué)位。
談及他麾下的醫(yī)院當(dāng)前的規(guī)模,王英如數(shù)家珍:經(jīng)過多年的不懈努力,目前,昔日的類風(fēng)濕病醫(yī)院已發(fā)展成為建筑面積10 000平方米,設(shè)置病床120張,擁有類風(fēng)濕病、椎間盤、婦產(chǎn)科、甲狀腺、核醫(yī)學(xué)前列腺5大專科及內(nèi)、外、兒等職能科室的大型專科醫(yī)院,先后被中華傳統(tǒng)學(xué)會(huì)、中國保健科技學(xué)會(huì)科技發(fā)展中心授予首屆全國中醫(yī)專科專院科技合作交流會(huì)“十佳專科醫(yī)院”等榮譽(yù)。2001年被河北省勞動(dòng)和社會(huì)保障局認(rèn)定為“城鎮(zhèn)職工基本醫(yī)療保險(xiǎn)定點(diǎn)醫(yī)療機(jī)構(gòu)”。2003年,又被中華傳統(tǒng)醫(yī)學(xué)會(huì)授予“類風(fēng)濕、椎間盤突出癥河北霸州專科治療康復(fù)基地”。
與此同時(shí),王英近40年潛心中西醫(yī)結(jié)合治療風(fēng)濕病、中醫(yī)治療系統(tǒng)性紅斑狼瘡、肝硬化腹水等專科中醫(yī)藥學(xué)理論研究和臨床實(shí)踐,先后發(fā)表學(xué)術(shù)論文60余篇,出版學(xué)術(shù)類專著6部;他所取得的學(xué)術(shù)成就引起了全國專科醫(yī)學(xué)組織的普遍關(guān)注。2009年11月12日,在杭州舉行的中國中西醫(yī)結(jié)合系統(tǒng)性紅斑狼瘡研究學(xué)術(shù)會(huì)議上,王英被推選為中西醫(yī)結(jié)合專業(yè)委員會(huì)常務(wù)委員;2011年8月24日,在貴陽舉行的“第九屆全國中醫(yī)難治病學(xué)術(shù)研討會(huì)暨毒邪學(xué)說論壇”會(huì)議上,王英被中華中醫(yī)藥學(xué)會(huì)推舉為中華中醫(yī)藥學(xué)會(huì)難治病研究專家委員會(huì)委員及類風(fēng)濕病研究協(xié)作組副組長。
“醫(yī)學(xué)和文學(xué),歷來有著無法割舍的內(nèi)在聯(lián)系。我國古代的諸多名醫(yī),大多是流芳百世的詩人和文學(xué)家。我盡管無法與他們相提并論,但多年的人生路途中,我收獲的東西太多了。多年前,我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熱忱就一直在內(nèi)心激蕩……”談及王英出版的多部紀(jì)實(shí)文學(xué)和詩集、散文隨筆集時(shí),王英感慨地說,“在多年的臨床工作中,我發(fā)現(xiàn)社會(huì)上對(duì)于很多疑難疾病的認(rèn)識(shí),存在很多誤區(qū),所以,我先是抽空編寫了《當(dāng)代中藥外治十科百病千方》等多部科普書籍,又先后以自己從醫(yī)近40年的人生足跡為素材,寫出了長篇傳記《悠遠(yuǎn)的云》和行醫(yī)傳記《梨花雨》;還出版了詩集和散文隨筆集等等……”
采訪到最后,王英感慨地說:“這輩子選擇了中西醫(yī)結(jié)合的路子,我會(huì)一直走下去。經(jīng)過大半生的歷練,我越來越覺得,醫(yī)學(xué)充實(shí)了我的人生,而文學(xué)則裝飾了我的人生。無論是醫(yī)學(xué)專業(yè)著作還是文學(xué)作品,這都是我站在中西醫(yī)學(xué)的坐標(biāo)上,針對(duì)東西方文化歷練、思考和感悟的美好收獲……”
專家簡介
王英,主任醫(yī)師、醫(yī)學(xué)博士。現(xiàn)任河北省霸州開發(fā)區(qū)醫(yī)院院長、黨支部書記。系中國中西醫(yī)結(jié)合學(xué)會(huì)風(fēng)濕類疾病專業(yè)委員會(huì)常委、中國中西醫(yī)結(jié)合防治風(fēng)濕類疾病聯(lián)盟副主席、中華中醫(yī)藥學(xué)會(huì)難治病研究專家委員會(huì)委員及類風(fēng)濕病研究協(xié)作組副組長、中國特色醫(yī)療學(xué)術(shù)研究會(huì)副會(huì)長、中國醫(yī)療保健國際交流促進(jìn)會(huì)副理事長,國際華夏醫(yī)藥學(xué)會(huì)理事、美國中醫(yī)藥研究院客座教授、世界中醫(yī)藥研究會(huì)終身會(huì)員,河北省中西醫(yī)結(jié)合風(fēng)濕病專業(yè)委員會(huì)副主任委員、河北省作家協(xié)會(huì)會(huì)員,廊坊市醫(yī)療事故鑒定委員會(huì)專家。發(fā)表學(xué)術(shù)論文63篇,并著有醫(yī)學(xué)科普著作《當(dāng)代中藥外治十科百病千方》《尋醫(yī)問藥四百家》《腫瘤科病最新中醫(yī)治療》《中西醫(yī)結(jié)合治療風(fēng)濕四病》《中西醫(yī)結(jié)合臨床精粹》以及長篇傳記《悠遠(yuǎn)的云》、長篇紀(jì)實(shí)文學(xué)《梨花雨》、詩集《雅風(fēng)集》和長篇游記隨筆作品集《江山行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