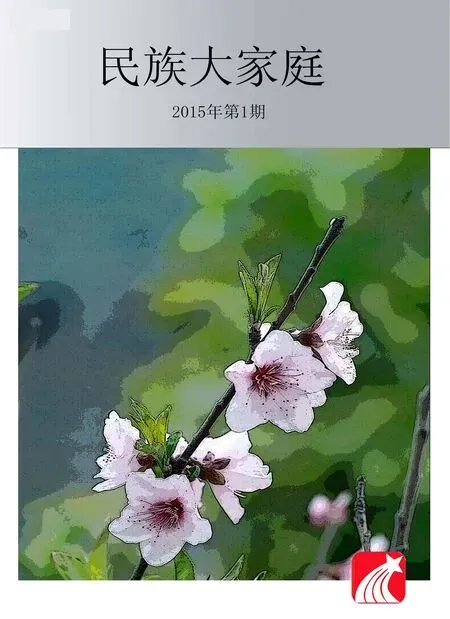難忘在雪域高原的青春歲月
——記援藏醫生、武漢大學退休校醫李春蘭
文/湖北省援藏辦公室
難忘在雪域高原的青春歲月
——記援藏醫生、武漢大學退休校醫李春蘭
文/湖北省援藏辦公室
青春,如詩如夢、如畫如火。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青春,而李春蘭的青春是在西藏高原度過的,準確的說,是在西藏拉薩度過的。她1972年8月進藏,同年9月在西藏自治區人民醫院參加工作,1983年起先后任心血管科、干部病房、內科護士長。在西藏,李春蘭度過了人生中最美好的16個春秋。進入暮年的她,每每回首人生,總忘不了那段艱苦難忘的青春歲月。
穿行川藏路
1972年8月,剛滿18歲的李春蘭放棄保送重慶師范學院學習的機會,辭去家鄉學校代課教師的崗位,隨一批熱血知識青年一起奔赴西藏,支援邊疆建設。告別父母親人,告別美麗富饒的家鄉川西平原,一行年輕人意氣風發地踏上了西去征程,踏上了一段人生的難忘旅程。
不走川藏路,就永遠不會知道川藏路艱險。川藏公路是一條世界上最危險、災害最頻繁、行期乃至生命最難預測的公路。加之當地晝夜溫差極大、天氣變化無常,六月飛雪,一天四季,一日數更衣,冰火兩煎熬。自打上路,李春蘭就時時刻刻都在真實地體驗著與靈魂、與大自然的對話。路途之遙遠,川藏公路之艱險,是她們這些從未出過遠門的年輕人所始料未及的。西藏艱苦之考驗,人生旅程之考驗,從上路之日起就開始了。
車過雅安,便進入了川藏公路最兇險、最令人驚心動魄的路段。走在高高的二郎山上,看著懸空的半個輪子和車下的萬丈深淵,李春蘭一陣陣心驚肉跳。此情此景,讓她不由地回想起那部歌頌當年解放大軍修筑川藏公路電影里的一句著名歌詞:二呀么二郎山呀,高呀么高萬丈。曲子還是那么悠揚動聽,只是心情別是滋味。
一路上,李春蘭與同伴們高原反應強烈,時常有人嘔吐哭泣。隨著雄偉壯麗的布達拉宮進入眼簾,1972年8月中旬,歷經13天約2500公里的艱苦行程,她們一行風塵仆仆地到達拉薩。
第一次出診
1972年9月初,經過嚴格考試審查和學習培訓,李春蘭和來自全國各地的20余名青年男女一道,進入西藏自治區人民醫院從事醫務工作。這一干,就是16年。16年間,參與過無數次重大病案的處置工作,但最讓她難忘的,還是第一次下鄉出診。
1974年7月,她隨自治區人民醫院下鄉醫療隊來到山南地區貢嘎縣駐診。這是她第一次,也是在西藏工作16年間唯一的一次離開拉薩赴外地下鄉出診。
今日的貢嘎縣因西藏唯一的國際航空港貢嘎機場坐落在那里而為人知曉。當年,西藏的醫療條件十分落后,基層更是缺醫少藥。李春蘭下鄉的貢嘎縣人口數萬,是西藏少數幾個人口大縣和農業大縣之一,但縣醫院僅有幾間簡陋平房和十來張病床,既沒有完備的醫療設施,也沒有技術過硬的醫務人員。為緩解基層民眾求醫看病的困難,自治區衛生主管部門開始有組織、有計劃地向基層地區下派醫療隊。像自治區人民醫院這樣的骨干醫院,當仁不讓地擔負起基層巡診和指導基層醫務工作的責任。
自治區人民醫院下派醫療隊到貢嘎縣,這在當地歷史上還是第一次。為此,西藏日報曾專門用藏漢兩種文字發布消息。
李春蘭所在的醫療隊此行一共10人,除翻譯外,其他人都是來自各科室的醫療技術骨干。赴山南地區貢嘎縣醫院駐診3個月,除了給縣駐地干部職工和群眾送醫送藥外,醫療隊還肩負著下農牧區巡診、培訓赤腳醫生、采集中草藥(供醫院制作柴胡、板藍根針劑與口服藥)和支農勞動等任務。
剛到縣駐地熱麥村,大家還沒來得及搬下行李,就見兩名中年藏族漢子馬不停蹄地趕到他們車前。翻身下馬,氣喘吁吁地拉著他們的手,一個勁地央求道:“阿門吉拉,阿門吉拉,求求你們救救我們大哥吧,他快不行了!”
隨隊翻譯央宗告訴李春蘭一行人,他們家有危急病人,請醫療隊無論如何前去救治。事后得知,這兩個藏族漢子是得到自治區人民醫院醫療隊要下鄉巡診的消息,早早便等候在公路邊等到紅十字救護車來后追隨而來的。
情況緊急,來不及休整,隊長當即安排李春蘭和剛從上海來西藏不久的年輕內科醫師蔣健 (后成長為國內知名心血管專家)一同出診。他倆二話不說,帶上急救箱和氧氣袋,騎上病者家屬的馬便出發了。

李春蘭(右)與關愛西藏學子33年如一日的武漢大學退休教師楊昌林在一起

1986年,李春蘭(前排中)在西藏自治區人民醫院
走進病人家中,躺在破舊昏暗屋角一個約40多歲的漢子進入李春蘭的眼簾。患者臉色蒼白,嘴唇發紫,雙眼緊閉,脈象細弱,呼叫不應,已處于休克性昏迷狀態,病情十分危急。來不及寒暄,她迅速組織人員將病人轉移至光線、空氣較好的屋外院子里開展搶救。
在醫生確診病人患重度肺結核,嚴重大咯血導致失血性休克后,遵照醫囑,李春蘭立即給病人輸氧、靜脈注射止血和補充血溶量藥液。實施一系列緊急搶救措施后,患者終于睜開了雙眼,慢慢清醒過來。病人暫時脫離了生命危險,她也長長地舒了一口氣。
“土及且,土及且,阿門吉拉!”見到睜開眼的兒子,單膝跪地的老阿媽激動地淚流滿面,一個勁地朝李春蘭這些醫護人員道謝,并雙手恭恭敬敬地將酥油茶奉上頭頂,請她們無論如何受禮喝茶。單膝跪地,將酒或茶雙手高舉頭頂,是藏族群眾對來訪貴賓的最高禮節。面對一個年齡如同母親的阿媽如此謝禮,年輕的李春蘭既惶恐又感動,不知如何是好,覺得自己實在承受不起如此崇高的禮節。她接過茶一飲而盡,并暗下決心以后要更加用心地為藏區需要醫護服務的人們提供幫助,絕不辜負藏區人民的一片誠意。
“神醫來啦,神醫來啦,頓珠被救活了!”一時間,消息轟動全村,驚嘆不已的男女老少村民們紛紛涌進這小小的院子,黑壓壓的將醫護人員圍了個里外三層。他們一邊舉著大拇指向他們咂舌夸贊,一邊虔誠地向他們求醫訴診。見此情景,大家也顧不上車馬勞頓和搶救病人后的勞累與饑餓,繼續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問診、把脈、測血壓、扎針灸、打針、發藥的過程中,一直忙到天將黑。
眼見求醫者依然絡繹不絕,有增無減,駐村干部阿佳拉心疼地趕緊替他們解圍:醫療隊有各科醫生,到縣醫院駐診3個月,這期間大家可隨時去問診,不要著急。經阿佳拉一番耐心、誠懇的解釋,村民們漸漸散去,累得精疲力竭的他們才得以休息。
收拾好急救箱,乘上村民主動牽來送行的馬車,帶上需要繼續觀察治療的那位肺結核大咯血病人,她和蔣醫生準備趕回縣醫院。村口處,全村男女老少流著眼淚,依依不舍地向他們揮手送行,直到他們的馬車走遠。
貢嘎出診是李春蘭到藏區的首次出診,雖然已經過去很多年,但想起缺醫少藥的藏族群眾對尋醫治病的渴盼、對醫務人員的盛情感激,以及為他們成功解除藏區群眾病痛后獲得的喜悅,至今李春蘭仍記憶猶新,難以忘懷。曾將熱血青春奉獻給了高原民眾,她感到無悔而自豪。
如今已經退休的李春蘭,仍然無時不刻地關注著第二故鄉——西藏的發展,西藏的人和事。多年來,她積極參與武漢西藏老同志聯誼會的活動策劃、組織和服務工作,并主動擔任武漢西藏老同志聯誼會武漢大學聯誼小組組長,積極熱心投身于援藏老同志、全國民族團結模范楊昌林同志關于在漢就學藏族學生的各種聯誼、文化交流活動的組織策劃和服務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