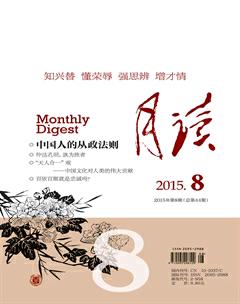漢宣帝整肅吏治:平冤用賢,正本清源
李仕權
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大破大立,功績卓著,然而,在他統治中后期,由于戰爭太久,拖累了國民經濟,幾大昏招對國家傷害甚大:算緡、告緡、不告緡,讓全國的中產幾乎悉數破產;鹽鐵酒官營,追求進度,不顧質量,官商勾結腐敗嚴重;大肆重用酷吏,敗壞民風,流民劇增,造成嚴重的社會危機……總之,漢武帝早期到中期,西漢王朝步步走向鼎盛;到了晚期,形勢卻急轉直下。司馬遷評價漢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于亡秦之禍”。
漢宣帝劉詢是漢武帝曾孫,歷經磨難才登上皇位。他大力改革,既學漢文帝休養生息,又學漢武帝霹靂手段,“以霸王道雜之”,兼具漢文帝和漢武帝兩帝之長,力避兩帝之短,文治武功,皆有大成。
治大國如烹小鮮。最厲害的廚子,不是用山珍海味做滿漢全席,而是把已經串味的飯菜給正過味來。漢宣帝就是這樣一個
廚子。
那么,在吏治方面,漢宣帝是怎樣“標本兼治”、正本清源的呢?
正本清源,從“打老虎”、平冤獄開始
改革,正本清源,通常從反腐“打老虎”開始,漢宣帝也不例外。原因很簡單,“打老虎”能最快立竿見影,能最快贏得民心,能最快贏得主動。
漢宣帝打的第一個“大老虎”,是位高權重名列九卿之一的大司農田延年。田延年在尊立漢宣帝時可是立下了汗馬功勞的,叫作“決疑定策”①,因此被漢宣帝封為陽成侯,出任大司農一職,主管全國財政。這可是一個大肥差,田延年也確實是把這個崗位當作大肥差對待的,結果就倒在了這個大肥差上。事情是這樣的:
話說漢宣帝的前任漢昭帝年紀輕輕就忽然去世了,皇室事先并沒有預備好修造陵墓的物資,所以非常著急。而茂陵的富戶焦氏、賈氏等人,曾經花費了幾千萬錢,收購了大量用于修造陵墓的物資。焦氏、賈氏以為這次能賣個好價錢發筆橫財,誰知高興得太早,田延年不僅不肯花錢從他們手里購買,反而生出了一個惡毒的主意:上奏皇帝,指焦氏、賈氏等商人蓄積建陵物資為非法勾當,應該全部予以沒收。于是,焦氏、賈氏賠了個血本無歸。
但這些富戶也不是吃素的。他們吃虧之后,就盯上了田延年,出錢找人調查田延年的罪行,伺機報復。
而田延年也確實就是個貪官。一邊廂,他借詔令沒收商人的東西,似乎是替政府省錢;但另一邊廂,他卻憑借手中的財政大權,大做手腳,大肆貪污。為漢昭帝修建陵墓,要用大量的沙土,運輸沙土又需要大量租用民間的牛車。拉一車沙土,要付給百姓一定數量的租金,田延年虛報賬目,每車沙土都虛報兩倍租金。陵墓修完,運送沙土的租金共花了六千萬錢,其中三千萬錢進了田延年私人的
口袋。
焦氏、賈氏兩家花了不少錢,終于掌握了田延年貪贓枉法的真憑實據,于是上書告發。漢宣帝下詔,命丞相徹查這宗貪污大案。有大臣以“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為理由,為田延年說情,不過漢宣帝并不以為然,派人傳話要田延年到廷尉那里去受審,田延年畏罪自殺。
田延年并不是漢宣帝打掉的唯一“大老虎”,實際上,漢宣帝對貪污腐敗向來毫不手軟,“拍蒼蠅”一直不斷,“打老虎”也一直
不停。
腐敗往往跟冤獄相伴生,由于漢宣帝有過牢獄之災的經歷,所以對冤獄深惡痛絕。“打老虎”之后,力矯嚴酷、平理冤獄,就順理成章地成為漢宣帝的關注重點。
重用酷吏、施行嚴刑峻法是漢武帝后期的弊政之一。當時的刑罰,嚴苛到讓人毛骨悚然的地步。何以至此?因為當時流行酷吏,負責判案的官吏把苛刻當作嚴明,從而博得“公正”的美譽,但這絕不是真正的公正——由于公正斷案往往會給自己招惹麻煩,所以負責判案的官吏們索性就把案犯置于死地,這樣做,并不是判案官吏恨人之切,而只是他們自保的辦法。漢武帝晚年,雖然下了輪臺罪己詔書,但刑罰深刻、重用酷吏之風積重難返,一時并未得到解決。漢昭帝時期,大將軍霍光為防止大臣爭權,仍遵循漢武帝時的法度,“以刑罰痛繩群下”,所以官吏們都把嚴酷當作本事能耐。
漢宣帝即位后,著力改變這樣的局面。當時的河南太守嚴延年,在打擊豪強、扶助貧弱方面功勞不小,但他過分任用刑罰,不擇手段,他治下的河南郡,每年到了冬天,就會把所屬各縣的囚犯集中到郡府門口,殺頭處斬,往往流血數里,恐怖之極。因此,河南郡的人都稱他為“屠伯”。嚴延年過于嚴酷,殺戮太重,連他的母親都憤然數落他的罪過,并預言:“天道神明,殺人太多的人必遭報應,我不愿在我老年時看見我的兒子受刑被殺戮!我走了!離開你,回到東海郡,等待你的喪期到達。”一年多以后,嚴延年果然被漢宣帝查處,被處斬棄市。
處理了嚴延年,漢宣帝琢磨:一個接一個地去處理酷吏也不是個辦法,于是想到幾個不錯的法子,著力從制度上保證執法的嚴肅性和公正性。
首先,專設廷尉平。以往判案,各個郡的太守簽署了就算是終審拍板了,冤假錯案還真不少。漢宣帝派廷尉參與各郡的司法事務,專門增設四名廷尉平官員,幫助廷尉決疑案、平冤獄。所有死刑判決,必須由廷尉復核才能生效,類似于現在的最高法收回死刑復核權。
其次,恢復文景時期“平獄緩刑”的政策。漢宣帝親政后不久,親自參加了一些案件的審理,為公正判案做表率,并盡力平緩刑罰。據統計,漢宣帝每年平緩死囚達千人,而在這方面貢獻突出的獄吏也會得到提拔和重用。
再次,廢除不合理律令。如地節四年(前66),下令解除“首匿”罪;元康二年(前64),下詔免除觸犯他名諱之人的罪;元康四年(前62),下令對老年人犯罪從寬處理;五鳳二年(前56),下令解除關于鄉民相賀的禁令……另外,還多次大赦天下。其中,“首匿法”是指在打擊逃亡犯本人的同時,還要懲罰逃亡犯的藏匿者。漢宣帝下令,子女藏匿父母,妻子藏匿丈夫,這樣的情形都在人倫情理之中,無需
連坐。
“打老虎”、矯嚴酷、平冤獄,果然立竿見影,全國上下一片叫好,漢宣帝贏得了民心,也贏得了主動。
正本清源,在選賢良、明獎懲中深化
“打老虎”、矯嚴酷、平冤獄,雖然立竿見影,但漢宣帝明白,這只是治標。
“吏不廉平,則治道衰。”早年的民間生活經歷,讓漢宣帝更了解社會實情,更知曉民間疾苦,深深懂得吏治好壞直接關系到百姓的安居樂業與社會的和諧穩定。要治本,必須從根本上整頓吏治,這就成為漢宣帝推行的正本清源式改革的重點。
整頓吏治,先從慎重選拔良吏著手。
自幼生活在民間的漢宣帝,對漢武帝晚年以來地方官吏的“酷暴”深有體驗,在此基礎上,他意識到:一個地方治理得好壞,百姓能否安居樂業,一方官員賢能與否至關重要。所以,他對于地方長官和郡國守相的選任,十分慎重和嚴格:先由大臣舉薦,接著進行廷推,然后擇日親自召見,仔細詢問治國安邦之術,再做定奪。漢宣帝“慎選龔遂”,就是嚴格選拔良吏的典型案例。
漢宣帝在位時,渤海附近郡縣鬧災荒,饑民紛紛起來造反,太守也沒有辦法。丞相和御史大夫都向漢宣帝推薦了龔遂。漢宣帝決定親自考察一下龔遂的人品和能力。
剛見龔遂時,漢宣帝顯然有些失望。當時的龔遂已經70多歲了,貌不驚人,又矮又小,漢宣帝擔心他不能稱職,問道:“渤海郡法律廢弛,饑民作亂,我很擔憂,你準備怎么處理盜賊?”龔遂回答:“渤海遠離京師,沒有稱職的官吏去安撫,百姓饑寒交迫,不得已做了不該做的事,并不是真正的盜賊。就好比陛下的子民拿著兵器在水塘中戲耍罷了,并不是真心叛亂。如今陛下是讓我安撫他們呢,還是讓我鎮壓他們呢?”漢宣帝聽后心頭微微一驚,覺得他出語不凡,于是說:“選用賢良,當然是讓你安撫百姓。”龔遂又說:“我聽說治理亂民就像理一團亂麻繩一樣,心急不得,要有耐心才能治理好。我請求丞相和御史大夫不要過于束縛我,多給些自由裁量權,讓我根據實際情況自行處理。”漢宣帝覺得龔遂說得很對,額外賞賜黃金,派他赴任。果然,龔遂不負厚望,把渤海治理得很好。很快,渤海郡中積蓄充實,官吏和百姓都安居樂業殷實富裕,訴訟案件也沒有了。
整頓吏治,再從加強績效考核發力。
“有功不賞,有罪不課,雖唐虞猶不能化天下。”漢宣帝深知官員考核的重要性,因此在詔令中反復強調。
一直以來,官員俸祿體系都是“垂直薪酬”制度,一級官員嚴格對應一級俸祿。漢朝官制,三公最高,俸祿是一萬石;九卿次之,俸祿是中二千石;以下還有真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千石、比千石、八百石、六百石、四百石、比四百石、三百石、比三百石、二百石、百石……官員為了獲得更高的俸祿,只能升官,于是很多官員往往把精力花在怎么升官“往上爬”方面,而做好本職工作特別是為民眾服務的激情卻遠遠不夠。但往上一級的官職數量是有限的、稀缺的,不可能大量增加,如何既不升官又能調動官員的激情和積極性?這是讓歷代君王頭大的一件事,但漢宣帝找到了一個好辦法,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寬帶薪酬”。
對表現優異而又提拔不了的地方官員,漢宣帝雙管齊下,用物質獎勵、精神激勵的辦法進行嘉獎:物質獎勵方面,在原有的薪俸基礎上增加俸祿,賞賜金錢若干;精神激勵方面,頒布詔書在全國通令嘉獎,甚至賜爵至關內侯。總之,就是使表現優異的官員享受到政治名譽與經濟利益雙重激勵。
膠東國丞相王成在“考績”中被認為安撫了大量流民,功勞很大,漢宣帝就頒布詔令在全國褒獎,并把俸祿從“二千石”提高到“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另外一位功臣黃霸,曾經因為有過失而被貶,以八百石的官秩出任潁川太守,任職八年,郡中大治。漢宣帝下詔稱贊,并給予“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的額外獎賞。按照常規,郡太守的俸祿高者為“二千石”,低者可至“八百石”,而王成、黃霸實際享受的“中二千石”俸祿,與朝廷九卿持平,僅次于三公。
相比于以往的“垂直薪酬”,漢宣帝的“寬帶薪酬”有明顯優點:雖然官員的職務沒有得到升遷,但是利益得到保障,待遇得以改善,政績得到肯定,不僅對當事人有安撫和激勵作用,而且可以給后來者樹立榜樣。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這些舉措刺激了政風吏治的改善,大量良吏、循吏執法公平、恩威并施,治理“合人心”,得到時人
好評。
在“寬帶薪酬”的基礎上,漢宣帝逐步建立起一整套對官吏的考核制度,包括獎懲制度。他多次下詔,嚴格執行“五日一聽事”制度,也就是加強對二千石官員的考核管理,并不定期派使者巡視郡國,對二千石官員的工作進行考核。根據考核結果,優秀的進行獎勵,稱職的進行鼓勵,失職的進行處罰。
在漢宣帝執政的24年中,他不僅重視地方官吏的選拔,也十分重視其他職能部門官吏的選拔,先后六次下詔要求地方官吏為朝廷選拔優秀人才。另外,查閱漢宣帝一朝高級官吏的身世,不少是從基層小吏起步的。如位列三公的丙吉、于定國出身獄吏,魏相、張敞曾經做過郡卒吏,趙廣漢擔任過郡吏,尹翁歸也是獄小吏出身。
漢宣帝在吏治領域正本清源,對漢武帝的用人政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久久為功,終于革除了長期以來地方吏治中存在的種種弊端,選任了一批勤于吏事、廉潔奉公、為民興利除害的“良吏”,為后世所稱道,也為中興漢室奠定了基礎。
反腐敗、矯嚴酷、平冤獄、整吏治,使得自漢武帝后期以來不斷激化的社會矛盾得到緩和,幾十年積累下來的嚴重社會危機得以平息,社會從動蕩中又逐漸走向穩定。
(選自《改革的教訓:打撈中國歷代沉沒的改革》,中信出版社。有刪節。作者現為《人民日報》頭版副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