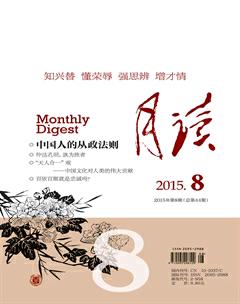四子侍坐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a。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夫子哂之b。
“求!爾何如?”
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赤!爾何如?”
對曰:“非曰能之,愿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c,端章甫d,愿為小相焉e。”
“點!爾何如?”
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f,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
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
曰:“莫春者g,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h,風乎舞雩i,詠而歸。”
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
三子者出,曾皙后。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
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曰:“夫子何哂由也?”
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唯求則非邦也與?”
“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唯赤則非邦也與?”
“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論語·先進》)
注釋:
a 子路:仲由,字子路,以政事見稱,為人伉直魯莽,好勇力,事親至孝。 曾皙:曾點,字晳,故稱曾皙,春秋末期魯國人,乃儒家“宗圣”曾參之父。 冉有:冉求,字子有,故稱冉有,尊稱冉子。他多才多藝,尤擅長理財,曾擔任季氏宰臣。 公西華:公西赤,字子華,又稱公西華,具有非常優秀的外交才能。
b 哂(shěn):微笑。
c 會同:古代諸侯會盟和朝見天子。會,諸侯不定期朝見天子,后來兩諸侯國君相見也叫會。同,眾諸侯一起定期朝見天子。
d 端:一種禮服。 章甫:一種禮帽。“端”和“章甫”這里都是名詞做動詞。
e 相(xiàng):在祭祀或盟會時主持禮贊和司儀的人。又分大相和小相,卿大夫主持禮贊,稱為大相,士主持禮贊,稱為小相。
f 作:站起來。
g 莫春:即暮春、晚春。莫同“暮”。
h 沂:水名,在今山東曲阜市南。
i 舞雩(yú):魯國求雨的壇,在今山東曲阜東南。古代求雨之祭,叫“雩祭”,因求雨時巫人會在壇上歌舞,故稱舞雩。
大意: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陪孔子坐著。
孔子說:“不要因為我年紀比你們大一點,就約束而不敢暢所欲言。(你們)平時總說:‘沒有人了解我呀!假如有人了解你們,你們打算怎么做呢?”
子路急忙回答:“一個擁有一千輛兵車的國家,夾在大國之間,受到別國軍隊的侵犯,接著又遇上饑荒;如果讓我去治理這個國家,等到第三年,就可以使人民勇敢善戰,而且還懂得遵守
禮義。”
孔子聽了,微微一笑。
(孔子又問:)“冉求!你怎么樣?”
(冉有)回答說:“一個縱橫各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的國家,如果讓我去治理,等到第三年,就可以使老百姓富足起來。至于禮樂教化,那就只有等待君子了。”
(孔子又問:)“赤!你怎么樣?”
(公西華)回答說:“我不敢說能做到什么,但我愿學著去做。在宗廟祭祀,或者諸侯會盟、朝見天子時,我愿意穿著禮服,戴著禮帽,做一個小相。”
(孔子又問:)“曾點!你怎么樣?”
曾晳彈瑟正接近尾聲,瑟聲漸漸稀疏下來,“鏗”的一聲,他把瑟放下直起身來,回答說:“我和他們三人的志向不一樣。”
孔子說:“那有什么關系呢?不過是各自談談自己的志向
罷了!”
(曾晳)說:“暮春時節,穿上春天的衣服。我和五六位成年人、六七位少年,到沂河洗澡,在舞雩臺上吹吹風,再一路唱著歌走回家。”
孔子長嘆一聲說:“我贊成曾點的想法呀!”
子路、冉有、公西華都出去了,曾晳最后走。曾晳問孔子:“他們三個人說的話怎么樣?”
孔子說:“也不過是各自談談自己的志向罷了!”
(曾晳又)問:“您為什么笑仲由呢?”
(孔子)回答:“治理國家要講禮讓,可他的話卻一點不謙虛,所以笑他。”
(曾晳問:)“難道冉求所講的不是國家大事嗎?”
(孔子回答:)“怎見得縱橫六七十里或者五六十里的地方就不是國家呢?”
(曾晳問:)“公西赤所講的不是國家大事嗎?”
(孔子回答:)“宗廟祭祀、諸侯會盟、朝見天子,不是諸侯國的大事又是什么?(公西赤是個十分懂得禮儀的人,但他只說愿意學著做一個小相。)如果公西赤只能做小相,那么誰來做大相呢?”
【題解】
“四子侍坐”是《論語》中少有的具有完整故事情節的一章,也是孔子的“課堂實錄”。它以言志為主線,將孔子師徒的言談舉止生動地展現出來,從中我們可以觀察到子路、冉有、公西華、曾晳這四位孔子高足各自的性格特點,以及儒家“足食足兵”“禮樂治國”的政治思想。子路性格直率、信心十足,卻失之于魯莽,不懂得謙遜,因此受到孔子的哂笑;冉有為人謙虛、實事求是;公西華敏而好學,但過于謙遜而趨向保守,孔子希望他再自信一些;曾晳灑脫,淡泊于功名,他的話似乎與政治無關,其實描繪的是一個太平社會的縮影,即形象化的禮樂之治的盛世,這與孔子的思想最為契合。
整個對話中,孔子始終沒有以“師者”和“長者”自居,而是作為一位傾聽者、對話者和啟發者,這給教學帶來一種平等、輕松、和諧的氣氛,使學生們能夠毫無保留地暢談自己的理想,發表自己的看法,提出自己的疑問,學生的主體性由此得到體現,而孔子作為教育家的風范,及其循循善誘的教學態度也展露無遺。(高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