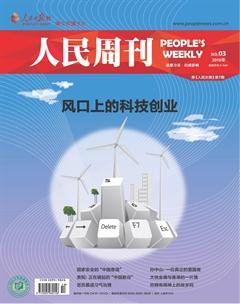國家安全的“中國意蘊”
郭思遠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新一屆黨中央,為進一步完善國家安全體制和國家安全戰略,確保國家安全,決定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去年4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首次提出了“總體國家安全觀”概念。
今年1月23日,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國家安全戰略綱要》。在5月15日全國國家安全機關總結表彰大會上,習近平再次強調國家安全工作的重要性。習近平指出,要“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堅定理想信念,忠誠黨的事業,與時俱進開創國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國家安全乃國之根本,是安邦定國的重要基石,是每個中國人的共同利益。在認真領會習近平總體國家安全觀的“中國意蘊”的基礎上,構建總體安全體系,這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迫切要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要保障。
新國家安全觀的“中國意蘊”
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事而制。習近平總書記新國家安全觀應運而生,創造性地提出了總體國家安全觀,并具體闡述了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具體內涵。習近平在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指出:“當前我國國家安全內涵和外延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豐富,時空領域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寬廣,內外因素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復雜,必須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
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院教授吳楚克接受《人民周刊》記者采訪時認為:“從伊拉克安全戰爭開始到阿富汗戰爭結束,國際安全局勢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國也在不斷調整自己的安全戰略,但是并沒有形成有創新意義的宏觀政策。經過這么一段時間的發展,習總書記的新國家安全觀才逐步形成和發展完善。我們現在面臨的安全形勢不僅越來越嚴峻,而且產生了新的爭議地區和安全威脅,如果不系統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的話,在應對周邊態勢和非傳統安全威脅時,就不能迅速有效合法地采取重大安全措施,國際和國內輿論也認為領導層面沒有對當前的總體安全形勢作出準確回應。從時機上來說,此時宣示習總書記新國家安全觀也是國際政治經濟形勢發展的必然反應。”
總體國家安全觀是一個宏觀概念,包括了安全的方方面面。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所研究員李少軍說:“總體國家安全觀就是綜合的、宏觀的、把方方面面都照顧到的一種安全思想。這種思想的出發點是以人為本,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在他看來,總體國家安全觀的要旨是把國家安全視為一個整體,既考慮國內安全,也考慮國際安全;既包括傳統安全,也包括非傳統安全;既立足于國家安全,更立足于人民安全。作為頂層設計,它的宗旨是指導和統籌協調安全的全局,哪個方面都不忽略。
李少軍對《人民周刊》記者稱:“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提出,需要人們轉變觀念,即不一定非要確定一個主要矛盾或主要問題,因為現在國家面臨的安全形勢非常復雜,涉及全球、地區、國家乃至公民個人的不同層面,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社會、生態等多個領域。由于各種安全問題已交織在了一起,因此制定安全戰略必須要有總體觀,不能把它們割裂開來。有了總體的安全戰略設計,才能適宜地處理不同時間點的比較突出的安全問題。”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梁云祥說:“中國的新國家安全觀就是考慮到方方面面的利益,不是說我強大了,我壓服你了,就是安全。新國家安全觀新就新在共同,只要是地球上的任何一個國家,都應該有安全的權利。不過這樣的目標太過于美好和宏觀,越美好的東西實現起來就越難,自古以來,哪個國家不想安全,只不過以前的國家安全是建立在壓服你、消滅你基礎之上的。現在的追求是我們誰都不要消滅誰,我們共同生活在地球上,平等相待,這就是中國特色的新國家安全觀。”
“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概念本身具有中國特色,是中國概念,而總體安全在體系架構和具體內涵上,也體現出明顯的中國特色,這就是習近平指出的,中國的總體安全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以經濟安全為基礎,以軍事、文化、社會安全為保障,以促進國際安全為依托,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葉自成在《習近平總體安全觀的中國意蘊》一文中如此指出。
葉自成認為,習近平的總體國家安全觀具有其“中國意蘊”。首先,安全意識就是憂患意識,習近平曾指出,要增強憂患意識,做到居安思危,是我們治黨治國必須始終堅持的一個重大原則;其次,安全意識就是防止危險,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安與危是分不開的,所謂安全就是沒有內外的危險;最后,安全意識是整體意識、全局意識,中國的《易經》有鮮明的整體思維,《管子》等經典則強調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一體。
政治安全是總體安全的根本
“當前,我國正處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時期,面臨復雜多變的安全和發展環境,各種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因素明顯增多,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任務繁重艱巨。”習近平在全國國家安全機關總結表彰大會上如此指出,同時還提出各級黨委和政府要重視、理解、支持國家安全機關工作,同心協力開創國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葉自成認為,中國總體安全突出政治安全,把政治安全作為中國總體安全的根本。中國是一個大國,國情超巨復雜,處理好國內的政治問題是國家政權最重大的安全問題。如果中國不能保持政治秩序的正常運行和政治穩定,一切安全問題都將是空談,相反,在政治安全良好狀態下,其他的安全問題相對容易解決。中國把政治安全確定為總體安全的核心,反映了中國維護國家政治安定、穩定、有序、和諧的復雜性、長期性、艱巨性和內向性。
他說:“中國的總體安全是把人民安全作為國家安全的宗旨。所有的安全問題,歸根到底是由人民來感受、決定和評價的,任何不安全最直接影響的首先是廣大的民眾。國民安全是以民為本思想在安全領域的拓展。”
解放軍南京政治學院院長蔣乾麟曾經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政治安全關系到國家、政府系統和意識形態的穩定性、合法性。政治體系是否存在顛覆性威脅是政治安全的基礎性前提。在全球化日益發展的今天,實現政治安全必須做到國家主權獨立、國家政權穩定、政治意識形態包容、政治制度合適、執政黨執政地位鞏固、政治秩序良好。實現政治安全必然要求確保政治穩定與政治發展共舉、政治有序與有效并重。
蔣乾麟說:“政治安全不僅關系到國家的長治久安,更與民族復興和人民福祉休戚相關。在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文化多樣化、利益多元化的今天,社會上的確存在淡化甚至忽視政治安全的傾向,把政治安全歸為執政黨的事、政府的事、領導干部的事。”
如何增強憂患意識,做到居安思危?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主任任天佑認為,強烈的憂患意識、清醒的底線思維、勇毅的擔當精神是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應有的精神境界。強化憂患意識、底線思維和擔當精神,必須與強化戰略定力結合起來。離開戰略定力,極易導致“神經過敏”和戰略誤判,落入敵對勢力設置的陷阱。
任天佑分析稱,當前,無論外部干擾如何變換花樣,我們都要緊緊扭住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這個戰略目標和時代主題,始終高度警惕國家被侵略、被顛覆、被分裂的危險,改革發展穩定大局被破壞的危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進程被打斷的危險。這樣就能在壯大實力的同時,強固安全底線,提升安全系數。
非傳統安全威脅更為突出
從廣義上講,國家安全包括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傳統安全指的是主權國家所面對的政治軍事安全。人們通常把這種安全界定為保衛國家免受外來的顛覆與攻擊。非傳統安全則是指傳統安全以外的其他安全。涉及這種安全的問題非常復雜,種類繁多。李少軍說:“對非傳統安全進行界定很難。如果畫一個圓,內圓就是傳統的政治軍事安全,而外圓就是非傳統安全。非傳統安全涉及金融危機、恐怖主義、氣候變暖、能源、健康等很多方面。在理論上,非傳統安全可以說包括了政治軍事安全問題以外所有已知和未知的安全問題。”
李少軍認為,盡管在當代非傳統安全問題凸顯,但不能籠統地比較傳統安全威脅與非傳統安全威脅哪個更大。國家在不同的時期肯定會面對著不同的突出問題,但在戰略上必須把這兩類安全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
“相比傳統安全威脅,非傳統安全威脅正成為威脅安全的主要方面,因為傳統安全威脅是能看清楚的,我們可以根據對手的情況做好應對準備,而非傳統安全威脅核心是指在國家綜合力量發展越來越不平衡的情況下,利用信息、交通和輕便的突防手段對國家重要的設施、機構、人員進行戰爭和恐怖威脅,除此之外,對國家金融、能源、運輸、信息、航空航天和文化的安全威脅正成為非傳統安全威脅的主要方面。比如信息安全中輿論被有意操控,對突發事件的惡意引導,特別是民族地區發生極端宗教和恐怖事件,對正常的社會生活秩序破壞力強,造成的社會恐懼心理影響面大,應該說背后都有一只看不見的手。”吳楚克如此說道。
梁云祥認為,目前中國面臨的最主要安全威脅是非傳統安全威脅,比如糧食、石油等資源不夠用,或爆發恐怖主義活動,或國家信息安全泄露等。另外,環境安全也比較重要,因為中國近幾十年的快速發展,已經造成了很多環境問題,現在雖然已經開始治理,但不可能一下子完全治理好,這就潛伏著一些危機,不知道什么時候就爆發,比如河流污染、地下水污染、大氣污染等,這些問題不出事的時候就沒事兒,一出事就是政府危機。
自從美國爆發“棱鏡事件”以后,全球都在關注信息安全。對于信息安全威脅,梁云祥說:“因為現在是一個信息時代,不管硬件配置得多么好,信息是一個溝通的工具,如果沒有信息安全,所有的硬件都會癱瘓。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信息安全是一根神經,是聯結各個領域安全的不同神經系統。現代社會信息越發達,信息安全的作用就越重要,如果說信息都不能由自己控制,一旦發生戰爭,網絡系統就會立刻癱瘓,比如導彈、航空母艦等就發揮不了作用。”
國際社會應建立“安全共同體”
安全總是一定關系的產物。就國家安全而言,如果只有一方感覺到安全,另一方感覺不到安全,那么感覺到安全的一方也不會有真正的安全。“即使你有很大的軍事優勢,也未必有安全。不接受安全現狀的國家即使不向你發動實際的挑戰,你也仍然面對著不安全問題。就像以色列,軍事上很強大,周邊的國家都不是對手,但以色列從來沒有感到安全,因為周邊國家都不同意它的存在。”李少軍說,“在國際關系中,國家必須實現共同安全,即建立一種各相關方都同意的安全結構。如果說合作安全主要是一種手段,那么共同安全則是一種安全模式。”
從實現途徑講,實現共同安全即得到各方同意,最終是需要經過談判的。要談判,就要有一個大前提,即各方要處于主權得到尊重的正常狀態。李少軍認為,如果進行安全互動的國家處于主權原則得不到尊重的非正常狀態,那就沒有談判的基礎,即使有國家費力組織會談,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結果。在這種情況下,國家互動只能先謀求關系的正常化,然后才談得上謀求同意和“共同安全”。在這里,是否存在正常的國家關系狀態構成了能否推動“共同安全”進程的判斷標準。觀察當今的國際關系,可以看到,國家間破壞主權原則的事態是很常見的,因此,國家在很多時候是需要為建立正常的國家關系而斗爭。
“中國正在崛起,自身也需要發展,利益也在擴大,但也會給國際社會帶來一些所謂的‘中國威脅論’。安全是國際關系中永恒的主題,任何國家任何時候都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中國的新安全觀既要考慮自己的利益,同時也要照顧對方的利益,這就是所謂的‘共同安全’。”梁云祥說,“‘共同安全’只是一個原則而已,就像我們說人和人之間都應該友愛一樣,但是自有人類以來,能說人與人之間都是友愛的嗎?但這是人類追求的共同目標,只有共同都感覺到安全了,才有所有國家的安全,因此只能在首先追求自己安全的前提下一步一步地去實現。”
對此,葉自成認為,國際社會應建立以共同安全為目標的“安全共同體”。近年來,習近平的講話不斷提到“命運共同體”的概念,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的講話中,習近平又提出了“安全共同體”的問題,指出中國的安全必須既重視自身安全,又重視共同安全,打造命運共同體,推動各方朝著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標相向而行。“安全共同體”是對過去的共同安全的發展,也是命運共同體在安全領域的運用。
構建總體安全體系的頂層設計
“構建總體安全體系要有頂層設計,建立國家安全委員會是構建總體安全的第一步。要完成總體安全的構建還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葉自成認為,首先,應該有一個能夠反映中國安全形勢特點、任務、宗旨、目標的國家安全戰略。同時,應從文化入手,強化國家、社會、國民的安全意識。安全不僅關系到國家命運,也關系到每個國民的命運。國民不僅是國家安全的最終受益者,也是維護國家安全的強大動力。應當強化國民的安全意識,形成凡是危害國家安全、國民安全的,自覺進行抵制;凡是有益于國家安全、國民安全的,自覺進行維護。不做危害國家安全和國民安全的事情,從小事做起,從自己做起,從自己從事的工作做起。
就如何構建總體安全體系的頂層設計,梁云祥認為,在做頂層設計的時候,首先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要共同重視,過去人們更多的是關注傳統安全,航母下水,導彈上天,這些都是必須的,但是不全面,要讓老百姓了解到日常生活的安全也是國家安全的一部分,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都是同等重要。其次,法律的整備也非常重要,比如建立國家安全委員,就應該從法律上規定得非常細,比如職能是什么,權限是什么,什么問題歸它管,什么問題不歸它管等。
對此,吳楚克認為,構建總體安全體系的頂層設計,首先還是要以國家周邊安全為重點,解決臺灣問題是中國周邊安全的關節點,極大地影響南海問題、釣魚島問題的解決;第二是應該把現代的網絡技術手段,作為國家安全的重要方面,要對網絡傳播有一個總體的把握,這個把握不是控制,而是讓我們正確的網絡傳播占主流;第三是應該在國家各個層次的教育中,進行國家安全教育;第四是在科研、軍工生產、邊疆一線等領域給予政策傾斜,要讓那些有愛國之心、能夠報效祖國的人得到應有的地位和利益。
吳楚克對《人民周刊》記者說:“總體安全不是相安無事,大家都平安下來,這是不可能的,更不是不打仗我們就安全,我覺得這是對安全的錯誤理解,所以,總體安全應該是采取積極的態度,全方位調動中國人民的愛國熱情和愛國之心,擰成一股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