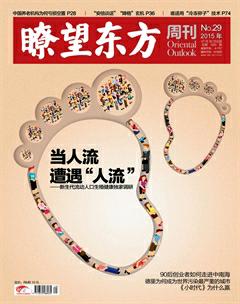中國需要精明增長
齊岳峰
中速增長對于中國的今后發展是精明增長、佳好增長、通向世界經濟強國的增長
盛夏的午后,天慢慢轉陰,雨幕很快遮住了窗子。
75歲的陸大道對此似乎毫無察覺,他坐在輪椅上,聽取弟子們關于“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支撐系統”的分析與建議。
2014年,相關部門啟動關于國家“十三五”發展規劃問題的研究。陸大道與同事們也對此開展預研究。
他告訴《瞭望東方周刊》,高速增長的經濟為中國帶來了長期利好,但長期追求高增長率,也為社會發展帶來了一系列問題。環境和自然資源已經支撐乏力,調整經濟增速的預期非常重要。
近些年他多次發出類似的呼吁。他說自己的動因是“地理學者要有國土情懷和國家情懷”。
“癌癥村”猛于“水俁病”
《瞭望東方周刊》:根據你的研判,中國長期高速而低效的經濟增長,已經引發結構性困境。1998年與2008年之后的兩次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在保障經濟增速的同時,造成了過剩的產能,透支了部分增長因素和環境承載力。環境承載力的透支,情況究竟如何?
陸大道:中國環境污染的態勢很嚴峻。具體來說,霧霾的影響范圍遠遠超出了1952年的“倫敦霧”,而水污染及其影響比霧霾更嚴重。嚴重的土壤污染正在快速使部分優質耕地喪失生產功能。“癌癥村”分布于中國中部、南方、西南、川陜甘的許多河流中下游——就其涉及的地理范圍、人口規模、對居民生命和健康的摧殘及對社會經濟的影響,都遠遠超過了上世紀50年代日本的“水俁病”。
現階段,中國的環境和生態系統,已經無法繼續承載高速的經濟增長和大規模空間擴展的城鎮化。
如果不能從經濟增速、結構和發展模式方面解決問題,環境污染還可能進一步加劇,而這已成為廣大民眾的沉重負擔,也是對黨和政府執政能力的重大挑戰。
《瞭望東方周刊》:如你所言,長期依靠自然資源過度消耗,將為中國帶來怎樣的影響?
陸大道:自然資源的過度消耗,可能帶來嚴重的國家安全問題。近十多年來中國的能源和礦產資源消費總量達到驚人的規模,對世界資源的高度依賴,特別是進口大量的優質能源和大宗礦產資源(原油、鐵礦石對國外依賴度已經達到70%,銅、鋁等礦石和天然氣對外依賴度也將很快達到50%以上),將使國家面臨巨大的地緣政治壓力。
不可否認,長期進行低端產品生產的“世界工廠”模式,以及依賴投資拉動的發展模式,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理念和支撐。但這種模式也引起了國內重要資源的加速消耗,并導致“世界在污染中國”,以及經濟效益低、國內競爭國際化、加深國民經濟結構性困境等問題。目前看來,建立在高消耗、高污染基礎上的發展模式已不可持續。
中速增長是精明增長
《瞭望東方周刊》:你擔任組長的中國科學院學部咨詢項目組認為,中國經濟進入中速增長(年增長率在6%~4%)已是必然趨勢。你說過,中速增長對于中國的今后發展是精明增長、佳好增長、通向世界經濟強國的增長。為何經濟中速增長反而是好事?
陸大道:這其實是一個經濟發展速度與國家競爭力/影響力之間的關系。國家影響力與全球化的推動進程相關。15世紀地理大發現以來,全球已經發生了三次世界權力轉移或更替,每一次都重塑了全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而支配權力分配的國家往往是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國家。
比如,伴隨第一次權力轉移開始的歐洲崛起,伴隨第二次權力轉移開始的美國崛起。
而今,世界正經歷著第三次權力大轉移。期間,伴隨著重要國家經濟增長速度的變化,相關國家對世界的影響力也在同步變化。我們看到,英國在1831~2013年的180多年間,經濟增速波動不大,除1936~1940年之間發生過一次10個百分點以上的高速增長外,其余年份大多維持在5個百分點左右。
我們發現,經濟超高速及高速增長的國家,往往是競爭力較低的國家,并處于全球平均水平以下。經濟的超高速及高速發展,往往帶來民生、社會、環境等問題,導致國家競爭力下降。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國家里,僅中國保持著較高的競爭力。
《瞭望東方周刊》:如果中國經濟進入中速增長模式,對能源礦產資源的依賴是否會有所減輕?
陸大道:即便在中速增長模式下,中國仍然需要龐大的能源礦產資源的支撐。美、日等發達國家在其快速工業化階段,也曾出現經濟總量和能源礦產消費同步增長的趨勢。
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尚未完成,人民生活水平還處于持續提高階段。1970年,美國的人均GDP已經達到20000美元,城鎮化率73%;而目前中國的同比數字分別是3500美元、不足60%。因此,中國的工業化和城鎮化還需要繼續推進,社會經濟發展對能源與礦產資源的需求還將繼續增長。
在經濟中速增長情景下(2015~2020年GDP年均增速6%,2020~2030年5%),2020年能源消費規模將達到46.8億噸,2025年和2030年將分別達到55億噸和60億噸。
效益放在最主要位置
《瞭望東方周刊》:你提出,只有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結構優化和發展效率的提高,才能確立“我們所希望建立的新常態”。并建議制定包括GDP在內的一組指標,綜合衡量國民經濟發展的實際績效。比如,你提出“三維目標”,將經濟增長、社會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三者同步,作為國家發展的三個主要目標,這是否有實現前景?
陸大道:大國在工業化初期與中期,若謀求經濟快速增長,只有實行不平衡發展策略。只有到了高度發展階段,才可能縮小地區差距。從這一點來看,改革開放前些年優先保證沿海地區增長,是符合全國利益的。
事實上美國各州人均經濟實力差距也很大。
中國自“十一五”開始就不提“取消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差距”了,事實上這種目標是達不到的,各地區經濟實力差距縮小并不符合全國人們利益。
目前這個階段,尤為緊迫的是環境問題。否則,經常性出現的環境危機,將變為社會危機。
現在來看,中國對世界的依賴程度太高,而出口則在不斷下降。
中國能否迅速輸出資本、輸出產能,并進一步推進全面開放,是關系到中華民族能否崛起的大問題。
《瞭望東方周刊》:以前我們也提“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這與你提到的“資源節約型社會經濟體系”有何異同?
陸大道:中國歷來重視這個問題,但我們現在的資源利用效率與單位GDP排放,在世界范偉內都是比較高的。
各地很明顯仍然只注重GDP,不注重環境。因為降低基礎設施建設速度,會影響經濟增長速度。而淘汰落后產能,地方上更受不了,于是客觀上就把環境問題放在次要位置了。
我所提到的“資源節約型社會經濟體系”,與30年前我們提出的資源節約型社會,在理念上一脈相承,但內涵上有變化——現在資源能源的形式與當時不同、緊迫程度亦有區別。
這個過程中始終存在一個質疑:中國為何不用綠色GDP統計國民經濟?
數十年前,“里約大會”上提出“綠色GDP”,這種提法要扣除生態成本。也就是說,被污染的環境要恢復原貌。且綠色GDP的統計數值,要比現在中國慣用的GDP統計數值小得多,各地分歧很大。
世界銀行曾就此作過類似研究:1978年印尼名義上的GDP是7%,但按綠色GDP核算后卻是4%。要承認這樣的落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更何況,在中國,有些地方的GDP統計,原本或許就存在一些浮動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