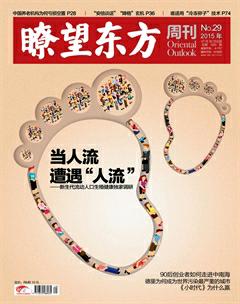馬宏杰:中國底層的影與像
鄭秋軼
“沒有一個人悲觀,這是民間的生存智慧”
《西部招妻》,一個主角是殘疾人老三,數次去寧夏買妻,花光了積蓄。《中國國家地理》攝影師馬宏杰拍了30年。
他拍老三,既沒有譴責,也沒有頌揚,只是觀察。實際上,老三是馬宏杰的親戚,他也幫過老三不少忙。
馬宏杰記得,母親有個女同事來自四川,口音顯得孤獨而奇怪。她是被買來的。1984年,馬宏杰第一次拿起相機時,這個四川女人的形象就浮現出來。恰在這時,老三出現了。他跟著老三到處相親,一路上發生了許多辛酸事。
2008年,老三的故事在媒體上發表,馬宏杰卻收到一封來自湖北的信。那里有個青年劉祥武,有同樣的需求,想請馬宏杰“帶路”。
馬宏杰見了劉祥武。“我會一直關注他和老三,想看看這個社會能給他們帶來多大的變化。”劉祥武后來成了《西部招妻》的另一個主角。
老三和劉祥武,以及他們代表的人,一直是馬宏杰的描述對象。
2015年夏,馬宏杰專門拍攝中國家庭的作品《中國人的家當》出版。而幾個月前,他那部拍了12年的《最后的耍猴人》剛剛引起知識階層的轟動。
現在,他又“拍了一個大選題,比前幾本書都要震撼。涉及中國人怎么對待自己的劣勢、命運。”
走近“底層人”
很多時候,是一個瞬間決定了馬宏杰要用幾年、十幾年去拍攝一個人、一群人。
2001年6月的一天,馬宏杰在洛陽街頭拍攝,看到幾個身背猴子的人在趕路,就此對這群人產生了興趣。
經人引見,他接觸到耍猴人老楊。老楊最初并不信任他。直到馬宏杰跟他們一起從襄陽扒火車到成都,再扒回來,老楊才對他敞開心扉。
扒火車時,馬宏杰給自己買了保險。“后來才知道,扒火車本來就是違反條例的,真要出了事,保險公司也不會賠。”
馬宏杰跟著耍猴人去跑江湖。除了同吃,他們還一起睡高架橋下。下雨了,老楊和同伴給馬宏杰騰出一塊地兒,鋪上塑料布,把他夾在中間。攝影包和相機裝在編織袋里,枕在頭下。
有一天,老楊收到50元假幣,心情不好,蹲在窩棚邊吃飯。大公猴撿起一塊石頭扔到鍋里,把一鍋飯打翻了。祖上傳下的規矩,每天演完戲,猴子都是要吃第一碗飯的。這一天,老楊忘了。
馬宏杰還拍到一張照片:耍猴人的妻子用自己的乳汁給小猴子喂奶,小猴子親吻她。
耍猴人經常被當作“盲流”驅趕。有時會被沒收“作案工具”。有一次,猴子被收走了。幾天后,當耍猴人費盡力氣找到猴子時,已是僵硬的尸體。耍猴人跪在地上,哭得呼天搶地。
老楊的兒子結婚,作為朋友,馬宏杰去了,送了紅包。2015年3月,《最后的耍猴人》新書發布會,老楊帶著猴子來到現場,還表演了一段猴戲。
馬宏杰在內心深處,對這些“底層人”有著強烈的認同和同情。
靠圖吃飯
1963年出生的馬宏杰,長于物質匱乏年代。小時候沒有留下一張照片。父親在洛陽玻璃廠上班。6歲時,他看到奶奶家的窗戶糊著紙片,那時他最大的愿望,就是給奶奶家的窗戶裝上玻璃。
中學畢業后,有個同學有了照相機。馬宏杰常和他去龍門石窟、白馬寺拍照。1984年,他花700元買了第一臺單反相機,開始自己沖洗照片。起初,他在田間地頭、車間里找素材。直到后來他看到外國大師的作品。
特別是某次,他在雜志上看到一組“喜馬拉雅采蜜人”的圖片,表達這些底層人的視角、手法、觀念都讓他震撼。他決定,一定要做這樣的攝影師。他相信自己能靠圖吃飯。
馬宏杰曾夢想做戰地記者。離這個夢想最近的時候,是在報社做記者的那些年。上世紀90年代,他先后在4家報社做了10年記者。剛開始,他很有正義感,后來發現自己的力量如此渺小。“當老百姓跪在我面前,把我當救命恩人時,我的內心承受不起。”
于是,他辭掉了工作,做起了自由攝影師。曾有一年,他拍了2000多個膠卷。那時是紙媒的黃金期,報社需要大量專題圖片。他每拍完一個選題,就刻成50張光盤,寄給50家報紙,采用率是90%。那幾年,稿費像雪片一樣飛來,收入不比上班低。后來,連郵局的人都認得他了。
2001年,一家雜志社的編輯到河南選圖片,馬宏杰帶來了50斤底片。幾天后,編輯告訴他,你拍的是《中國國家地理》的風格。兩年后,他就進入了《中國國家地理》雜志社,成為圖片編輯和攝影師。
十多年后,馬宏杰成了“馬老師”。他說,以后老了,打算從事攝影教育。
想摸摸中國人的家底
只是“一個人永遠走不出童年的影響”。馬宏杰說,他的攝影之路,源自對童年記憶的尋找。小時家里只有一張大床、一張小床、一個方桌和四條凳子,這些都是公家的。
后來,父親花10元錢買了一個收音機,是家里的第一件家當。兒時對“物”的記憶影響至今,他想摸摸中國人的家底。
《中國人的家當》一共拍攝了47戶人家。東到江南水鄉,西至帕米爾高原,北抵呼倫貝爾草原,南達三沙群島,分布在中國的每一個省份。馬宏杰用一張紹興水鄉人家的照片做了書的封面,理由是“比較有中國特色”。
拍之前,他會拿一些樣片給人看,人們一看,覺得不錯,就同意拍攝。有時也會遇到麻煩。在江蘇宜興拍運河人家時,正往外搬東西,鎮上的會計來了,堅決不讓拍,認為“有損形象”。
馬宏杰和朋友解釋無效。眼見就要動手打假,馬宏杰給當地宣傳部長打了一個電話,才平息沖突。
每戶人家,拍完都要做訪談。所拍人家中,收入最高的是河南朱仙鎮的年畫人家,托非遺保護的福,他家的年畫一年可帶來上百萬元的收入。收入最低的懸崖人家,則剛夠溫飽。
“就像很少人知道自己的血型。”馬宏杰說,“很多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家族歷史。”黑龍江某人家的故事讓他唏噓。故事主人公的父親是軍閥韓復榘手下的連長,1936年在一次戰斗中死了。此后家道中落,跟著母親闖關東。后來又經歷了各種運動、變故,人生跌宕起伏,“比電影還要精彩”。
《中國人的家當》有9萬多字的拍攝手記。楊錦麟說,馬宏杰的文字甚至比他的圖片還好看。他自己說,今后可以考慮出一本沒有圖、只有字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