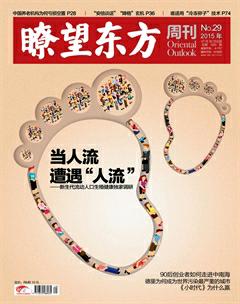修書人的“現(xiàn)代化”
王斯璇
2007年開(kāi)展中華古籍保護(hù)計(jì)劃之前,我國(guó)修復(fù)人員的最高學(xué)歷是大專,一個(gè)本科也沒(méi)有。只有中等專業(yè)學(xué)校在培養(yǎng)古籍修復(fù)人才
“修書人的學(xué)歷有沒(méi)有用?一定有。”國(guó)家圖書館副館長(zhǎng)、國(guó)家古籍保護(hù)中心副主任張志清開(kāi)口就一針見(jiàn)血地說(shuō)。
一次去南方的專業(yè)學(xué)校看古籍修復(fù)人才培養(yǎng),他意識(shí)到了這件事情的嚴(yán)重性。
那里都是十幾歲的孩子在學(xué)修書,“非常熱愛(ài),學(xué)得也很快”。他和其中一個(gè)手法極好的男孩交流。
“你在修什么書?”“不知道。”“這一頁(yè)有書名的,能給我指指嗎?”“不知道。”“你拿的這個(gè)補(bǔ)紙是什么紙?”“不知道。”
“他補(bǔ)的那一頁(yè)古籍的版心上就寫著書名——《資治通鑒長(zhǎng)編》。”張志清如今說(shuō)起來(lái),還有些神色黯然。
這其實(shí)是一種傳統(tǒng),或者說(shuō)是習(xí)慣。
國(guó)家圖書館古籍館研究館員、第四批國(guó)家級(jí)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項(xiàng)目古籍修復(fù)代表性傳承人杜偉生對(duì)《瞭望東方周刊》說(shuō),老師傅們沒(méi)上幾年私塾,十二三歲就出來(lái)了,“每天修書,師帶徒,也不上課,一切都是干活兒為主,來(lái)一個(gè)活兒告訴你怎么做,如果一輩子碰不上的,就不講了。”
再往前,直至明清時(shí),中國(guó)才有個(gè)叫周嘉胄的人寫了一部《裝潢志》,“這還是文人為裝裱寫的,不是師傅寫的。師傅寫不出來(lái)。師傅的技藝只能傳給兒子,連女兒都不傳。”在杜偉生看來(lái),中國(guó)從來(lái)沒(méi)有將修復(fù)古籍當(dāng)做一門學(xué)問(wèn)。
可是對(duì)于中國(guó)可能高達(dá)3000萬(wàn)冊(cè)的待修古籍,和它們對(duì)中國(guó)歷史文化的重要意義而言,所謂“修書匠人”,已經(jīng)不能滿足修復(fù)它們的需要了。
而把修書人的學(xué)歷“先提起來(lái)”,是這門學(xué)問(wèn)現(xiàn)代化的第一步。
快,再快,更快
“目前全國(guó)的漢文古籍?dāng)?shù)量超過(guò)4000萬(wàn)冊(cè)。”張志清說(shuō),“現(xiàn)在只普查到全國(guó)藏書單位的47%,太艱難了。”
這里的“古籍”,其定義是1912年以前寫印的、具有中國(guó)傳統(tǒng)裝幀形式的書籍。“如果把1912年以后出的民國(guó)書都算在內(nèi),絕對(duì)不止,可能漲一倍。”杜偉生解釋說(shuō)。
杜偉生已在國(guó)家圖書館古籍修復(fù)小組工作40余年,根據(jù)他和同事的經(jīng)驗(yàn),通常三分之一的古籍有破損,而破損的古籍中只有三分之一一定要修復(fù)。
“不是說(shuō)破損的一定就要修復(fù)。”張志清介紹,“一本破損古籍放在那兒,不會(huì)繼續(xù)破了就不用修復(fù)。有的酸化嚴(yán)重,紙張噼里啪啦往下掉,掉一個(gè)字兒都是損失,這就要搶救性修復(fù)。”
如今,全國(guó)收藏單位專門從事古籍修復(fù)的人已超過(guò)800人,較2007年國(guó)務(wù)院辦公廳發(fā)布《關(guān)于進(jìn)一步加強(qiáng)古籍保護(hù)工作的意見(jiàn)》以前翻了8倍。
但如杜偉生所說(shuō):“我們比大熊貓還珍貴,大熊貓還有2000多只呢。”
國(guó)圖古籍修復(fù)小組1953年建制。有些進(jìn)館的書破得不能上架,要簡(jiǎn)單整理,于是成立了這個(gè)組。
杜偉生進(jìn)入修復(fù)小組是1974年的3月,大專學(xué)歷,22歲,體重96斤。
那時(shí),他以退伍軍人的身份被分配到國(guó)家圖書館,二話沒(méi)說(shuō),馬上就來(lái)了,“我就覺(jué)得在部隊(duì)風(fēng)吹日曬,去圖書館能在屋里干活,已經(jīng)很不錯(cuò)了。”
1976年,杜偉生跟著師傅在故宮修從新疆出土的紙棺材,“紙糊的盒子,扣在尸體上,尸體腐化了,特別臟,光清洗就味兒死了。”
伴著滿屋子尸首味兒,師傅帶著杜偉生把紙棺材一點(diǎn)點(diǎn)揭開(kāi),拼成了幾十個(gè)卷子的文書。
當(dāng)年和杜偉生同來(lái)的另外3個(gè)人,兩個(gè)留下來(lái),一個(gè)去了別的單位。后來(lái)留下的也走了,“覺(jué)得這活兒沒(méi)意思,出去開(kāi)車了。”
按張志清所言,“這個(gè)行業(yè)當(dāng)初在圖書館界是被看不上的,因?yàn)槭墙橙恕!?/p>
這樣的工作在杜偉生口中,簡(jiǎn)化成“一天到晚就是跟破爛兒打交道。一支毛筆,一碗漿糊,一張紙。20個(gè)洞和200個(gè)洞對(duì)于我們都是一樣的”。
特別是“要求修得快,就盯著你干活,平均一天一本。只要你書拿出去上架是好的,能翻就行了,哪怕你補(bǔ)斜了。”他回憶說(shuō)。
直到上世紀(jì)90年代,杜偉生作為交流學(xué)者赴大英圖書館整理修復(fù)《敦煌遺書》時(shí),才第一次顛覆“快”的習(xí)慣。
“理念不一樣。”杜偉生說(shuō)。英國(guó)不要求快,修補(bǔ)一個(gè)檔案,分給四五個(gè)人一起做。杜偉生開(kāi)玩笑,“你們干活太慢了,這活兒我一個(gè)人全干了。”
當(dāng)年大英圖書館敦煌修復(fù)組組長(zhǎng)馬克,一個(gè)人修復(fù)868年雕版《金剛經(jīng)》前后用了7年。這在杜偉生看來(lái)太不可思議。“擱我兩個(gè)月都用不了,出活兒啊。”
馬克卻與他討論,某個(gè)破口是因?yàn)榫碜哟蜷_(kāi)時(shí)的力道還是紙張厚度的不同造成的,這會(huì)導(dǎo)致不同的修補(bǔ)方法。
“他們修和研究是統(tǒng)一的。”杜偉生說(shuō),“咱們是脫節(jié)的。干活兒的時(shí)候根本沒(méi)有研究的時(shí)間,干完了回家挺累的,沒(méi)有研究的念頭。加上入行要求也不高,初高中畢業(yè)就來(lái)了,直接限制了研究水平。”
修書也得有個(gè)總結(jié)
“1949年到1956年,修復(fù)國(guó)寶級(jí)的善本《趙城金藏》,15年,這么大的工程,沒(méi)留下一個(gè)字兒。”提起這些,張志清感到十分遺憾。
《趙城金藏》是金代山西民女崔法珍斷臂化緣、募資所刻的漢文大藏經(jīng)。因發(fā)現(xiàn)于山西趙城廣勝寺,稱為《趙城金藏》。
這部7000余卷的經(jīng)卷,與《永樂(lè)大典》、《四庫(kù)全書》、《敦煌遺書》都是單獨(dú)編號(hào),并稱國(guó)家圖書館四大專藏,外界稱為鎮(zhèn)館之寶。
“當(dāng)年《趙城金藏》藏在山洞里,拿出來(lái)時(shí)80%黑得跟碳棒一樣。怎么把它揭開(kāi)?碳如何去掉?在古紙上補(bǔ)的新紙是廣西的還是貴州的?一個(gè)字兒的檔案都沒(méi)留下。因?yàn)樵蹅兊膸煾敌W(xué)水平,動(dòng)起手來(lái)技藝極好,可就是不會(huì)總結(jié)。”張志清說(shuō)。
2007年,時(shí)任國(guó)圖善本特藏部主任的張志清,在全國(guó)古籍部主任會(huì)議上提出了從本科學(xué)生入手培養(yǎng)古籍修復(fù)人才的設(shè)想,很多人反對(duì)。
某位老師說(shuō):“你想得太多了!干修復(fù)的是修復(fù)工人!你告訴他怎么做就完了,還本科以上?根本用不著,中專就行了!”
這樣的情景讓張志清回想起,當(dāng)年北大古典文獻(xiàn)專業(yè)也經(jīng)歷過(guò)不被視作學(xué)問(wèn)、評(píng)不上職稱的往事。
那時(shí)的質(zhì)疑是:“整理標(biāo)點(diǎn)、注釋翻譯,也算學(xué)問(wèn)?”
創(chuàng)立這個(gè)專業(yè)的文字學(xué)大家裘錫圭也不辯駁,只道:“我給你一本書,你試試看。”
古典文獻(xiàn)專業(yè)從北大、復(fù)旦起家,到2000年之后雨后春筍般在高校鋪開(kāi),再到大量古籍所的建立,一走便是30多年。“現(xiàn)在不也是二級(jí)學(xué)科?就算那時(shí)候也走過(guò)很艱難的路。”
如今的古籍保護(hù)修復(fù)遭遇同樣的境遇。首都圖書館館長(zhǎng)倪曉建倒是相當(dāng)支持張志清,在眾人反對(duì)中,一句“現(xiàn)在銀行前臺(tái)點(diǎn)票子的都是研究生,我們這么好的技藝都不如這個(gè)?”全場(chǎng)沉默。
敬畏還是要有的
“2007年開(kāi)展中華古籍保護(hù)計(jì)劃之前,我國(guó)修復(fù)人員的最高學(xué)歷是大專,一個(gè)本科也沒(méi)有。只有中等專業(yè)學(xué)校在培養(yǎng)古籍修復(fù)人才。”張志清回憶。
相比較,在日本,修復(fù)專業(yè)的研究生畢業(yè)后才可以從事古籍修復(fù)。英國(guó)倫敦兩所大學(xué)培養(yǎng)修復(fù)研究生,一半時(shí)間在課堂,一半時(shí)間在博物館、圖書館進(jìn)行修復(fù)實(shí)踐,沒(méi)有碩士研究生學(xué)歷不讓動(dòng)善本。
從2014年開(kāi)始,廣東中山大學(xué)、上海復(fù)旦大學(xué)率先招收古籍保護(hù)方向的專業(yè)碩士。時(shí)任復(fù)旦大學(xué)校長(zhǎng)楊玉良與張志清也進(jìn)行了商議。
“我提出的一些問(wèn)題他都可以從科技角度解決。”張志清回憶。“比如古籍除塵問(wèn)題,用抹布擦?書擦壞了。用吸塵器吸?書吸壞了。若用西方一種除塵機(jī),每本書要從機(jī)器上慢慢過(guò)一遍,也不切實(shí)際。”
楊玉良馬上提出“風(fēng)淋”的辦法。
“古籍修復(fù)是交叉學(xué)科,需要不同學(xué)科背景。” 張志清表示。
兩人一拍即合,楊玉良成立了第一家古籍保護(hù)研究院——復(fù)旦大學(xué)中華古籍保護(hù)研究院,準(zhǔn)備集合化學(xué)、物理學(xué)、材料學(xué)、文學(xué)、歷史學(xué)等多個(gè)專業(yè)學(xué)者參與古籍保護(hù)研究和人才培養(yǎng)。
如今,復(fù)旦大學(xué)首屆古籍保護(hù)方向?qū)I(yè)碩士預(yù)招生10人已全部報(bào)滿。每位學(xué)生將得到古籍保護(hù)中心的資助。張志清也希望保護(hù)行業(yè)解決就業(yè)出路,讓真正的古籍修復(fù)人才“在各個(gè)崗位上發(fā)揮作用”。
“知識(shí)層面決定你為什么修,如何修,未來(lái)再怎樣提高。”張志清強(qiáng)調(diào)。
不過(guò)張志清還是經(jīng)常面對(duì)質(zhì)疑:一個(gè)較為熟練的專業(yè)古籍修復(fù)師最多一年修100冊(cè),在古籍不繼續(xù)破損的情況下,要完成全部修復(fù)工作仍需數(shù)百年——“為什么不能培養(yǎng)幾萬(wàn)人?”
“古籍人才的培養(yǎng)要經(jīng)過(guò)艱苦的實(shí)踐過(guò)程,不可能幾年出大師。修復(fù)人才匱乏狀況在文物行業(yè)都有,修復(fù)青銅器、絲綢、陶瓷、書畫等,都會(huì)遇到人才匱乏問(wèn)題。”張志清說(shuō),“古籍保護(hù)中心近年培養(yǎng)了不少人,但百年樹(shù)人,需要實(shí)踐積累和鍛煉。”
而且“修書本身就是小眾東西”。杜偉生40多年也是堅(jiān)持這個(gè)“老理兒”。最基本的,“敬畏古人,敬畏古籍。大眾化之后,敬畏感沒(méi)有了,神秘感也沒(méi)有了,大家不當(dāng)回事兒了,就相當(dāng)危險(xiǎn)了。”
——評(píng)《中國(guó)現(xiàn)代化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