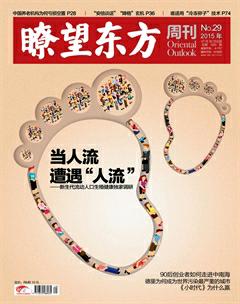螢火蟲之問:生態(tài)旅游何處去
楊天
這些活動(dòng)都將“數(shù)萬只螢火蟲集體亮相”“不設(shè)隔離,游客可以與螢火蟲親密接觸”等作為吸引游客的重點(diǎn)
7月的上海夜空,原本會(huì)出現(xiàn)螢火蟲點(diǎn)綴的“星空奇觀”。但這個(gè)“數(shù)萬只螢火蟲”點(diǎn)綴的“仲夏夜之夢(mèng)”還沒開始,就已結(jié)束。
7月9日,“上海首個(gè)螢火蟲主題公園”活動(dòng)開始的前一天,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分局官方微信“警民直通車松江”正式發(fā)布信息,稱“該項(xiàng)目未經(jīng)審批,存在重大安全隱患,現(xiàn)已被松江區(qū)相關(guān)主管部門勒令整改”。據(jù)上海本地媒體報(bào)道,該活動(dòng)2015年內(nèi)將不會(huì)在上海舉辦。
2015年夏天的這場(chǎng)活動(dòng)被擱置了,但一場(chǎng)由螢火蟲發(fā)端的關(guān)于生態(tài)旅游的討論卻蔓延開來。
螢火蟲為什么這么火
被叫停的上海螢火蟲主題活動(dòng)并非個(gè)例。
據(jù)本刊記者查詢,早在2010年,中國(guó)內(nèi)地城市開始有與螢火蟲相關(guān)的主題活動(dòng)。僅2015年,就有北京、上海、武漢、西安、鄭州、貴陽、南陽、湛江、宜昌等10多個(gè)城市計(jì)劃舉辦“螢火蟲主題公園”活動(dòng)。
對(duì)于螢火蟲,中國(guó)人似乎有著特殊的情感。然而,絕大多數(shù)在城市生活的人卻并沒有見過螢火蟲的廬山真面目。
華中農(nóng)業(yè)大學(xué)植物科技學(xué)院副教授、湖北省守望螢火蟲研究中心主任付新華,是中國(guó)第一位專門研究螢火蟲的博士。
2007年,他在北京香山植物園做過一次螢火蟲展覽,結(jié)果發(fā)現(xiàn),95%的城市孩子從沒見過螢火蟲,80%的成年人在近五年內(nèi)也沒有見過螢火蟲。
2010年,付新華和幾個(gè)武漢大學(xué)的學(xué)生在武漢市的一次街頭調(diào)查中發(fā)現(xiàn),74%的受訪者不知道螢火蟲是什么。
廣東螢火蟲保育協(xié)會(huì)會(huì)長(zhǎng)、廣州南湖螢火蟲公園負(fù)責(zé)人許松告訴《瞭望東方周刊》,“近年來,水污染、土壤污染、光污染、河道工程建設(shè)、外來生物入侵等問題使很多螢火蟲棲息地遭到嚴(yán)重破壞,許多地方的螢火蟲減少乃至消失,大多數(shù)人沒有機(jī)會(huì)見到螢火蟲,所以,專門的螢火蟲主題活動(dòng)才會(huì)如此火爆。”
環(huán)保之爭(zhēng)
與這些螢火蟲主題活動(dòng)的前期高調(diào)宣傳和公眾翹首期待相左的是,這些活動(dòng)舉辦的實(shí)際情況大多不盡如人意。
幾乎在上海螢火蟲主題活動(dòng)被叫停的同時(shí),鄭州有關(guān)部門因安全原因叫停了當(dāng)?shù)匾患疑虉?chǎng)的螢火蟲放飛計(jì)劃。而原定于7月17日在北京朝陽區(qū)郁金香花園舉行的螢火蟲展,也被無限期推遲。
本刊記者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近年來,各城市螢火蟲主題活動(dòng)被叫停,除了安全隱患和客流量大等“客觀”因素外,對(duì)商家主辦類似活動(dòng)的“主觀”動(dòng)機(jī)和會(huì)否對(duì)環(huán)境構(gòu)成傷害的質(zhì)疑,成為活動(dòng)舉辦受阻的重要原因之一。
有相關(guān)業(yè)內(nèi)人士透露,這些活動(dòng)都由同一個(gè)團(tuán)隊(duì)在經(jīng)營(yíng)和策劃。從前期宣傳來看,這些活動(dòng)都將“數(shù)萬只螢火蟲集體亮相”“不設(shè)隔離,游客可以與螢火蟲親密接觸”等作為吸引游客的重點(diǎn)。
上海“螢火蟲主題公園”活動(dòng)主辦方負(fù)責(zé)人此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shí)表示,原計(jì)劃來上海“作客”的螢火蟲來自湖北、江西和云南,其中湖北的蟲源為人工養(yǎng)殖,而江西和云南的蟲源既有人工養(yǎng)殖,亦有野生采集,具體比例不明。
付新華認(rèn)為,螢火蟲的人工繁殖并不容易,國(guó)內(nèi)掌握技術(shù)的人并不多,能夠大規(guī)模繁殖的更少,因此,商業(yè)活動(dòng)為了逃避環(huán)保質(zhì)疑而聲稱的人工繁殖幾乎都是野外捕捉的。
大量捕捉成蟲后的野生螢火蟲,不僅會(huì)影響蟲源地的螢火蟲繁殖,導(dǎo)致種群基因庫縮小,引起基因滅絕,整個(gè)種群也可能消亡。而通過食物鏈,螢火蟲的消亡會(huì)影響到整個(gè)生態(tài)系統(tǒng)的平衡。對(duì)放飛地而言,如果放飛地沒有該品種的螢火蟲,也可能造成生物入侵。
“這樣的活動(dòng)本質(zhì)上就是對(duì)螢火蟲的殺戮。”南京青環(huán)志愿者服務(wù)中心負(fù)責(zé)人、環(huán)保志愿者朱翔宇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朱翔宇所在的青環(huán)志愿者服務(wù)中心從2010年起就開始關(guān)注和保護(hù)螢火蟲。據(jù)他介紹,目前他們對(duì)螢火蟲保護(hù)的基本模式是:得知螢火蟲活動(dòng)信息-網(wǎng)上聯(lián)名抵制-聯(lián)系當(dāng)?shù)刂驹刚呓M織和媒體,向活動(dòng)主辦方和政府有關(guān)部門施壓-叫停活動(dòng)。在他看來,叫停活動(dòng)并不是他們的目的,保護(hù)螢火蟲、保護(hù)環(huán)境才是根本目的。
與其他城市的“螢火蟲主題公園”活動(dòng)被屢屢叫停不同,許松一手建立起來的廣州南湖螢火蟲主題公園則得到了環(huán)保人士的青睞。
許松向本刊記者介紹,他所經(jīng)營(yíng)的廣州南湖螢火蟲主題公園面積約二三十畝,主要進(jìn)行螢火蟲復(fù)育保育和相關(guān)生態(tài)旅游項(xiàng)目的開發(fā)。
“這和其他城市的所謂螢火蟲主題公園完全是兩回事。”許松說,他們不是把螢火蟲抓回來直接放在大棚里供游客觀賞,然后任其死去,而是通過前期環(huán)境的培育改善整個(gè)生態(tài)環(huán)境,包括水源的改良、植被的復(fù)育、幼蟲的投放等等,從而對(duì)螢火蟲進(jìn)行復(fù)育和保育,“整個(gè)過程中環(huán)境營(yíng)造投資相當(dāng)大。”
復(fù)旦大學(xué)助理研究員、環(huán)保志愿者裴鵬也贊同這種做法。他認(rèn)為,目前觀螢活動(dòng)要發(fā)展,當(dāng)務(wù)之急是環(huán)境的培育而非從外地大量引入螢火蟲成蟲,因?yàn)橹挥袕母旧媳Wo(hù)好僅有的螢火蟲棲息地,才能有助于整個(gè)螢火蟲種群的發(fā)育和生態(tài)旅游的發(fā)展。
“最怕的,就是那種一邊打著環(huán)保的旗號(hào)一邊又在破壞環(huán)境的事。”裴鵬對(duì)《瞭望東方周刊》說。
生態(tài)旅游往何處去
“螢火蟲主題公園”被叫停之后,一些網(wǎng)站和微信公眾號(hào)趁機(jī)推出針對(duì)各個(gè)地區(qū)的各式“賞螢攻略”,均列出了各個(gè)城市觀螢的“勝地”,其中有專門的動(dòng)植物園,也有尚未開發(fā)的野外之地。
從2009年開始,上海植物園推出一項(xiàng)名為“暗訪夜精靈”的夜間自然觀察活動(dòng),每年的七八月開放一定的名額,供6~12歲的小朋友在家長(zhǎng)的陪同下參加。
本刊記者也親身體驗(yàn)了一次暗訪夜精靈的旅程。一個(gè)半小時(shí)的活動(dòng)中,幾十個(gè)孩子和他們的家長(zhǎng)打著手電穿梭于夜幕籠罩下的上海植物園。在生態(tài)講解員的引導(dǎo)下,孩子們很快就找到了夜空中飛翔的夜鷺和蝙蝠,結(jié)網(wǎng)的蜘蛛,草葉上的螳螂、螽斯,草叢里的小刺猬,聚居在石頭下的西瓜蟲,爬在樹干上的鼻涕蟲、天牛、獨(dú)角仙、巨鋸鍬甲以及傳說中的金蟬脫殼,池塘里的金線蛙、小龍蝦、田螺,當(dāng)然也少不了林間草地一明一滅忽隱忽現(xiàn)的螢火蟲。
據(jù)上海植物園經(jīng)營(yíng)策劃科副科長(zhǎng)趙鶯鶯介紹,“暗訪夜精靈”活動(dòng)的導(dǎo)賞員都經(jīng)過培訓(xùn),考核合格后才能上崗,均具備相當(dāng)?shù)膶I(yè)知識(shí)。在活動(dòng)中,他們特別強(qiáng)調(diào)“無痕”的生態(tài)旅游觀念,即尊重自然,做不打擾捕捉的旁觀者,進(jìn)而保護(hù)自然。
通過幾年的發(fā)展,“暗訪夜精靈”成為上海植物園最受歡迎的科普活動(dòng)之一。4歲的Amy是由媽媽陪同來參加活動(dòng)的,Amy的媽媽告訴《瞭望東方周刊》,她曾帶女兒幾乎逛遍了上海的博物館,但大都沒有導(dǎo)賞員進(jìn)行講解,全靠自己上網(wǎng)查一些資料再給女兒講解,很難做到準(zhǔn)確。她認(rèn)為,像“暗訪夜精靈”這樣的生態(tài)游、科普游項(xiàng)目非常好,可就是機(jī)會(huì)太少。
另一位帶孩子來參加活動(dòng)的家長(zhǎng)則告訴本刊記者,對(duì)于二三百元的套票價(jià)格來說,普通家庭要經(jīng)常參加還是很有負(fù)擔(dān),希望這樣高質(zhì)量的生態(tài)游能夠多開發(fā)一些,價(jià)格更大眾化一些。
中國(guó)科學(xué)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王獻(xiàn)溥對(duì)中國(guó)的生態(tài)旅游現(xiàn)狀進(jìn)行過深入、翔實(shí)的調(diào)查,他在一份報(bào)告中展示了一個(gè)實(shí)堪憂慮的現(xiàn)實(shí):生態(tài)旅游的核心內(nèi)容——環(huán)境教育和知識(shí)普及明顯缺失。
上海知名環(huán)保人士姜龍告訴《瞭望東方周刊》,“當(dāng)前生態(tài)旅游發(fā)展的痼疾在于‘重硬件輕軟件’,即對(duì)景區(qū)的硬件建設(shè)投資很容易、政府也很支持,而環(huán)保理念的推廣、專業(yè)人員的培養(yǎng)等軟件方面則十分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