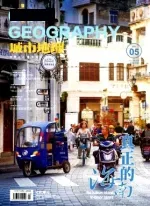從世界城市發展看我國大都市發展及人口控制
許 璐
(長安大學建筑學院,陜西 西安 710018)
1.緒論
隨著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我國在全球經濟份額與日俱增,經濟社會發展日益融入全球化進程,為以北京為核心的首都經濟圈提供了發展機遇及發展要求。但是,由于周邊要素極化吸附效應強烈,城市規模的加速擴張,使得城市問題突出,區域協同發展的平衡性、協調性、聯動性不足。
2.世界城市人口分析
2.1 世界城市人口吸納力分析。在人口吸納能力方面,近二十年來,倫敦、紐約等世界中心城區的全球化移民增加,人口恢復增長,吸引年輕高素質的國際移民成為這些城市保持全球競爭力的重要戰略。但是我國在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李克強總理提到“控制超大城市人口規模”,以上海為代表,雖然人口控制并未被寫入上海市政府工作報告,但在今年的上海市兩會上,卻成為了最多關注的議題之一。
2.2 我國大都市人口問題分析。以上海市為例,一個城市的人口變化由三個指標構成:出生人口,死亡人口,和遷移人口。依照我國上海市的人口普查中穩定的生育率及死亡率來計算,如果人口控制持續產生作用,那么上海市百歲圖的結構將從2010年的楓葉型逐漸變成蘑菇型。從一個擁有巨大勞動年齡群的健康結構逐漸變成了一個超不穩定結構:巨大的老年人群體盤踞在百歲圖的上方,而下面則是孱弱像一條線一樣的勞動年齡人群和學齡人群來勉力支撐,這樣的城市必然是沒有競爭力和未來的。
分析世界城市,以日本為例,雖然其全國的老齡化已經非常嚴重,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已經完全失調,但對于東京都這樣的全球城市,卻依然保持著高度的年齡結構競爭力,其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在70%上下浮動。而以倫敦、紐約等城市為例,其城市人口隨著年齡增長,會逐漸搬離城區,尋找更好的學區和更寬敞的居住環境,從而使城市在中老齡人口上會呈現凈遷出態勢,即使勞動年齡人口總量不大幅度增大,也能保持健康的比例。但是對于上海而言,上海人隨著年齡增長,開始置業買房,養育后代,守著全國數一數二的醫療和福利設施所在地,他們不會選擇搬離上海,所以在現今極低的死亡率情況下,又缺乏有效機制鼓勵老齡人口遷出上海,那么上海的老齡化現象越演越烈。即使現在上海具有人口紅利,但是建立在一種極不穩定的年齡結構上,對外來人口具有極高的依賴性。那么,想要沖淡上海市指數型增長的老齡化率,就只有適當放開戶籍控制,按比例引入年輕人口。那么對于人口總量的控制,要通過其他模式解決而非簡單粗暴的控制外來人口進入。
從用地視角分析,對于我國現在占比例過高的工業用地,未來勢必有所縮減。按照工業用地正常的15%-30%的比例,無論是北京還是上海都將有大量的工業用地發生置換,其主要方向有兩個:工業用地轉換為第三產業用地,即“退二進三”,那么將大量提高就業崗位總量;工業用地轉換為居住用地,提高居住用地將增加住宅的供給和居住容量,進而提高人口規模。由此可以看到,在總用地不減少的情況下,無論是哪一種用地調整方向,其結果都指向了人口規模增加。而結合我國現在提高土地集約利用水平及建設用地“零增長”的政策導向,占比例過高的工業用地調整勢在必行,這又會與控制人口規模的目標發生沖突,給人口調控帶來困難。
所以,我國人口調控的關鍵就在于城市職能的疏散,采用“圈層分異,廊道拓展”的空間組織模式,疏散具體包括居住與就業職能,避免產生區域性的“職住分離”。以此形成不同難度等級的疏散產業。引導城市向多中心體系發展。
3.世界城市職能發展分析
在城市職能發展方面,各國首都經濟圈得出,首都地區世界職能的國際化、區域性職能拓展是其保持全球競爭力的重要途徑,這就要求區域走多元化產業升級路徑,保持高端服務功能向中心城區集聚,各類專業化服務、生產功能加速向區域轉移。
4.世界城市空間組織模式分析
在空間組織模式,空間政策體系,綜合交通體系,生態網絡空間四方面看,四大世界城市的空間布局大部分采用“圈層分異,廊道拓展”的組織模式。15 公里范圍內的中心城區各高端服務功能高度混合;15-30 公里范圍是中心城區的配套協作區,是新興職能拓展的主要區域;30-60 公里主要沿交通走廊布置專業化的產業新城,是疏解首都職能的重點區域。為保障不同圈層的有序發展,各大城市制定“分類分區,差異管制”的空間政策體系,如首爾劃分擁塞抑制區,增長管理區及自然保護區。對于交通系統,世界城市均采用公交優先和交通需求導向的策略來適應人口和功能擴張,在空間組織上采用多層次多方式集合的模式,中心城區15 公里以內是綜合樞紐集中分布的區域;15-30 公里范圍是國家級區域性交通網絡廊道集中分布區域;30-60 公里圈層范圍主要以城際軌道和市郊鐵路來承擔客運交通。各國對于生態網絡空間總的來看是在“環形+斑塊+網絡”的生態安全格局基礎上,建設區域綠道、國家公園等,30 公里以內采用“楔形綠地+環形綠隔”來組織綠化隔離帶;30 公里以外分布生態保護區等。
5.總結
通過研究世界城市發展規律,可以相對應的認識到我國上海北京等大都市未來的職能調整方向及空間拓展模式。在職能方面,推進首都職能的區域化發展,按照“首都核心區-首都功能區-協調發展區”等層次考慮;在交通方面,北京應加快中心城區軌道網向郊區延伸,并形成主要通勤量大的走廊地帶多條軌道網格局;在空間體系方面,應進一步優化中心城區的多中心體系,依托軌道網絡加強中心城區與新城之間的便捷聯系并沿軌道交通站點形成多個綜合功能生活圈,在中心城區外圍培育職住平衡的綜合性城市和專業化城市;在區域管控方面,應建立起跨區域的剛性管控和彈性協調規劃體系。
[1]絲奇雅·沙森著,周振華等譯,全球城市(M),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5年7月
[2]劉龍勝、杜建華、張道海,軌道上的世界——東京都市圈城市和交通研究(M),人民交通出版社,2013年8月
[3]左學金,世界城市空間轉型與產業轉型比較研究(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12月
[4]盧明華、李國平、孫鐵山,東京大都市圈內各核心城市的職能分工及啟示研究(J),地理科學,2003年第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