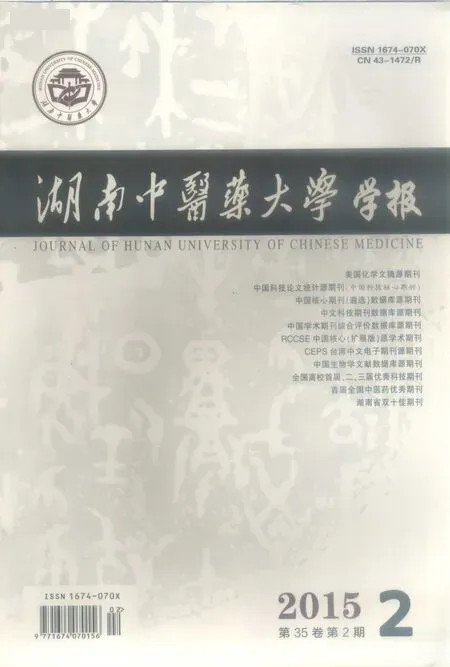天地觀對《黃帝內(nèi)經(jīng)》理論建構(gòu)的影響初探
許盈,黃政德(湖南中醫(yī)藥大學(xué),湖南長沙410208)
·中藥藥理·
天地觀對《黃帝內(nèi)經(jīng)》理論建構(gòu)的影響初探
許盈,黃政德*
(湖南中醫(yī)藥大學(xué),湖南長沙410208)
天地觀;《黃帝內(nèi)經(jīng)》;陰陽;五行
〔Keywords〕concept of heaven-and-earth;Huangdi Neijing;Yinyang;Wuxing
關(guān)于天地觀的內(nèi)容及意義,學(xué)術(shù)界多有論述,且開始結(jié)合哲學(xué)、宗教、建筑等多領(lǐng)域進(jìn)行研究[1]。中國醫(yī)學(xué)文化史著名學(xué)者馬伯英曾于2014年就中醫(yī)文化的深層次結(jié)構(gòu)在《科學(xué)》雜志撰文,認(rèn)為中醫(yī)整體論“由三大支柱支撐:一是天地人大小宇宙觀,二是活體生命觀,三是生命關(guān)系網(wǎng)”[2]。本文試圖梳理《黃帝內(nèi)經(jīng)》(以下簡稱《內(nèi)經(jīng)》)如何從中國傳統(tǒng)文化深處的天地觀尋找支持,以天地觀作為理論建構(gòu)的基本要素之一,從而成為經(jīng)典文本的歷史過程。

圖1 中國上古人的宇宙天地觀念示意圖
1 傳統(tǒng)文化的源頭:天地觀念的形成
溯源古代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上古傳說是解讀傳統(tǒng)文化天地觀的密碼。《山海經(jīng)》一書可視為描述上古時代中國人對天地起源認(rèn)知的代表。《山海經(jīng)·海外東經(jīng)》關(guān)于神樹扶桑的故事記敘:“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齒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具有濃厚神話色彩的扶桑天地觀,是殷商之前的中國人對天地空間和時間的認(rèn)識。何新《諸神的起源》中第六章《神樹扶桑與宇宙觀念》結(jié)合先秦及傳世文獻(xiàn),對這種天地圖式復(fù)原如圖1所示[3]。
由圖1可知,扶桑故事寓意的上古中國人的天地觀主要有三方面內(nèi)容:其一,先民的思想世界一開始就與“天”有關(guān),天門有九層,九個太陽象征著日月星辰等九天;其二,與“天”相對的“地”中心在昆侖山上,山高一萬一千里,地下深三千六百里,大地的四角各有一根地柱支撐;其三,天地不僅有邊界,還有中心,人居其中,以建木為正中線。上古傳說所折射的古人對天地的感覺與想象,暗含一系列的隱喻,天與地相對,天地有中心和邊緣,由中央與四方構(gòu)成,在空間關(guān)系上中央統(tǒng)轄四方,在時間順序上中央早于四方。
周人延續(xù)了上古以來的天地秩序化認(rèn)識,且對天象地理的觀察和體會有了進(jìn)一步發(fā)展。且周人重禮樂,借助儀式推崇禮制的觀念與行為,背后暗含著禮儀實際也是天地秩序的象征。天地如此整齊有序,秩序化的格局為人們處理現(xiàn)實世界的關(guān)系提供了指導(dǎo)和行為依據(jù)。以“國之大事”的祭祀為例,祭天地的圜丘、方丘、明堂等場所都以形制象征天地四方,仿效天象置于一個有序的空間格局中。天子祭祀時,進(jìn)出的儀仗要仿效天象,就像天象一樣“進(jìn)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這樣,在當(dāng)時人們的觀念中,來自天地整齊不亂的“天地格局”提供了一種價值的本原,在人們心中投射了一種觀念:天地格局支持著人們對自然現(xiàn)象的理解,支持著建筑的基本格局,支持著祭祀儀式的規(guī)范,支持著人類社會的各種行為等,最終發(fā)展成為中國古代思想的一個起點和支持背景。
2 傳統(tǒng)文化的依據(jù):系統(tǒng)化哲理化天地觀的建構(gòu)
“在軸心時代得到發(fā)展的各種思想傳統(tǒng)延展了人類意識的邊界”[4],中國的軸心時代處于春秋戰(zhàn)國時期,百家爭鳴,古代中國人關(guān)于天、地的各種認(rèn)識逐漸從零散走向系統(tǒng),從經(jīng)驗走向抽象,成為傳統(tǒng)文化的基點和依據(jù)。
2.1天地的結(jié)構(gòu):從中心向四方延伸,次序滋生的整體
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人們普遍認(rèn)為,宇宙有一個中心,稱為“道”、“一”、“太一”等。《老子》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強(qiáng)字之曰道。強(qiáng)為之名曰大。”老子認(rèn)為“道”是比天地更早的存在,“道”廣闊無邊,周流不息,是產(chǎn)生天地萬物的前提,一切事物變化無窮的終極依據(jù)。及至后來,儒家四大經(jīng)典之一的《中庸》雖未給天地的中心命名,但也同意并確認(rèn)了天地中心是一切存在的依據(jù):“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致中和,天地位矣,萬物育矣”。天地的中心,本來是天文地理實測和經(jīng)驗的知識,經(jīng)過思想家的感悟和推測,提升為哲學(xué)高度的抽象術(shù)語。
一旦“道”的概念被確立,廣泛地延伸到對天、地、人的結(jié)構(gòu)解析中。因而在時間次序上,宇宙從一到多,從簡到繁漸次滋生。《老子》所謂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簡單描述了生長的階段性;在天地間體驗到了天地演化是“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過程。自然,日月的升起降落,星辰的運轉(zhuǎn),四季的交替更迭等都是按時而至,是天經(jīng)地義的“道”的顯現(xiàn)。
2.2建構(gòu)的思路:運用數(shù)類元素進(jìn)行拆分歸納的推導(dǎo)
祖先為單個具體的事物創(chuàng)制漢字之后,逐漸開始將同類的事物放在一起,產(chǎn)生抽象的“類”的概念。《說文解字》序中有這樣一段精彩的論述:“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后形聲相宜,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馮契認(rèn)為,類是中國傳統(tǒng)邏輯學(xué)的起點[5],這種從具體可感的事物出發(fā),逐漸將各種事物歸置為抽象“類”的思維方式,符合人類認(rèn)知的規(guī)律,擴(kuò)大了古人對外部世界的把握。四時、五行、八方、九州、十二時、二十八星宿……盡管不知道中國古人對數(shù)字的崇奉從何時開始,但可以明確的一點是,中國古人偏好使用某些數(shù)字。定數(shù)與事類相互搭配起來,成為指稱宇宙事物的基本方式。
典型的代表數(shù)字就是“五”。區(qū)分天文星象為歲、月、日、星、辰,歸納為“五位”;區(qū)分祭祀儀式為禘、郊、宗、祖、報,歸納為“五祀”;區(qū)分五行之神為木正句芒、火正祝融、水正玄冥、土正后土、金正蓐收,概括為“五正”;區(qū)分兵器為戈、殳、戟、酋矛、夷矛,總括為“五兵”;區(qū)分調(diào)料為醯、酒、蜜、姜、鹽,歸納為“五味”。“五”成為一個定數(shù),歸納系列事物的基本單位,被春秋戰(zhàn)國時代的人們普遍接受。
2.3關(guān)聯(lián)的世界:天地人之間對稱和對應(yīng)的聯(lián)系
在古代中國人的心目中,外在天地與人自身之間廣泛地聯(lián)系著,構(gòu)成了一個充滿聯(lián)系的整體。主要有陰陽對立和五行對應(yīng)兩種聯(lián)系。
陰、陽最初是表示山南水北的地理方位詞,逐漸衍生為相反概念的類名,如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cè)帷⑦t速、高下、出入等。《周易》謂:“一陰一陽謂之道”表明陰、陽已經(jīng)抽象為對立的概念,成為天地間的兩大基本因子。
五行最初與地理有關(guān),后來在很多領(lǐng)域通用,在春秋時期就已經(jīng)成為了很系統(tǒng),表示對應(yīng)概念的類名。《左傳》記載昭公二十九年,蔡墨論五行之官為木正、火正、金正、水正、土正,又可見人們已經(jīng)有了五行與五神相配的傳說。在古人將事物以“五”和“類”搭配的過程,關(guān)鍵的環(huán)節(jié)是古人想象它們存在著對應(yīng)的相似性。比如五行中的木,萬物在春天欣欣向榮,于是四季中的“春”就和五行中的“木”屬一類,草木在春天色澤青翠,于是“青”又與“木”、“春”相配。“五”這個數(shù)字就有了極為豐富的內(nèi)涵。
3 天人相應(yīng):《黃帝內(nèi)經(jīng)》醫(yī)學(xué)思想體系的預(yù)設(shè)
先秦時期的思想家多有論述人與天地之間存在相應(yīng)關(guān)系,馬伯英認(rèn)為“‘天人相應(yīng)’是在《黃帝內(nèi)經(jīng)》中才得以反復(fù)強(qiáng)調(diào)的”[2]。當(dāng)《內(nèi)經(jīng)》的醫(yī)家意識到中國古人獨特天地觀作為傳統(tǒng)文化理論依據(jù)的重要意義時,他們亦開始有意識地從中尋找依據(jù)和邏輯力量,同時借助天人相應(yīng)的理論預(yù)設(shè),以進(jìn)入社會思想主流中。
3.1人的身體仿照天地次序格局
天地的架構(gòu)是依據(jù)、尺度,引著醫(yī)家根據(jù)預(yù)設(shè)的天地時間和空間框架,洞察人的身體結(jié)構(gòu)。《內(nèi)經(jīng)》卷一記:“賢人法則天地,象似日月,辨列星辰。逆從陰陽,分別四時”,總括了醫(yī)家自覺地以天地四時象征的次序格局為綱領(lǐng),系統(tǒng)地闡述人體結(jié)構(gòu)及生命活動規(guī)律。這表明,天地觀是形而上層面建構(gòu)醫(yī)學(xué)理論合理性的思維定勢,也是《內(nèi)經(jīng)》確立權(quán)威性的必然選擇。葛兆光注意到,春秋戰(zhàn)國時期思想集大成之作《呂氏春秋·序意》中引用黃帝教誨顓頊的話作為論據(jù):“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為民父母”,葛氏認(rèn)為:“這幾句話很可能就是黃帝之學(xué)的要緊處,也就是說,黃帝之學(xué)是以大圜和大矩即天地為不言而喻的依據(jù),引申和推衍出來的一套實用技術(shù)和思想理論。”[6]
生理學(xué)意義上的“人”效法天地結(jié)構(gòu),有一個中心,次序衍生。心為主宰的五臟系統(tǒng)是人體結(jié)構(gòu)的中心,“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肝脾肺腎輔佐心。由中心向外延伸,六腑、五官、五體、四肢百骸等人的組織器官都納入人體結(jié)構(gòu)中。如《靈樞·邪客》說:“天圓地方,人頭圓足方以應(yīng)之。天有日月,人有兩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竅。天有風(fēng)雨,人有喜怒。天有雷電,人有音聲。天有四時,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藏。”
3.2人的生命節(jié)律與宇宙以“氣”為中介相通相應(yīng)
《內(nèi)經(jīng)》有“生氣通天”的提法:“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陰陽,天地之間,六合之內(nèi),其氣九州九竅五藏十二節(jié),皆通乎天氣。”同出于“氣”的本源,同又具備整齊有序的相同結(jié)構(gòu),人和天地一體同構(gòu),以“氣”為溝通宇宙與人體的介質(zhì),人的生命節(jié)律和宇宙就有了相通相應(yīng)的關(guān)系。天地之氣流轉(zhuǎn)不息,古代醫(yī)家相信人的生命亦是由“氣”維持的,可以從氣在人體內(nèi)運行的時間和運行的路線這兩點得到確證。一方面,氣在人體內(nèi)運行有一定的時間規(guī)律,它與天時相對應(yīng)。人體的變化即與天地四時之氣次序遞變產(chǎn)生春夏秋冬的季節(jié)變化。《素問·診要經(jīng)終論》云:“正月二月,天氣始方,地氣始發(fā),人氣在肝……十一月十二月,冰復(fù),地氣合,人氣在腎。”一年四時十二個月,由氣主導(dǎo)的天氣、地氣及人體的變化一一配屬。另一方面,氣在人體內(nèi)的運行有一定的路線。李建民先生認(rèn)為《素問·五運行大論》所云:“黃帝坐明堂,始正天綱,臨觀八極,考建五官,請?zhí)鞄煻鴨栔保馕吨包S帝所處的是一個具有神圣宇宙圖式的空間”[7]。從二繩四維切割而形成的天體的八個方位來說,人體內(nèi)十二經(jīng)脈在手足四肢分布的位置正與之一致。
中醫(yī)治療和養(yǎng)生將“導(dǎo)氣以令其通”作為一條基本的原則。這要求人將自己的身體與天地聯(lián)系起來,與天地之氣的變化規(guī)律相適應(yīng)。尤其是導(dǎo)引行氣的過程,更注重人體之氣與天地相通應(yīng)的體驗。氣在體內(nèi)暢通有序,與天地運行“通則久”,“周行而不殆”的主題一致。
3.3人體內(nèi)的氣血變化可用數(shù)類概念表述
與西方醫(yī)學(xué)相比較,氣血概念為中國傳統(tǒng)醫(yī)學(xué)特有,血氣在春秋時代已被視為人身的重要物質(zhì)要素,《內(nèi)經(jīng)》從結(jié)構(gòu)和功能的角度,運用陰陽、五行等數(shù)類概念表述人體內(nèi)的氣血變化,有天然的合理性和說服力。
《素問·金匱真言論》云:“夫言人之為陰陽,則外為陽,內(nèi)為陰;言人身之陰陽,則背為陽,腹為陰;言人身之藏府中陰陽,則藏者為陰,府者為陽。”從人內(nèi)外的一陰一陽為邏輯起點,步步解構(gòu),以陰陽觀說明人自身的對立屬性。“東方青色,入通于肝,開竅于目”,肝的特性與東方、青、目等之間有相似性,以五行觀說明人體五臟與五行之間的對應(yīng)關(guān)系。以此運用于針刺治療中,沿著分天地為四方、一年為四季、一日為四時的思路,醫(yī)家也需將春夏秋冬四季及平旦日中黃昏雞鳴四時與人體五臟絡(luò)屬的十二經(jīng)脈對應(yīng)施針,以達(dá)到人體的氣血平衡。
[1]孫熙國.《易經(jīng)》的宇宙觀與陰陽五行家思想之淵源[J].周易研究,2006,75(1):56-62.
[2]馬伯英.人類學(xué)方法:探索中醫(yī)文化的深層次結(jié)構(gòu)[J].科學(xué),2014,66 (2):28-31.
[3]何新.諸神的起源[M].北京:時事出版社,2007:93-104.
[4](英)凱倫·阿姆斯特朗.軸心時代[M].孫艷燕,白彥兵.譯.海口:海南出版社,2010:3.
[5]馮契.中國古代哲學(xué)的邏輯發(fā)展[M].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9:1 094-1 096.
[6]葛兆光.中國思想史[M].上海: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2013:105.
[7]李建民.生命史學(xué)——從醫(yī)療看中國歷史[M].上海: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2008:305.
(本文編輯賀慧娥)
Primary Study of the Effect of Concept of Heaven-and-Earth on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Huangdi Neijing
XU Ying,HUANG Zhengde*
(Hu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ne,Changsha,Hunan 410208,China)
R221
A
10.3969/j.issn.1674-070X.2015.02.002.003.03
2014-11-12
許盈,女,在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醫(yī)醫(yī)史文獻(xiàn)。
*黃政德,男,教授,博士研究生導(dǎo)師,E-mail:Hzd112@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