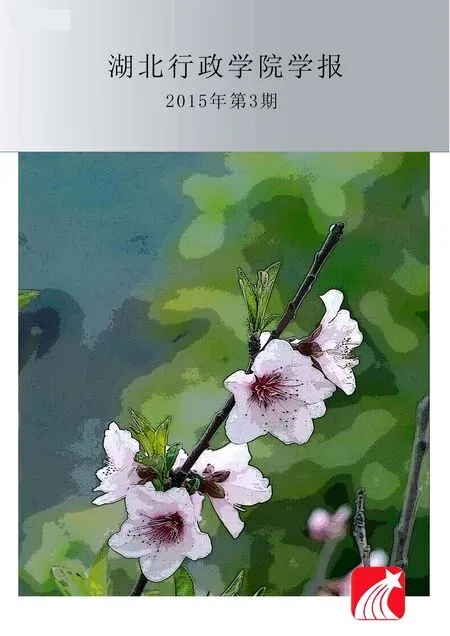農村村民環境態度與環保行為研究
——基于湖北部分農村居民的問卷調查
蔡科云,孟燦
(湖北大學,湖北武漢430062)
·社會學研究·
農村村民環境態度與環保行為研究
——基于湖北部分農村居民的問卷調查
蔡科云,孟燦
(湖北大學,湖北武漢430062)
以湖北農村部分村民為樣本,通過比例分層隨機抽樣的實地訪談與問卷調查,以定性、定量分析村民的環境態度和環保行為。結果表明:環境態度對環保行為存在正向預測作用,同時也受到情境因素相當的限制。一方面,生態教育塑造著著村民的環境價值觀;但另一方面,人文環境與硬件設施的雙重困境讓友好的環境行為始終是紙上談兵。村民喜聞樂見的環境宣傳以及環境友好的外部設施能夠為農村生態公民的培育、以“農民為主體”的農村環境治理破冰。
環境態度;環保行為;情境因素;雙向宣傳;硬件塑造
DOl:10.3969/j.issn.1671-7155.2015.03.013
一、引言
傳統粗放的耕作模式下,我國農村經濟相較于計劃經濟時代取得了長足發展。但是,改革紅利初期顯現后,隨之而來的土地荒漠化、水污染、垃圾污染、植被破壞、野生動物銳減等生態問題愈演愈烈,嚴重制約了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村民普遍對農村的生態環境表示憂慮,然而,這種憂慮卻并沒有帶來農村生產生活模式的根本變革。村民的環境意識在相當程度上還是一種傳統中國人的模糊文化,人們淺層的初級的環境態度深受環境現狀所左右,與環境行為之間普遍沒有亦步亦趨;而在生態文明建設的時代主題之下,農村生態公民作為其主體基礎,改變傳統陋習,倡導綠色生活,走低碳農業之路,是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關鍵。筆者認為,環境研究雖然在國內已有20余年的歷史,但是關于農村村民環境行為的構成因子、環境態度與環境行為的關系并沒有得到充分的揭示和驗證。那么,在中國的農村,哪些因素影響著人們對環境的態度,環境態度又是如何對環保行為發生作用,對環境態度、意識和環保行為之間的不一致現象如何解釋,這是本次研究所關注的重點。
在環境態度與環保行為的關系研究中,我們首先得厘清在環境研究中涉及的相關概念。一般而言,環境態度包括兩類:對環境的態度(一般環境態度)和對某種環境行為的態度(特定環境態度)。大部分學者認為一般環境態度預測一般環境行為,特定的環境態度是指對某種環境行為的態度;在相關文獻中,還將環境態度引入生態公民的概念和理論框架,賦予其時代內涵,將生態科學知識和正確的生態價值觀相統一,包括生態價值觀、生態倫理觀、生態審美觀等,強調每個公民以謙卑、和睦與節制之德行,對有益生態的行動有著發自內心的擁護與贊成并逐步形成穩定的有利于生態環境的情感。而對于環保行為的稱謂和定義,有積極的環境行為、具有環境意義的行為、負責任的環境行為、生態行為之說,國內外學者雖研究視角有所差別,但涵蓋的范圍基本一致,大都強調個人基于其環境態度,為了環境保護和影響生態環境問題的意向行為。而本文在前人研究結果之上,保留其核心內容,將其簡化為環保行為,以期有化繁為簡、深入淺出之效。
在現有研究中,國外Hines和Stern等學者的研究較有指導意義,經典的計劃行為論①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a認為,人的行為是經過深思熟慮的計劃的結果。以及負責任環境行為模式論①負責任環境行為模式人們對一般環境的態度,是廣義上的環境態度;特指對某種環境行為的態度,可稱之為狹義的環境態度。研究成果表明,環境態度是預測環境行為的重要因子,與情境因素共同作用,形成個人的環境行為。環境態度作為影響人們環境行為的重要因素,在知識分子當中形成了不小的語境,但是還沒有進入整個社會的主流。然而,總體而言,國內針對環境態度與環境行為的研究相對較少,并且大多旨在研究城市居民、高校學生、游客等群體,對于生態公民建設的重要成員——農村村民的實證研究卻鮮有涉及。而當前塑造生態公民、建設美麗鄉村、改善村民生態意識單薄的現狀,樹立起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協調發展的觀念,迫在眉睫。
綜上,本次調研將嘗試驗證上述研究成果,并深層次地探討村民環境態度與負責任的環境行為之間的關聯,嘗試對村民環境態度、意識和環保行為之間的不一致現象做出解釋。
二、村民環境態度與環保行為的測量與問卷調查
此次調研以湖北省農村地區為調查區域,以該區域內部分村民為調查對象,力圖對我國農村村民的環境態度與環保行為的關系進行一次實證研究。湖北是我國的農業大省,以不足全國2%的國土面積生產了占全國相當比重的稻谷、棉花、油料、豬肉和淡水水產品,并為全國5.2%的鄉村人口提供了生存空間。但是從傳統農業向機械化學農業轉型之日起,巨大的環境危機就蟄伏于這一片花紅柳綠的土地之上:掠奪式開發,土壤地力等自然資源過度消耗,水、大氣、廢物的嚴重污染所帶來的次生危害,生態系統脆弱所引發的惡性循環,農業生產效力走低等一系列問題接踵而來。湖北作為千湖之省,水體污染問題尤為突出,農藥、化肥的濫用,重金屬等廢棄物的不當處置以及生活中的“白色污染”和面源污染,使得農村地下水大量污染……從單一的村民這一環境主體的視角而言,加強公民生態意識的培育刻不容緩。此次研究,根據農村地區的具體實際,設計體現環境態度與環保行為的觀察量,探究個體差異對環境態度的影響,以及環境態度對環保行為的影響。
(一)研究工具
本次調查在成熟量表之基礎上,結合農村村民的生活實際與村民環境行為的特征,有針對性地編制了環境態度與環保行為問卷。經過前期對初始問卷征求專家意見以及訪談討論,甄選了一些生動、具體、貼近農村生活實際的研究變量,經過反復修正并最終形成此次調查問卷。
1.環境態度與環保行為研究項的構成
正式問卷包括4個分量表,細言之,包含村民的基本信息、環境態度、環境行為與環境問題的解決4個維度,共設置了26個題項。就問卷的內部結構而言,首先設置“村民基本信息”量表以增強被試者代入感與主體意識,量表具體包括性別、年齡、文化程度、收入來源共4個小項;其次,考慮本研究的目標、背景和群體的特殊性,本“環保行為”分量表主要針對具體環境行為,以適用于農村地區的生產生活實際。量表由8個題項(C1-C8)組成,涉及對治理環境投工投勞的程度、農藥化肥的使用情況、種植林木的狀況、生產生活用水的循環利用、垃圾分類的情況、“三下鄉”中節能家電的選擇等6個方面。對于問卷的設計也借鑒采用了李克特五點計分方法②由美國心理學家李克特與1932年改進而成,該量表屬評分加總式量表最常用的一種,屬同一構念的項目用加總來計分,單獨或個別項目是毫無意義的。該量表由“非常同意”、“同意”、“不一定”、“不同意”和“非常不同意”五種回答,分別記為1,2,3,4,5,每個被調查者的態度總分就是他對各道題的回答所對應分數的加總,這一總分可說明他在某一問題上態度的強弱以及不同狀態。,參照Smith-Sebasto等(1995)及Halpenny(2006)為測量環境行為的量表而制成;隨后,問卷設置也遵循由具體到抽象的認知規律,由淺層次的外在行為深入到內在的環境態度,環境態度分量表具體分為對“綠色農業、生態公民、節能低碳”這些詞的認識來源以及認識程度,對環境污染的關注程度、對破壞環境行為的態度、對農村環境的處理建議,共12個題項(Dl-D12)構成;最后,以“環境問題如何解決”來引導村民對整個農村環境問題解決的思考。
2.村民環境態度與環保行為研究項的信度
測驗結果的內外部一致性、穩定性及可靠性,被統計學界稱為量表的信度,而一般多選取內部一致性來檢測研究結果信度的高低。在村民環境態度的信度檢驗結果方面,相關系數值高達0.761,由此可見該問卷的信度較高,問卷可靠性強。檢驗結果也表明,環保行為分項中,具體環境行為可信度為0.795,同樣地表明環保行為項的信度以及可靠性均較高。“村民的基本信息”、“環境態度”、“環保行為”與“環境問題的解決”這4個分量表以及各個研究項之間具有內部一致性。
(二)方法與程序
調查以問卷為主,輔之以個人訪談、現場實地考察。此外,我們對環境問題的解決機制,也做出了探討。2014年7月至8月,我們對湖北農村部分居民進行訪談和問卷調查,本次調查共完成了402份問卷,經遴選有效問卷為363份,有效回收率為90.29%,調查對象的男女比例接近1:3。問卷數據收集后利用統計學相關原理對原始數據進行頻數分析、相關系數分析、交叉表分析等。
研究使用SPSS統計軟件等多種統計方法對數據進行分析。首先通過信度分析檢驗了問卷設計的可靠性,分析了被調查者個體的基本特征,考察了基于人口變量與地方因素的環境態度與環保行為差異;具體操作關于“環境態度與環保行為”變量分析統計工具,使用線性回歸分析方法考察環境態度與環保行為之間的關系。
三、環境態度與環保行為的結構分析及影響因素調查
(一)環境態度的結構
研究采用最大方差法對環境態度因子分析的結果進行旋轉,并進行大小排序。問卷中的性別、年齡、文化程度與環境態度中的各個小項用SPSS軟件相關系數1作檢驗。檢驗發現,村民的文化程度和環境態度中對“環境知識的來源”、“環境知識的熟悉程度”、“環境污染的關注度”、“破壞環境行為的態度”、對“農村環境的處理建議”的P值相較于性別、年齡這兩個維度而言,其相關性最為顯著,P值均大于0.8。具體而言,將被調查者的文化程度與“對環境污染的關注程度”做交叉分析,數據顯示,二者呈正相關,隨著文化程度的提高,對環境污染問題更加關注。但由于農村地區教育水平有限、農民的知識結構單一,導致在“很關注”這一選項上百分比最小。此外,調查結果顯示,年齡、性別與環境態度也存在一定的相關性,這驗證了“年齡、性別、文化程度”環境態度的三因子結構假設。
檢驗顯示,在體現村民環境態度的4個維度中,內含D2、D3、D4、D5、D6共5個題項的環境知識的熟悉程度,與下文的環境行為有顯著的相關性,相關系數高于其他環境態度變量,對破壞環境的態度、環境知識的來源以及對環境污染的關注度這三項的相關性則依次遞減。因此我們選擇它來與村民的環保行為作交叉分析,其系數均達到0.201。綜合以上分析結果,我們選擇環境態度最顯著相關性的因子——“村民的文化程度”與對村民環保行為貢獻率最大的“對環保事業投工投勞”這一小項作交叉檢驗,關于環境態度與環保行為之間的具體關聯見下表:

文化程度與對環境污染的關注度以及投工投勞行為交叉制表
(二)環保行為的基本結構
對環境態度因子分析的結果表明,本研究的測量量表具有良好的結構效度。我們將體現農村村民環保行為的參數具體化為:主動實施綠色生產的程度,農藥化肥的使用情況,種植林木的狀況,生產生活用水的循環利用,垃圾分類的情況,節能家電的選擇。如前所述,環境態度中的“村民環境知識的熟悉程度”之相關系數高于其他環境態度變量,故以此再與問卷中環保行為小項(C1-C8)作一一對應的檢驗,得出環境態度與環保行為之間的相關性。
(三)結果與分析
村民環境態度的總體特征結果顯示,環境態度的總體均值為27.38。其中,“環境知識的來源”維度總體均值為17.07,“環境知識的熟悉程度”、“環境污染的關注度”、“破壞環境行為的態度”、對“農村環境的處理建議”,12個測量指標的平均得分為3.637。數據顯示,村民具有粗線條的親環境認知和非自覺的生態情感。例如,調查中我們了解到:宜昌市特別是枝江的老一輩村民,在耕作中還保留著幾千年的勞動傳統——水耕火薅,其中燒火土是農民積肥的一種生產習俗。村民將渣土、塵灰,動物糞便以及秸稈麥草等在秋冬季節燒掉,將其火土灰用作肥料;同時用火土灰覆蓋農作物種子及幼苗以發揮其保暖、持水、透氣的功能,起到保護和促進生產的作用。渣土、棄土等建筑垃圾,牲畜糞便等養殖垃圾以及植物秸稈等在小幅度范圍內得以處理消耗,一方面表達了村民自發的“物盡其用、保護地力、人地和諧”的生態情感;但另一方面,隨著農村耕作模式的轉變,水耕火薅這一傳統逐漸消失。而且單純的原始焚燒,也給農村帶來空氣污染,并對森林防火造成威脅,易造成二次污染。而對這一潛在危害,村民對此大都表示“不了解”,顯示村民在傳統習俗之余對深層次的生態理念知之甚少,其重視程度低下表現為一種當然。總體而言,湖北地區農村村民群體的整體環境態度水平偏低。
對環境行為的整體特征進行分析,結果表明,村民環境負責任行為總體均值為12.039,相較于吳向陽等學者關于城市居民一般環境行為的調查,本次調查結果中湖北農村地區村民這一維度的總體均值偏低,具體環境行為維度總體均值為10.491。調查還發現,村民對自身在環境問題上的主體意識不清,表現最為突出的是對農村環境的處理建議。村民大都以漠視觀望的態度壓抑著內心對美好家園的渴求,他們的共同心聲便是強有力的政府資金以“糧食直補”的方式滴管式的注入,然后再社會主義地大家干,我們不難看出其中的單一性和局限性。具體而言,他們本身受制于現有的外部軟硬件設施,包括低層次抽象性的宣傳、薄弱的環境基礎設施等。據了解,在湖北省“三萬”活動的帶領下,黃糧鎮對垃圾治理問題作出了一些有益探索:村干部到枝江市問安鎮學習取經,并結合實際,制定《黃糧鎮公路沿線垃圾處理辦法》,依托黃糧鎮城鎮建設及環境保護服務中心,成立“黃糧鎮源源勞務公司”,村莊垃圾實行農戶分類—小區集中—源源勞務部清運、填埋,“以錢養事”,推進鄉村環衛管理市場化,鄉村生活垃圾“戶分類、村收集、鎮清運處理”的機制逐步完善;制定《黃糧鎮廢舊工業污染品回收辦法》,每村聘請一名熱愛環保公益事業、責任心強的農戶負責該村的廢舊電池、燈泡、塑料等“不易消化”的有害工業品回收,再交由鎮源源勞務公司收購處理,鎮政府按照交售數量給予經濟補貼,即雙倍于市場價收購。但通過截至撰稿時的回訪,村民表示垃圾治理還是“面子工程”,村干部表示城建站缺乏專項垃圾清運資金,以問安鎮為例,一個村進行垃圾分類年投入至少要5萬元。前年、去年各村垃圾清掃經費有3萬元,今年只有2萬元,投入不夠。問安鎮保潔員年收入為3500元左右,沒有積極性,導致本該一周一次的垃圾清運變成現在的一月一次,很多地方垃圾沒人清掃、分類,村委會也無法對其建立獎懲機制。在資金來源渠道單一、農村經濟還相對比較困難的情況下,垃圾處理經費的投入嚴重不足,環衛設施建設也隨之滯后,更缺乏地域化的環境宣傳培育,這些已成為制約農村生活垃圾有效治理的主要瓶頸。
此外,對于在村莊公共區域“路邊、溝邊、塘邊”垃圾無序堆放的原因,53.85%的受訪者認為主要是村民環保意識淡薄,還有23.08%的人認為是因為沒有專門機構、人員維護,15.38%的人認為沒有完善獎勵懲罰機制,還有極少數受訪者認為把垃圾丟到一個相對固定的地方讓其自生自滅,是從長輩和生活中習得的經驗行事,無所謂;對于本村當前處理農村生活垃圾最大障礙是什么,超過15%的受訪者認為是“村民環境參與途徑少”,村民無所適從也很無奈。有18.18%的認為是“對垃圾無害化處理和回收利用力量薄弱”,政府委托的收運機構或個人拿錢不辦事或不辦足事,有資金使用的腐敗。并且對于生活垃圾的治理,60%以上的村民主張“集中處理”,而不是分散的“單獨處理”、“聯戶處理”。村民對“環境事業人人有責”異化為“人人無責”有一種強烈的信仰——大多“寬于律己,嚴以待人”。譬如,談及生活垃圾的處理,有村民認為只要資金到位,環境問題迎刃而解,提議建立垃圾填埋場、發電廠以實現垃圾的資源化、減量化。針對生活垃圾集中收運及填埋、焚燒的收費問題,60%以上的村民支持對垃圾清理進行收費,但只有其中的31%接受向農戶家庭收費,另外的39%主張向周邊商戶、工廠收費,或者由財政買單,而不是向農戶收費。值得注意的是受訪者中有大約14%堅決反對收垃圾費,還有16%未置可否;60%的贊成收取垃圾費的村民中,對于垃圾收費的計費方式,42%主張“超量才收費”,其次才是“按垃圾排放量”、“按戶”、“按人頭”。我們直接設置一個問題“若進行生活垃圾收費,您能接受的收費標準是多少”,77.22%贊成的收費標準都是每戶每月10元以下,還有25%贊成每戶每月10元到20元。
(四)群體的差異性分析:村民在性別、年齡、文化程度上的差異影響
以相關變量為基礎,使用單因素方差法考察環境態度方面的差異,結果表明村民的環境態度與環境行為在文化程度上差異性較為顯著:調查人群中有77.2%是初中以下(含初中)學歷,他們明確表示在節能家電的選擇上,關鍵要看其價格,環境成本并不納入考量;高中以上學歷受訪者中有80%會從保護環境和美麗鄉村建設考慮環保行為。
在當前生態惡化的背景下,分析婦女與生態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十分必要,婦女群體應當是我們關注的一大重點。女性在環境態度和行為上的自評分顯著地高于男性,這可能與農村傳統文化及社會經濟生活基礎的聯系有關。在傳統的農業社會,女性對家庭的依附關系具有歷史上的合理性,在農村,家庭承包制度仍然保留了一定的傳統家庭分工;農業生產安排、經濟投入分配、家人生活起居都在婦女的肩上,婦女作為一個家庭的主要角色,她的意識、行為會對家庭和孩子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
不同年齡階段的村民對環境的看法差異性明顯,兒童以及青壯年(40歲以下)的村民在環境價值觀上更為先進和積極,而40歲以上的村民則對環境的關心程度較低;從環境知識的認識程度來看,40歲以上的群體、女性群體和高中以下文化水平的群體相對較為淺薄,同時以高中以下文化水平的群體表現更為鮮明;從主動實施綠色生產生活的現實行動而言,女性群體以及青少年的自覺程度以及實際行動較為突出。
村民的環境態度與環保行為在地方依附感上不存在顯著差異。地方依附感(地方依戀、場所依賴),是指個體對于周圍環境的滿足以及歸屬感。一般而言,對該地環境的了解程度越深,產生的責任與擔憂越強烈。而在走訪中,我們發現外來移民(例如宜昌三峽庫區移民)與當地村民,雖有居住年限、地方依附感不一,但在環境態度以及環保行為的自覺性上,并無明顯差異。
村民的環境態度與環保行為在家庭月收入方面,不存在顯著差異(F=2.336,P=0.075),即村民收入的高低不會影響村民對環境的態度與行為,但其大學生下鄉創業群體的得分最高;此外,湖北省內不同地區,其得分具有一定差異,但差異并不明顯。我們根據具體得分自然劃分出鄂西、鄂東、鄂中三個區域,鄂東地區得分普遍高于其他地區,在比較地區特色與差異之上,我們認為這可能與其經濟發展水平高、以武漢市為依托、城鄉一體化進程領先有關。基于前述推論,我們根據問卷具體各小項的得分不同,數據分析顯示鄂東部地區的知曉度、踐行度要比中西部高,但認同度不如中西部,由此我們認為經濟與文化程度一樣對村民環境意識的影響較大。譬如鄂東地區村民被調查者普遍對當前生態環境狀況表示高度擔憂,最關注的問題有霧霾、飲用水安全、重金屬污染等,而鄂西與鄂中部地區表現不明顯。
四、結論分析
通過對照國內外的類似研究,我們可以看到,與城鎮居民的環境意識相比,農村居民的環境意識更為淡薄。村民的環境認知、環境行為的自覺程度,這兩者之間并不存在理想狀態中的正相關線性關系。無論是抽象的還是具體的環境行動,村民的環保行為關心程度均不高,并且僅僅停留于觀望層面。關于中國社會發展的優先次序,村民最優先考慮的是經濟發展,絕對收入增長而相對收入下降的農村村民,他們對經濟利益的增長情有獨鐘:犧牲經濟增長或減少社會福利來換取環境改善的道路,村民在過去的形而上的整頓風中已經用腳投票——并不踴躍參與環保活動。然而,從農民的行動邏輯中,我們欣喜的發現,村民已經有了“生態價值”的初步意識。在訪談中,我們也了解到幾乎每位村民都對水體富營養化、土質污染、工廠污染發出了嘆息與不安,但事后卻沒有更進一步的思考和行動;同時,我們也看到,幾乎人人都抱怨他人——以環境為代價的經濟行為(圍湖造田、開墾山林),但人人都樂衷于此;并且如若要打破這一格局,人人卻都有一種捍衛的自覺、難得的默契。環境態度與環保行為的掣肘,絕不僅僅是觀念的問題,而是我國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多種因素長期作用的結果。針對以上分析結果,筆者作如下深入探討:
(一)社會體制的淵藪
村民對農村環境問題的認識以及行為選擇,同質化較強,具有局限性和單一性,這可能是與當前壓力型體制和政經一體化體制有著莫大淵藪。20世紀90年代后期,環境污染的治理已經從純粹技術性問題深化為各個利益群體博弈的經濟社會問題。基于經濟發展和政治體制的“一邊倒”,地方政府與企業形成了利益共同體。無論是純農地區還是城市與農村結合的縣域地區,都深刻體會到城市化進程中的“陣痛”:一方面,外部供應系統失靈,農村環境治理的社會環境、相應的組織保障機制以及開放的法治環境和輿論氛圍,遠不及于村民所向往的大城市的供給;另一方面,原子式的小農個體因其分散性且不具有深厚的組織淵源,因而無法與家庭之外的其他力量進行抗衡,在當局者轉換陣營時,村民則當然成為環境決策的局外人和環境問題的客體。
此次調查的江漢平原屬于典型季風水稻農業區,其面源污染與生態破壞有深刻的社會原因。其一,商品率、機械化、集約化程度低,小農式耕作方式的封閉性和自給自足性,導致了個體在解決外部性生態環境問題上先天不足。其二,公民權利意識淡薄和行政中心理念是環境問題的觀念成因。村民社會是要比大中城市封閉得多的人情社會,村民們對于法治的崇尚和理解都要比大中城市遜色,從而人們更加容易迷信“人”而非尋求法律意義上的救濟。村民個體力量弱小,需要核心人物領導村民形成組織來表達訴求。其三,行政國家高度集權的體制特征回潮。行政吸納社會仍在較長時期內存在,這其中就包括農村基層組織的行政化。加之,當前的財政稅收體制、政績考核機制、公務員福利保障機制均源于當地的經濟創收,利益驅動下,犧牲環境利益與公眾福祉也有了社會妥當性。基于前述的政治經濟一體化,在經濟大旗的指揮棒之下,代表群眾利益的自組織逐漸異化。在沒有核心人物的領導后,村民自身沒有力量與強權抗衡,更加劇了集體行為的困境。其四,不可忽視的是,環境這一公共物品本身的非競爭性和排他性對政府科以了廣泛義務,需要國家的促導、強制、參與來克服村民普遍的搭便車心理。然而,正如前文所述,農村環境公共服務仍處于起步階段,農村環境保護缺乏一系列制度、設施等外部供應系統。綜合以上,從外部環境上講,這一論述在解釋中國環境問題時具有較強的針對性。
(二)文化教育的熏陶
不同年齡階段的村民對環境態度的看法差異性明顯,基于個體的差異根源,我們從社會文化的視角探尋環境問題的內在邏輯:訪談發現,80后、90后、00后生態觀強烈。據了解,學校將環境知識納入學校教育內容,培養學生的環境觀念,從而塑造學生的環保行為。學校教育是人們環境態度與環保行為的啟蒙,反觀中老年這一群體,尚未接受現代生態理念教育,而其本身農業社會長期形成“親土地”的生產、生活方式,在現代工業文明的荷槍實彈之下慘遭淘汰;而在外源污染泛濫之下,傳統“天地人”的村落形成傳統的社會規范,環境道德價值觀又瀕臨淪喪,因此該群體對環境科學認知落后于民族。然而,雖然青年群體相較于年長者,其環境觀念較為科學,但仍然是模糊的、片面的、不系統的,且在環境行為的意向上,青年人的表現并不突出,年齡差異并不明顯。態度與行為之間的異化與悖論,凸顯了當前環保宣傳工作的蒼白。在受教育程度低的農村地區,環境教育的針對性、宣傳的廣度與深度,還難以滿足當今生態公民的要求,迫切需要政府完善課堂內與課堂外的環境宣傳與普及工作,營造重視自然的環境倫理風氣。
環境保護部公布我國首份《全國生態文明意識調查研究報告》中顯示,我國公眾的環境意識呈現“認同度高、知曉度低、踐行度不夠”的狀態,也進一步證實了村民的環境態度與環境行為之間并不是亦步亦趨的。經走訪發現,村民的環境態度廣泛受制于外部硬件設施(情境因素),個人的環保行為不僅取決于環境態度,也與外界環境公共服務系統的供給淵源廣闊。村民將環保行為的難以深入歸責于農村基礎設施落后,人文環境與硬件設施雙重困境。一方面,城市污染向鄉村大規模轉移,當前農村的污染排放已經觸目驚心,而農村的環境基礎設施建設嚴重滯后,城鄉環境公共設施呈中國特色的二元結構;另一方面是法規標準真空,宣傳教育低端,農村環境管理缺位。由此,硬基礎的塑造與軟環境的熏陶是環境治理之一個問題兩個方面。
(三)性別與環境科學認知
在本次檢驗中,社會性別差異對環境科學認知產生差異性影響,在農村地區也得以驗證。其中,環境態度在性別上存在顯著差異(F=3.305,P=0.023)。正如龔文娟(2007)對中國城市居民的環境關心和環境友好行為的社會性別差異檢驗結果一樣,村民的環境關心水平普遍偏低,其中抽象環境關心水平男性高于女性,但實際的環境友好行為比例男性卻低于女性。相比于城市,農村地區更為典型,這可能與農村“女主內”的傳統觀念相較于城市更為濃厚相關;在私人領域內的環境友好行為比例女性高于男性,比如女性在“生產生活用水的循環利用”這一選項上,選擇“盡可能”的為73%,而同比的男性卻大多表示不太經常;相較私人環境友好行為而言,公共環境友好行為性別差異并不明顯,男女的親環境行為比例都走低。這正對農村某些地區“屋內現代化、屋外臟亂差”的現狀做出了解釋。
如前文所指,農村婦女與農村生態環境之間的聯系也具有獨特性。一方面,婦女在生態環境影響中的地位與作用有別于男性,婦女是家庭生活事務的主要承擔者,家庭主婦基本上決定了一個家庭的飲食習慣、生活規律甚至家庭硬件環境的建構,綠色農村家庭消費的踐行,其主體基礎主要在于婦女群體;在生產活動中,婦女的工作方式對生態影響重大。在采訪中我們了解到,被采訪群體中的婦女承擔了79%的家庭種植業和養殖業,主持著92%的生活實踐、消費實踐。該群體在生產以及生活過程中能否兼顧環保的要求,在開發生態環境的經濟利益的同時,洞見到環境的生態價值以及美學價值等,對于低碳農業發展之路也尤為關鍵。另一方面環境對婦女造成的影響與感受有別于男性。女性的角色代表著自然與本源,擁有獨特的環境感受能力,“婦女在環境保護和發展中發揮重大作用,這標志著婦女在環境決策程序中地位得到了很大提升”(1992年在里約熱內盧召開的聯合國環境和發展大會中闡明),而這一點,在婦女對消費品和消費方式的選擇等具體環境行為之中,表現得淋漓盡致。此外,婦女除了作為生產和消費活動的重要成員,在家庭教育中也具有重要的影響力——婦女肩負著環境保護意識和環境保護責任,耳濡目染著下一代的生活習慣(具體的親環境行為)、環境觀念以及價值取向。婦女在環境科學認知上的敏銳與巨大導向作用,足以表明婦女們的環境態度與環保行為,這關系到廣大農村未來的環境狀況,也決定了農村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增強農村婦女的環保意識與參與能力,促進婦女投身到環保工作中來,將會是美麗鄉村建設、農村生態公民塑造的重要方面。
綜上所述,大到整個“社會體制”、細到“文化教育”、小到村民個人的“性別與環境科學認知”,歸根結底都無外乎起因于環境態度又受制于現實的情境因素。而這正與Stern和Dietz提出的ABC理論不謀而合,環境行為(B)是個人的環境態度變量(A)和情境因素(C)相互作用的結果。農村生態公民的培育,在維度上一方面需要形成環境保護、環境治理、環境維權、環境風險規避、環境危機預防與處理等知識、能力與素養結構,以應對日益多元、復雜的環境議題;另一方面,更需要外部供應系統提供物質保障。不僅要讓公民形成“有關環境及環境問題的知識、解決環境問題的技能、保護和改善環境行為的價值觀”,更重要的是,完善外部供應系統,讓村民有主動做出環保行為的可能。
五、進一步討論
總之,文化程度與環境態度有最顯著的相關性,學校教育對于人們環境態度的形成影響廣泛而深遠。一方面是環境惡化的現實所帶來的直觀感受,另一方面,科學的環境知識的普及教育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著村民的環境價值觀。因此,普及生態環境知識對于當下農村生態公民的培育顯得更為突出。于此本文認為:
(1)在美麗鄉村建設、生態公民培育這一問題上,環境意識的提升并不能直接轉化為環保行為。在維度上,應當將村民當前受情境因素制約的現實困境納入研究領域,克服現有研究缺乏的系統性、持續性和對話性,塑造實施親環境的外部硬件,使村民友好的環境行為意向能夠自覺轉化為村民環保行為。
(2)應提升方法論自覺,采取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和策略,以微觀、地域性、特定的環保項目、環保活動為重點,進行橫貫層面的比較和縱貫層面的跟蹤研究,并將“方法”置放到調查研究的重心中去。
(3)在宣傳和教育方面,基于環境態度的三因子結構假設年齡、性別、文化程度與環境態度的相關性,注重和村民之間的雙向溝通,考慮村民的意愿和偏好,增強宣傳對象的針對性,發展村民喜聞樂見的環境宣傳。
(4)特別是,由于在不同的自然生態區域和社會發展條件下,社會個人特征均對環境科學認知產生差異性影響。所以,培育生態觀念的內容與方式也應因地制宜,重點在于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相結合,從普及環境知識向培養環境意識、變革環境觀念、增進環境情感和促進環保行為轉變;從親環境的口號到腳踏實地地加強外部硬件設施引導村民環境行為。如此,環境意識的調查研究方能走出簡單的“提升環境意識”止于表象的窠臼,觸及美麗中國建設的深層。
[1]武春友,孫巖.環境態度與環境行為及其關系研究的進展[J].預測,2006,(4).
[2]包智明,陳占江.中國經驗的環境之維:向度及其限度[J].社會學研究,2011,(6).
[3]趙宗金,董麗麗.地方依附感與環境行為的關系研究:基于沙灘旅游人群的調查[J].社會學評論,2013,(3).
[4]唐明皓,周慶,匡海敏.城鎮居民環境態度與環境行為的調查[J].湘潭師范學院學報(自然科學版),2009,(1).
[5]邵鳳孌,王永貴,王慧濟.濟南市高校大學生環境意識調查研究[J].環境科學與管理,2010,(9).
(責任編輯周吟吟)
蔡科云(1978—),男,湖北大學政法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法社會學;孟燦(1994—),女,湖北大學政法與公共管理學院2012級法學本科生。
D422.7
A
1671-7155(2015)03-0067-07
2015-0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