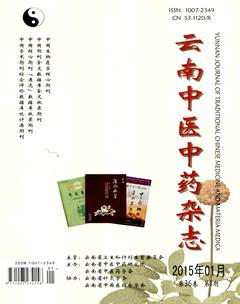胃腸病治從脾腎肝芻議
吳玉濤
關鍵詞:繼承;實踐;體驗;創新中圖分類號:R256.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2349(2015)02-0012-03胃與腸,在中醫理論中屬“六腑”之列,其生理特性是“以通為用”、“以降為和”。胃腸功能為“受納腐熟”、“泌別清濁”、“傳導糟粕”,其與現代醫學所言的胃腸功能有類似之處,但又不完全相同。中醫認為,胃腸的消化吸收及代謝排便,又與脾的運化、肝的疏泄、腎的氣化溫煦密切相關。因此,中醫對胃腸疾患的診治則不僅著眼于胃腸,更要從整體考慮,以調理臟腑關系為主旨。本文僅就胃腸病治從脾腎肝試作探析。1 立論依據
中醫認為,脾胃同處中州,胃受納腐熟水谷,向下傳至小腸,通過小腸的泌清別濁,清者上傳于脾肺,由脾的升清、肺的宣肅以濡養機體;濁者下傳于大腸排出體外。《內經》所謂的“飲入于胃,游溢精氣,上輸于脾,脾氣散精,上歸于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津四布,五經并行”1以及“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瀉而不藏,宣五臟濁氣,名日傳導之府,此不能久留,傳瀉者也”[1]便是對飲食物消化、吸收及排泄過程的描述。但在上述升清、降濁、化物、傳導過程中,尚需肝的疏泄調達,使脾能升清胃能降濁;腎的氣化溫煦,使胃能腐熟脾能運化。雖然,心主血脈的運行、肺主津液的輸布以及三焦的氣化等,也是飲食物消化吸收必不可少的重要環節。但是,在中醫長期的臨床實踐過程中,對于胃腸道疾患的診治,更多地是從脾從腎從肝論治。2前人經驗
中醫認為“腎為先天之本”、“脾為后天之本”,歷代醫家對脾腎在診治疾病中的重要作用都很重視。宋·李東垣著《脾胃論》強調“脾胃之氣既傷,而元氣也不能充而諸病之所由生也”[2],而同時期的許叔微在《傷寒發微論》中則強調“真氣完壯者勿治,真氣虛損者難治”[3],朱丹溪在《格至余論》中也說:“氣常有余,血常不足”,治病則重視“滋其化源……養其本然之真”[4]。許、宋二氏則強調補益腎之真元的重要。自此則有后世醫家的“補脾不如補腎”或“補腎不如補脾”之說。諸如:明·方隅謂“人以脾胃為主,而治病以脾胃為先”[5]。清·吳澄《不居集》中也謂:“凡察病者,必先察脾胃強弱,治病者,必先顧脾胃勇怯,脾胃無損,諸可無慮”[6],而張景岳在《類經附翼》中則說:“治病必當求本,蓋五臟之本,本在命門……補脾不若補亦些謂也”[6]。程國彭在《醫學心悟》中則說:“是知脾腎兩臟,皆為根本,不可偏廢”[7]。
肝為剛臟,職司疏泄,調暢氣機,司理升降,其在疾病診治過程中也占有重要位置。《內經》謂:“百病生于氣也”[1]、“清氣在下,則生飧泄,濁氣在上,則生嗔脹”[1]。張景岳謂“病之生也,不離乎氣,而醫之治病也,亦不離乎氣”[6]。清·周學海在《讀醫隨筆》中說:“凡十二經之氣化,皆必藉肝膽之氣化以鼓舞之,始能調暢而不病……醫者于調肝,乃善治百病”[6]。先賢有關治病要重視肝、脾、腎的論述,都是自身臨床實踐的體驗。可見,胃腸病治從脾、腎、肝也是以前人經驗為借鑒的。3臨床體會胃腸疾患,包括胃炎、消化性潰病、痢疾、腸炎、胃腸功能紊亂以及胃脘痛、嘔吐、泄瀉、便秘等等。這些都是臨床極為常見的消化系統病癥。有人觀察發現,酗酒后,幾乎100%會引起急性淺表性胃炎;有人統計,慢性胃炎發病率青年人占20%,而60歲以上的老年人則占52%左右[8]。腹瀉、便秘者臨床更為多見。據個人臨床體驗,中醫藥治療胃腸道疾患常有一定規律可循。3.1 虛寒治從脾與腎 前人謂:“脾喜燥而惡濕,胃喜溫而惡寒”[5],李中梓在《醫宗必讀》中說:“陰證多寒,寒者多虛……茍涉虛者,溫補脾腎,漸欠康復”[9],葉天士《臨證指南》治吐案中更有“治胃之法,全在溫通”之說。由此可知,胃腸道疾患,尤其是慢性胃腸病,常以虛寒證較為多見。臨床治療也多從溫補脾腎投治。諸如:慢性胃炎,或消化性潰瘍引起的胃脘痛,一些臨床醫生則常用理中湯、黃芪建中湯,或香砂六君湯、良附丸之類加減化裁,以健脾調中、溫中和胃,或兼用緩巾止痛以治;慢性腸炎、胃腸功能紊亂,或慢性結腸炎引起的腹痛、腹瀉或便不成形等,則常用桂附理中湯、四神丸,或真人養臟湯之類,以溫陽益腎、健脾溫中,或兼用同澀止瀉以治……凡屬虛寒性胃腸疾患,黃芪、茯苓、白術、附子、肉桂、吳茱萸、香附、丁香、補骨脂、砂仁、元胡等,則每為多選用藥。一些名醫大家也常如是。例如:秦伯未氏在《謙齋醫學講稿》中介紹,以黃芪建中湯化裁治療消化性潰瘍病[10],《蒲輔周醫療經驗》集中介紹,蒲老以補中益氣湯治療虛寒久痢[11],岳美中以理中湯加吳茱萸,治療漚吐、腹痛[12],山東中醫藥大學教授祝德軍,用四神理中湯治療潰瘍性結腸炎而致的腹痛、久瀉[13]……由此可見,對于虛寒性胃腸疾患治從脾腎,不僅有理論依據,更有臨床的實踐基礎。3.2實熱治以肝胃腸前人謂:“肝氣有余不可補,補則氣滯而不舒”[6]、“諸病多自肝來,以其犯中宮之士,則性難馴”61。清·陸以湉在《冷廬醫話》中更謂:“今人所謂心痛、胃痛、脅痛,無非肝氣為患”[6]。中醫更有“氣有余便是火”的說法。可見,因肝而致的胃腸疾患常以實熱證居多。兇此,對實熱性質的胃腸病癥,中醫則常以疏肝理氣、疏肝和胃、清肝利膽,或清胃瀉火、消食導滯為治則。四逆散、大柴胡湯、左金丸、柴胡疏肝散及涼膈散、承氣湯之類,則每為常用選方。而柴胡、梔子、白芍、郁金、枳殼、丹皮、黃連、知母、大黃等,則多為常選用藥。諸如:因情志不暢引起的胃脘疼痛,或腹痛、腹瀉,則常用柴胡疏肝散、痛瀉要方加減;脅痛、腹脹、反酸,則可用左金丸、戊已丸化裁;若因飲食不當引致胃脘疼痛,或腹脹、吐瀉,則可選四逆散、平胃散、保和丸之類……現代一些臨床醫家,在繼承前人經驗的同時,又常有新的創建和體驗。諸如:京城名醫關幼波以白頭翁湯加秦皮、地榆炭、焦檳榔、阿膠珠,治療急、慢性痢疾[13]:劉渡舟以大柴胡湯加郁金,治療急性膽囊炎引起的脅痛、嘔吐、便秘[13];印會河以芍藥湯合大黃牡丹皮湯加馬齒莧、敗醬草等,治療結腸炎引致的腹痛、腹瀉[13]……總之,屬于實熱性的胃腸道疾患,中醫以從肝、胃、腸投治者居多。3.3標本治從的選擇 “治病求本”是巾醫辯證論治的核心,中醫所謂的標與本是一個相對概念。從“臟為本,腑為標”而論。胃腸病治從脾、腎、肝,也是治病求本的體現。治病求本,又有“治標”、“治本”、“標本兼治”以及治從先后和主次的不同。無非強調治病要分清疾病的矛盾主次而……臨床更多地是采用“標本兼治”,只是側重有別。胃腸病的治療同樣如此。諸如:寒邪客胃、飲食所傷、或肝氣犯胃、脾胃內虛均可引致胃脘疼痛,在針對病因、病機治療的同時,均宜酌情加用白芍、甘草、或元胡之類以緩中止痛;嘔吐,無論原因為何,其致吐機理均為胃氣上逆,皆可加用半夏、竹茹、生姜以止吐;痢疾,有虛寒久痢,也有濕熱下痢,在溫補同澀或清利濕熱的基礎上,皆可加用有抑菌、抗菌作用的白頭翁、秦皮、馬齒莧等,明·張景岳治胃腸的“中滿、大小不利”時,也十分強調“治標治本當相半矣”[6]。可見胃腸病的治療多以“標本兼治”最為常用。中醫藥學是以臨床實踐為基礎的經驗醫學,雖然它的某些認知方法,尚難被現代醫學所認同,但它確切可靠的治病效果,千百年來都被世人所公認和受益。認真發掘繼承前人的實踐經驗,發展創新符合時代要求的中醫藥學理論,乃是現代中醫藥工作者的共同使命。參考文獻:[l]南京中醫學院醫經教研組黃帝內經素問譯釋[M].上海:上海科 學技術出版社,1959:163;89;265;36.[2]宋·李杲,脾胃論[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57:3[3]中國醫籍提要編寫組.中國醫籍提要[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212.[4]元·朱震亨.格至余論[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56:11.[5]明·方隅,醫林繩墨[M].北京:商務印書館,1967:82.[6]周超凡,歷代中醫治則精華[M].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1:178;11;148;188;339;173;18;186:46.[7]清·程國彭.醫學心悟[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63:32.[8]林乾良,劉正才,養生壽老集[M].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2:176:175.[9]明·李中梓.醫宗必讀[M].上海:上海衛生出版社,1957:246.[10]秦伯未,謙齋醫學講稿[M].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78.200.[11]中醫研究院.蒲輔周醫療經驗[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76:59.[12]中醫研究院,岳美中醫案集[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9:62.[13]張豐強,鄭英.首批國家級名老中醫效驗秘方精選[M].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6:97(上集);25;91;94(續集).(收稿日期:2014 -12 - 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