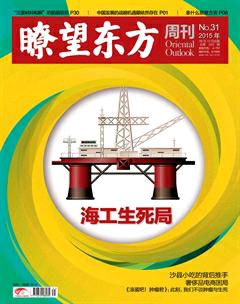“船工”敗局往事
馬雪婷

南通中遠船務設計建造的“希望7號”圓筒型海洋生活平臺出海試航
根據中國船舶工業行業協會日前公布的2015年上半年船舶工業經濟運行情況,6個月內全國造船完工1853萬噸,同比增長6.3%;但承接新船訂單1119萬噸,同比下降72.6%。
除承接新船訂單大幅下降之外,規模以上船舶工業企業的盈利能力同比下降13.3%,包括船舶制造企業以及船舶修理企業均有較大幅度的下滑,“受全球航運市場低迷、油價持續下跌的影響……企業交船難、融資難、盈利難、轉型難等問題依然突出。”
“進入新世紀之后,特別是從2003年開始,國際船舶市場進入快速發展階段。”中國船舶工業行業協會高級顧問、研究員王錦連告訴《瞭望東方周刊》,在這個契機下,中國造船產業發展進入快速通道,并于2005年進入世界前三名,“但這個大發展也存在一定的問題,導致目前產能過剩。”
這一跌宕起伏的產業發展歷程,足以給任何行業提供經驗、教訓。而如何在產業趨勢之中仍能把握前途,提早推動升級、轉型,可能不僅是“船工”、“海工”行業指導者的任務。

2007年3月20日,大連船舶重工有限公司為新加坡太平船務公司建造的4250TEU(標準箱)集裝箱船交工,其建造周期達到了世界造船先進國家的水平
第一造船大國的動力
改革開放后,隨著國門打開,通過國際合作,中國船舶工業開始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并承接香港船東的訂單。到2000年前后,技術上逐漸起色的中國造船企業進入國際市場。
2003年國際船舶市場的大發展,給中國船舶工業的發展提供了強勁動力。彼時,全球海運運力需求高漲,船舶供不應求,推動了世界造船業迅猛發展,造船大國低成本擴張,發展中國家趁機大力發展船舶工業。而加入WTO后中國與全球貿易的迅速增長,更是拉動了中外海運市場。
在中國,各種資本力量開始向船舶工業聚集,“之前市場主要以國有企業為主,在這個階段民營企業開始大發展,推動了我國造船大國地位的確立。”王錦連說。
彼時船舶工業的迅速發展,甚至連船舶維修業也成了一個“聚寶盆”。“那時,國內修船行業一片紅火。”南通一位船舶企業的負責人向《瞭望東方周刊》回憶說,當時排隊等待修理的船只,從南通港可以一直排到上海吳淞口,“當時的修船業很賺錢,毛利能高達30%,最高的時候甚至到了100%。”
這樣的狀況,吸引了大量投資者,越來越多的資本競相涌入船舶維修行業,甚至到2006年,僅在南通、舟山等長三角地區,就陸續出現了數十家修船企業。
哈爾濱工程大學船舶學院院長韓端鋒則告訴本刊記者,此間我國造船工業的快速發展,還得益于中國船舶研發能力增強、造船模式轉換帶來的生產效率提升,以及勞動力價格低廉等因素。雖然國家對此進行了相應扶持,“與日、韓、歐美等國相比,我們的扶持力度要小得多。”
農民沙灘造船
工信部高技術船舶科研計劃制造技術組成員、哈爾濱工程大學船舶工程學院教授孟梅認為,2000年到2008年期間,中國船舶業從工業能力和生產規模獲得的快速發展,從更大格局看也是一個制造業轉移的結果。
那時世界造船業有韓、日、歐三極。第一造船大國韓國已處于成長期的后期,發展潛力有限,而且隨著當時韓元升值幅度較大,勞動力成本居高不下,競爭力已出現下降跡象;日本則已進入成熟期、歐洲已進入衰退期。
世界造船業由勞動力高成本國家向勞動力低成本國家轉移,是普遍現象,盡管通過技術創新可以延遲這種轉移,但成本仍然是影響造船業競爭力和產業轉移的最顯在的因素。
與中國其他制造業一樣,人口紅利給造船業提供了極大的競爭優勢。當時專家估計,中國船廠的人力成本只有日本同行的20%到30%之間。在勞動力成本占一艘新船成本高達30%的情況下,中國造船廠顯然具有優勢。
大量船東開始向國內造船廠下單。比如2003年底,中國船舶重工集團公司與中國海運(集團)總公司簽約,為其建造9艘4250TEU集裝箱船。這個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簽約儀式,曾經創下國內航運業一次在國內造船數量最多的紀錄。
在政策鼓勵和市場吸引下,2006年前后中國船舶成交量頻刷紀錄,成交價格也居高不下,這樣的市場形勢下,除與船舶有關的行業,甚至服裝業、房地產以及煤炭等諸多行業的資本蜂擁進入船舶行業,期望在蒸蒸日上的造船業里分到一塊蛋糕。
那時,中國造船企業承接新船的訂單幾乎占全球市場份額一半以上。“最好的時候,2008年之前全球都在瘋搶的散貨船,單價炒到1億美元一條。”上海一家大型造船廠的副總經理告訴《瞭望東方周刊》,到現在同樣的散貨船,在人工費、材料費上漲,技術已經明顯改進的情況下,還是面臨腰斬,降到5000多萬美元。
除中船集團公司、中船重工等國內幾家造船巨頭拿下接近70%的訂單,當時剩下的新船訂單幾乎全部落入江浙一帶的新興民營造船企業手里。
造船業最紅火的時候,浙江一帶的農民也開始在沙灘上造船。一位合資造船企業的工會主席回憶說,當地有些村子集資起來就開始干造船,“枯水期在沙灘上擺墩造船,等到汛期時借助上漲的江水讓船體下水,這種粗放的造船技術與上世紀80年代之前沒有太大的差別。”
因為接單太多,規模不大的船廠也會同時在建3條船,“造船的工人加班到夜里十一二點很正常,一條船三四個月內就可以下水。”
危機帶來的“清涼劑”
好景不長,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不期而至,全球航運業進入蕭條狀態。特別是此前船舶訂單的不斷增加,金融市場動蕩進一步加劇了運力過剩的局面。“大發展階段同時存在一定的問題,就是導致產能過剩比較嚴重。”王錦連說。
那時候,中國船舶工業規模上已經超過各國成為世界第一,“但是在技術方面我們仍然落后于日韓等國。”王錦連認為,此外在生產效率和管理水平、造船的各種指標方面,諸如鋼材利用率這樣的細節上,與西方船舶企業相比都有較大差距。
國際金融危機之后,船舶行業的日子一直不好過。最困難的時候,船東只要一接船就虧損,給船找地方靠泊、融資、雇船員都需要花費成本。那時運營一條船一天的成本為1.2萬美元,而市場租金卻只有3500美元,還不到成本的一半。
除了有長時間積累的大型船廠,對于那些跟隨投資熱潮盲目進入船舶行業的船廠來說,一旦船東棄船,資金鏈就會斷裂,部分船廠開始為自己的盲目投資“埋單”。
此外,核心技術的缺失,讓一些船廠不得不依靠壓低價格去獲得新船的訂單。比如一條“好望角型”散貨船,當時國際市場價格大約為7700萬美元,韓國建造的價格約為8300萬美元,而在中國因為行業內的惡性競爭一度壓低到6800萬美元。
除經濟危機因素之外,韓端鋒認為,中國船舶制造業產能過剩的另外一個原因,是有些地方政府的不科學推動,“船舶工業對GDP具有較強拉動作用,使得地方政府繞開國家政策監管,盲目上馬了諸多船廠。”韓端鋒說。
孟梅也有類似的看法,進入新世紀之后的那段時間,中國船舶制造業的大發展“有一點失控”,“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到今天也沒有消失,對中國船舶行業來說,我覺得這是一片‘清涼劑,可以讓我們以更加冷靜的心態去調整,而不是一味去追求做大。”
孟梅認為,國際金融危機讓中國船舶行業進入了一個重大的調整時期,“也不是壞事,這會逼迫船舶企業在專業技術上作進一步的提升。”
而諸多船企選擇的升級之路,就是海洋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