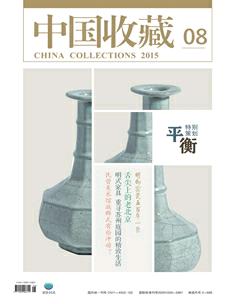廣陵涵秋
姚一鳴

大東書局1923年5月28日出版的《半月》第二卷第十二號(hào),是“李涵秋先生紀(jì)念號(hào)”。封面為謝之光所繪民初婦女圖,內(nèi)有袁克文的紀(jì)念題詞、李涵秋先生墨跡和簽名、李涵秋先生之遺物等圖片多幅,并且刊有紀(jì)念李涵秋的文章13篇,還有挽詩挽聯(lián)等近百首。
《半月》編輯部還為紀(jì)念號(hào)寫有說明:“本期李涵秋先生紀(jì)念號(hào),是為對(duì)于李先生表示悼念和敬意而作的,所有材料,除自撰的幾種外,其遺像遺物照片事略著作一覽表挽聯(lián)挽詩等,都有李先生介弟鏡安先生供給。……關(guān)于紀(jì)念李先生的文字,外間也有投稿幾種,只因寄到已遲,來不及加入,特此致歉。”
李涵秋卒于1923年5月13日,相隔一月有余的6月28日出版的《半月》即有紀(jì)念號(hào),除感嘆編輯出刊速度以外,可以見得李涵秋在舊時(shí)文壇的地位。那時(shí)的舊派文人紛紛撰文紀(jì)念,逝去的李涵秋似乎宣告著以鴛鴦蝴蝶派為代表的一個(gè)時(shí)代的終結(jié)。
李涵秋是近代著名小說家,別號(hào)沁香閣主,江蘇揚(yáng)州人。他生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少年時(shí)即聰穎過人,并且酷愛讀書,放棄科舉而致力于古詩文。初時(shí)以授課為生,后受李石泉聘赴漢口為西席,居于漢口四年,逐步走上了寫作之路。李涵秋于1909年至1911年間在漢口《公論新報(bào)》刊載小說《過渡鏡》,至五十二回因辛亥革命而輟刊。1914年復(fù)至上海《大共和報(bào)》、《神州日?qǐng)?bào)》續(xù)刊四十八回,且改名《廣陵潮》,并由震亞書局出版,一舉成名。李涵秋平生著作頗豐,所著小說為文言10種、白話文23種,另有筆記雜著多種,代表作有《廣陵潮》、《俠鳳奇緣》、《戰(zhàn)地鶯花錄》、《沁香閣詩集》、《沁香閣筆記》等。1923年5月,李涵秋因腦溢血病逝于揚(yáng)州,享年虛歲50。
在《半月》李涵秋先生紀(jì)念號(hào)上,同為舊派文學(xué)大家同時(shí)又是《半月》主編的周瘦鵑所寫《我與李涵秋先生》,披露了不少當(dāng)年他和李涵秋先生交往的軼事。在文壇如果論輩分,年長(zhǎng)周瘦鵑20歲的李涵秋應(yīng)算前輩,盡管在翻譯辦刊上不如周瘦鵑,可論創(chuàng)作李涵秋要早于周瘦鵑,并且取得的成績(jī)也要優(yōu)于周瘦鵑,尤以長(zhǎng)篇小說的創(chuàng)作最具影響力,其中《廣陵潮》為近代文學(xué)之佳作。李涵秋在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上取得的成就,亦讓周瘦鵑欽佩不已。
在《我與李涵秋先生》一文中,周瘦鵑除了褒獎(jiǎng)李涵秋的文學(xué)成就外,也透露了他們之間一些交往的細(xì)節(jié)。周瘦鵑在文中摯情地回顧了和李涵秋先生的幾次交往,并附了李涵秋先生同樣寫得出色的舊體詩作。周瘦鵑感嘆由于自己文事太忙寫作太多,對(duì)于李涵秋先生的幾部長(zhǎng)篇小說都只看了部分和大概。倒是對(duì)李先生十年前署名“包柚斧”、應(yīng)《時(shí)報(bào)》征文中選的那本《雌蝶影》,看完后印象深刻。但周瘦鵑也有疑惑,《雌蝶影》為什么不署李涵秋之名?此事實(shí)有緣故。
李涵秋到漢口第二年,看到上海《時(shí)報(bào)》以重金征求長(zhǎng)篇小說的廣告,便寫了一部五萬言的《雌蝶影》,然而由于對(duì)上海人生地疏,不敢貿(mào)然投寄。此時(shí)有詩社好友丹徒人包柚斧得知李涵秋的情況后,說上海有其好友,且識(shí)狄平子、包天笑等人。李涵秋感激之至,說如小說中選可平分稿酬。《雌蝶影》果被《時(shí)報(bào)》錄用,列為三等,但署名卻為“包柚斧”。李涵秋大怒責(zé)問包柚斧,包只得設(shè)宴謝罪,說只得虛名不要稿酬,并先付稿酬一百八十元予李涵秋。事后李涵秋才知包早已取稿酬,且侵吞了七十元。李涵秋因此和包柚斧絕交。到第二年上海有正書局出《雌蝶影》單行本時(shí),作者署名才改為李涵秋。后來李涵秋將此事寫入他的另一部小說《廣陵潮》,小說中的“鮑橘人”就是影射包柚斧,那個(gè)工于心計(jì)而掠取別人著作的小人,是應(yīng)該受到譴責(zé)的。周瘦鵑看過小說《廣陵潮》,但沒看仔細(xì),可能以為這只是小說情節(jié)。
李涵秋早慧,少年便聰穎過人,具有深厚的學(xué)識(shí)功底。自幼受到揚(yáng)州評(píng)話的熏陶,在他成年后創(chuàng)作的小說中有不少揚(yáng)州評(píng)話的技巧和影響存在。貢少芹在《李涵秋》(上海震亞圖書館1923年版)中寫道:“涵秋幼時(shí)最喜聽講,且成癖焉。顧天資極穎慧,一經(jīng)入耳,悉不遺忘,歸即摩肖書中人之姿態(tài)與口吻,于祖母及其母前復(fù)述之,頗得其仿佛。更能例舉書中之情節(jié),語極中肯。”在武漢四年成為了他一生的轉(zhuǎn)折,時(shí)年21歲的李涵秋不僅開始創(chuàng)作小說,發(fā)表了他的處女作《雙花記》(刊《公論新報(bào)》),而且結(jié)交了不少文友,奠定了他踏入文壇的基礎(chǔ)。但在武漢由于作詩結(jié)友中,有人妒李涵秋的才華,把李涵秋教女學(xué)生學(xué)詩說成是革命黨聚會(huì),弄得李涵秋差點(diǎn)被抓。李也將此事寫入《廣陵潮》之中。李涵秋一生大部分時(shí)間居于揚(yáng)州,直到1921年才到上海住了一年,由于不習(xí)慣上海的生活方式,一年后即返揚(yáng)州。
1914年震亞書局出版的李涵秋代表作《廣陵潮》用集錦的創(chuàng)作方式,濃縮了他許多個(gè)人經(jīng)歷,既有相思相戀的浪漫,亦有受騙上當(dāng)、被人陷害的痛楚,小說主人公云麟身上有著太多李涵秋的影子。《廣陵潮》真實(shí)生動(dòng)地反映了從清末到民初這一歷史過渡時(shí)期的社會(huì)百態(tài),如廢除科舉、洋學(xué)初現(xiàn)、男子剪辮、女子放足等,有歷史學(xué)、社會(huì)學(xué)和民俗學(xué)上的價(jià)值,被稱為鴛鴦蝴蝶派的代表作品。駱無涯曾盛贊李涵秋的小說有三大特點(diǎn),“第一情節(jié)奇突,如石破天驚,不可捉摸;第二前后銜接,無顧此失彼失節(jié)現(xiàn)象;第三描寫深刻,入木三分。”畢倚虹更稱贊道:“肥艷濃香之筆,典質(zhì)簡(jiǎn)樸之詞,吾視之不難;獨(dú)尖酸雋冷之言,刻畫社會(huì)人情鬼蜮,吾不如涵秋。”
作為舊派文學(xué)的代表人物,李涵秋并不像周瘦鵑、包天笑、王純根等能擅熟地游走于江湖,能辦刊寫文結(jié)社都不誤。他只是一個(gè)沉湎于寫作的舊式文人,喜歡蟄居鄉(xiāng)下獨(dú)自撰寫一些小說。但由于閉門造車,對(duì)于外部世界和新生事物了解甚少,以至于在其所著的小說中鬧出了不少笑話,如坐馬車去蘇州虎丘,游杭州西湖坐瓜皮船要張帆等等,這些都暴露出李涵秋閉門寫小說的弊端,間接地也反映了舊時(shí)小說家未跟上現(xiàn)代生活的節(jié)奏。
李涵秋所生活的年代正是社會(huì)動(dòng)蕩和革命維新之時(shí),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dòng)爆發(fā)前后,隨著革命的爆發(fā)和深入,以學(xué)院派精英為主的現(xiàn)代知識(shí)分子隊(duì)伍逐漸形成,在意識(shí)形態(tài)領(lǐng)域逐漸占得先機(jī)。與此同時(shí),以鴛鴦蝴蝶派為代表的舊派文學(xué)在市民階層中仍占有較大的比重,新舊文學(xué)爭(zhēng)奪讀者的斗爭(zhēng)從未停歇過。而隨著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dòng)的普及和深入,現(xiàn)代新文學(xué)社團(tuán)也處于萌芽之中,對(duì)于當(dāng)時(shí)的報(bào)刊話語權(quán)的爭(zhēng)奪亦處于激烈之中。就在李涵秋到上海的那一年,商務(wù)印書館的老牌刊物《小說月報(bào)》順勢(shì)而變,在茅盾主編的革新號(hào)上,發(fā)表了大量新文學(xué)作品。
李涵秋是一個(gè)浸潤(rùn)于舊時(shí)教育,有著封建士大夫氣的舊文人,盡管在他的作品中有批判現(xiàn)實(shí)的不合理和倡導(dǎo)進(jìn)步生活方式的內(nèi)容,但從本質(zhì)上說,以鴛鴦蝴蝶派為代表的舊文學(xué)依然有相當(dāng)?shù)木窒扌裕^多地在作品中渲染娛樂和趣味,在文學(xué)的主旨和批判意識(shí)上顯得較為消極。但在晚清至民國這個(gè)特殊的時(shí)期內(nèi),依然有著啟蒙和承上啟下的作用。
1923年的《半月》李涵秋紀(jì)念號(hào),折射的是舊派文學(xué)對(duì)一位前輩的紀(jì)念,也是對(duì)舊派文學(xué)的一種撫慰。上世紀(jì)20年代初期,時(shí)逢舊派文學(xué)再度勃興,大量的以休閑娛樂為主旨的期刊充斥文壇,他們以求新求變來博得生存空間。雖然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dòng)已東風(fēng)吹進(jìn),舊派文學(xué)依舊在市民階層中享有絕對(duì)的影響力,面對(duì)新文學(xué)作家的猛烈炮火,舊文學(xué)開始走向了衰落。李涵秋的去世是一個(gè)偶然,也是一曲舊派文學(xué)的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