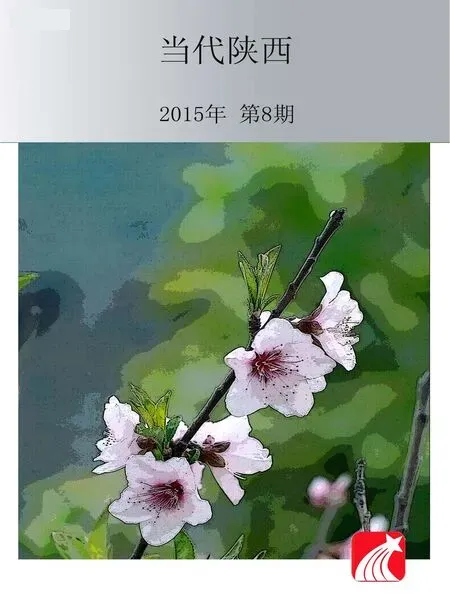縣委書記的擔當、壓力和困惑
文/梁生樹 張 帆(本刊記者)
縣委書記的擔當、壓力和困惑
文/梁生樹 張 帆(本刊記者)
“官之至難者,令也。”400多年前,明朝清官海瑞在《令箴》中說,最難做的官是縣官。
1月12日,習近平總書記同中央黨校第一期縣委書記研修班的學員暢談交流“縣委書記經”,回憶起30多年前在縣委書記崗位上的感悟時說:“我同大家的感受是一樣的,縣委書記這個崗位很重要,官不大,責任不小、壓力不小,這個官不好當……”
“縣官難為”是因這個崗位有其特殊性。一個縣,小則幾萬十幾萬人,大則百把萬人,中央有什么機構,縣一般大多有相對應的部門。對上,要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中央省市的工作部署要落地;對下,要領導鄉鎮、社區,直面群眾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無所不及。
新常態下,“快速轉型與科學發展”“既守規矩又敢作為”“既要金山銀山又要綠水青山”等一道道考題擺在縣委書記面前,使得這些基層政權“當家人”“責任人”面對著前所未有的壓力與困惑。
擔當:不怕“上刀山下火海”
全國優秀縣委書記馮振東,從北京表彰后回到富縣的一次工作會議上,對3名不作為、慢作為的縣部門“老局長”進行毫不留情的批評,并給予3人誡勉談話。
事后有縣級領導半開玩笑地勸他,“心平氣和等著組織提拔就行了,何必多余惹人”。馮振東的“回敬”是,如果用犧牲黨和群眾的利益換取自己所謂的“和諧”執政環境,自己良心上過不去。
馮振東告訴記者,有一個村多年來一直想占用耕地修建廟宇,縣里始終“硬頂著”,他被公示為全國優秀縣委書記的當天,村民就認定是個開工建廟的“好日子”。
他讓相關負責人到村里,明確告訴組織者,自己寧愿不當“全國優秀”,也不會達成“你不攔我開工,我不給你找事”的“默契交易”。村民服從了,也服氣了。
敢于擔當的馮振東能“修煉”成優秀,是陜西有著“能擔當”的政治生態,放眼全國,不少事讓“擔當者”寒心。
執掌有限權力、承擔無限責任,面對困惑與壓力,這是對縣委書記這個群體為官履職的“寫真”。
面對不斷強調的“擔當”這一熱詞,大多數縣委書記的心聲是上刀山下火海都可以,但為擔當者“擔當”是大問題,不能讓流汗的擔當者因擔責而“流血”。
記者梳理,為不擔當“開脫”的“冠冕堂皇”理由是,規矩意識加強;衍生出的“新產品”是“為官不為”。
新常態下,由于責權邊界不清,加之老辦法不靈,新辦法不明,守規矩與有作為形成尖銳的矛盾和對撞。河南一位縣委書記說:“現在亂作為是不敢了,‘容易的上、有風險的躲’這種選擇性作為現象增加了。”
更多縣委書記認為,之所以現在選擇性作為現象突出,都不愿去責任大、風險高、任務重、矛盾多的單位,關鍵是擔當的環境還沒有真正形成。
新形勢下,如何既守規矩又敢作為問題突出,尤其是處于宏觀之末微觀之首的縣級,已無法回避,必須盡快破局。
許多落在縣委書記肩膀上的考核指標、大項目建設、征地拆遷是在上級“行政思維”下制定和確定的,但出現問題卻完全用“法治思維”去問責,當初“拍板”的上級一轉身變成“拍磚”人。
一旦出了問題,一些具有“生殺權”的部門和領導,慣用的方法是“棄車保帥”,身背黨風廉政、安全生產、計生工作等多項“一崗雙責”的縣委書記,很容易成為被棄的“車”,如履薄冰的重壓之下,敢于擔當需冒很大風險。
有縣委書記表示,強調敢于擔當的同時,應該給予他們“合理區間內、非主觀意愿下”的“試錯”機會。
壓力:失眠成為“職業病”
“現在每當想起深入農戶調研時,看到群眾被疾病、災難和貧困折磨后的窘境,常常一個人發呆,甚至責怪自己太‘無能’。”一位剛從縣委書記崗位轉任市級部門的干部告訴記者,自己多次萌生去看心理醫生的念頭,這種焦慮是絕大多數有“良心”縣委書記的“通病”。
他坦言,自己任職縣長和書記近十年,每次訪貧時能做的就是讓縣上相關部門用足、用盡當下所有的惠民政策去幫扶和掏空自己身上所有的錢。但是量太大,僅靠“吃飯財政”遠遠顧不過來,面對“無米之炊”,常常痛恨自己沒有“三頭六臂”。

紫陽縣委書記王曉江在東木鎮調研茶葉產業 陳剛/攝
“當區長沒時間睡覺,當書記卻睡不著。”這是從區長轉任剛兩月的漢濱區委書記王孝成履新感受。
作為104萬人口的“一線總指揮”,王孝成面對的區情是:全市1915平方公里重點發展區,90%以上的區域在漢濱,十二五期間,全市確定了一般財政、人均收入等“五個翻番”硬指標,漢濱缺一項就拖了全市的“后腿”。
漢濱是安康政治文化中心,與重點項目建設、國企改革、征地拆遷“相生相伴”的是,信訪量占全市一半以上。
2014年,漢濱區財政支出是收入的8倍;21.59萬貧困人口要在“十三五”期間“拔窮根”;5年修通了19條通鄉路,卻背負2億元“配套資金”債務,最無奈時,曾動員社會力量捐贈償還;每年新增2500名中學生,相當于年年要新建一所標準化學校……
這些問題和困難,最終匯集到區委書記王孝成這里。再沒有退路,壓力不言而喻。
考核評比對縣委書記是一種考驗,不少縣委書記反映,過去檢查評比要么看虛的數,要么領導帶隊“拉練”看項目,如果不愿“擺紅旗”“造盆景”,只能修煉一張經得住罵的“厚臉皮”。
在資源型縣域“揚煤吐氣”時,陜北一個縣的財政收入就能超過陜南三市的總和,陜南不少縣委書記抱怨,自己是“戴著落后的帽子”上任的。
但一轉眼,陜南陜北縣委書記們的臉色“反轉了”。漢濱區今年上半年GDP增速達11.7%,而陜北不少資源大縣在煤油“量價齊跌”,竟然出現了“負增長”。
讓這些縣委書記們吃不香、睡不著的是,不少媒體報道中,在“負增長”前面喜歡加上“改革開放以來首次”這個定語,“不扭轉經濟下滑的態勢,我都感到自己要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了’。”陜北一位縣委書記舔舔嘴唇上的“火泡”,從牙縫里擠出這句話。
此一時彼一時,佐證縣委書記這個崗位沒有永遠的笑臉,只有永遠的壓力。
返稅收、零地價、融地貸款、搞“工業房地產”、先上車后買票、設寧靜日、給政治待遇,這是縣委書記們以前招商引資的“7種武器”,可老辦法不能用了。陜北一位縣委書記說:“過去強調‘闖冒試’,干部陶醉在這種成就里;如今,財政剛性支出不能減少,質量要求更高,沒了那些手段和環境,發展擔子更重了。”
湖南省平江縣因“火電事件”黯然辭職的原縣委書記田自立,在“今日平江”微信公眾號發布的一篇題為《寄語平江,祝福平江》寫道:喬治·奧維爾有句名言:‘在未被證明清白之前,圣徒總是被判定有罪。’何況我們都不是圣徒,誰也用不著推卸責任,誰也用不著叫屈鳴冤。”
2014年7月,“平江擬建火電廠”一事在網上持續發酵,至9月中旬,部分民眾連續三天群體性上街游行反對該項目,最終以縣政府一紙通告宣布“停止項目前期工作”收場。
如此博弈,田自立不甘心也無奈。
困惑:權小責重應對難
一位縣委書記用“雙三角形對頂”,表達他所理解的縣委書記所處的位置:一個倒置的大三角形壓著一個正放的小三角形,縣委書記恰恰處在對頂的兩個三角形尖兒上。
上級層層壓擔子、派任務,最終都集中落在縣一級,但縣里資源有限、回旋余地有限。把這個圖倒過來,立時變成上小下大,又恰似縣級政權和群眾的關系,一方面新時期群眾期望值高、訴求多;另一方面,縣級權力機構解決問題的能力有限,這就讓這個崗位成為上下施壓的最大承受者。
困惑一:很大的精力用在協調溝通各種關系、參加會議、應付檢查指導上,難以靜心研究問題。
不少縣委書記講,從中央到省市,三令五申精簡會議,但減掉的都是原本縣委書記不參加的會議,要求“一把手”參加的會議實際沒減多少。有些縣委書記戲稱自己是“三陪”書記:整天陪著上級領導檢查工作、陪著匯報工作、陪著吃工作餐。
困惑二:信訪維穩是最大“心病”。陜南一位縣委書記講了個“生動”的“維穩案例”:北京召開奧運會,為了維穩,小縣投入干部最多時,平均8名干部“維穩”一名纏訪戶,最終以“零上訪”圓滿完成任務。國家部委一位司長讓其介紹經驗,這位書記實話實說:不惜成本、不擇手段。他強調最難的是后4個字,既要確保“不離開視線”,又不能觸碰“維穩對象”的權益。
一些縣委書記中流行著“擺平就是水平,沒事就是本事;搞定就是穩定,妥協就是和諧”的順口溜。隨著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訴求的利益性、參與的群體性、成因的復雜性、方式的偏激性日漸突出,加之網絡輿論壓力加大,“上訪變上網”,信訪維穩壓力驟增。
困惑三:部門權力化、權力利益化。一些權力部門把正常的經費下撥當“施舍”,只強調自己的“一畝三分田”,對基層的實際視而不見。
一些縣委書記抱怨,你說一些制定政策者不懂基層實情,他們講起來有深度、有高度,一套一套的,但出臺的政策落實難。惠農經費中,農、林、水等等各口只管撒“胡椒面”,縣里整合資金欲干像樣的涉農工程,從政策上就通不過。這些貌似歸口管理,其實都為了將中央財政的“蛋糕”攬在懷里,等著基層來“磕頭”。
困惑四:“三無記者”經常騷擾,網絡輿論壓力大。一位縣委書記無奈地說,每天能收到類似“我在你縣發現一處污水直排口,速來縣城某賓館說明情況”的“媒體求證短信”。有一次他都編好了“你是什么東西”的短信,忍了忍沒發出去。他笑著說,擔心這條短信一發,“會搶了汪峰的頭條”。
更多縣委書記反映,一些網絡媒體對基層問題的報道不是引導型,而是放大型。有時為平息輿論,板子只能打在基層干部身上。
縣委書記責任大,事無巨細都要親自管,發展、穩定、民生、安全,“一個都不能少”。既要上級滿意,又要群眾滿意。“周六保證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證”成了縣委書記日常工作的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