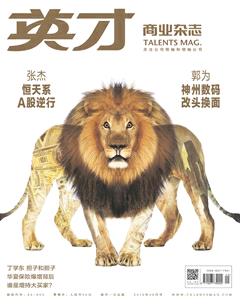朱海斌 保7還得看投資
張延陶++孟杰

盡管靠投資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廣受詬病,但是相較于消費與出口,投資的表現仍然是關乎經濟增長的命脈所在。
摩根大通首席中國經濟學家朱海斌近期接受了《英才》記者的專訪,他坦言:“投資是制約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因素,下半年能否實現全年保‘7就在于此。”
另外,股市的“異軍突起”無疑是上半年經濟運行當中的驚喜之處。然而股市是否能夠為實體經濟貢獻強有力的資金支持?朱海斌坦言現狀并不樂觀。
股市難撐實體經濟
《英才》:在上半年的經濟運行中,股市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朱海斌:今年上半年整個金融行業的增速超過17%,我們算一下其對整個GDP的貢獻,上半年大概是1.5個百分點,也就是20%。雖然金融業增長并不完全是股市,它還包含了銀行、保險業等。但股市對GDP的貢獻還是達到了0.5個百分點。
《英才》:目前股市對于實體經濟的貢獻如何?
朱海斌:政府一直強調金融要為實體經濟服務,股市也要為經濟實體運行。從上半年看,如果說股市對實體經濟有支持作用,最主要的體現來自于股市上行后,可以通過股市進行融資,更好地為實體經濟服務。但是從數據上看,上半年社會融資規模總額中,股市占比很低,大概3%左右。
因此,上半年股市對實體經濟起的支撐作用整體來看是有限的。但如果分行業來看,股市對一些新興行業的支持比較明顯。上半年,尤其在一些互聯網+、醫療、技術創新領域,股市還是提供了強有力的融資規模。
《英才》:股市財富效應下,消費與投資是否能得到提升?
朱海斌:這個邏輯并不成立。上半年股市火熱之際,消費并沒有特別明顯的變化。零售業的消費、汽車的消費反而是下滑了的。
從微觀個體來看,中國股市目前有9000多萬個賬號,但按人口比重來看,股民占比也就6%-7%。因此大部分股民都是中產階級或富人階層。對于這些家庭而言,基本消費是比較固定的,股市收入更多將致其整體財富增長,而非增加其基本消費的支出。
投資下滑是“禍首”
《英才》:目前拖累中國經濟增長的根本因素是什么?
朱海斌:二季度經濟數據公布后,很多海外投資者疑問為什么中國的GDP同比企穩,環比反彈,但是在很多指標上并看不到,包括像用電量,以及中國對于一些大宗商品的需求等,我認為這與中國經濟結構的變化有很大關系。
推動二季度經濟好轉的主要原因是服務業的加速。但是展望三、四季度,尤其7月股市大跌之后,我們也擔心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將受到抑制、甚至較上半年出現下滑。在這種情況下,投資能否穩住將一定程度上決定全年能否保“7”。
可以看到,二季度的經濟運行當中,制造業或者跟投資相關的一些指標并沒有明顯地好轉,反映到企業層面尤其是一些身處傳統行業的企業,其經營狀況普遍還是比較困難的,包括利潤率也在下滑。
因此,投資下滑是造成經濟減速的一個最主要原因。
《英才》:下半年制造業與房地產投資會否出現好轉?
朱海斌:傳統制造業、房地產行業投資增速的下滑屬于預期中的趨勢。產能過剩的現象仍然在持續,所以這一輪去產能并未結束,下半年制造業投資可能還是會往下走。
房地產行業仍然供大于求,從房地產投資的增速來看,我們判斷下半年仍然會往下走,全年可能是一個低的個位數增長,到明年有可能房地產投資會負增長。也就是說從房地產投資對經濟的影響來看,它仍然是一個負面因素。
《英才》:如何看待PPP模式在基礎設施投資中所帶來的影響?
朱海斌:目前政府最強調的一個問題就是發展基礎設施投資。但是我們看到二季度基建投資是非常低迷的,直到6月才有一個比較明顯的反彈,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地方政府沒錢。很多項目得到了批準,但是地方政府沒有30%的啟動資金,所以導致最終無法開工。
6月,財政政策進行了一些調整,比如允許地方政府債務的存量置換、以及43號文的局部性調整等。在短期內扭轉了地方政府缺錢的困難,伴隨著政策利好,預計三季度基建投資可能仍然會比較強。但從中期來看,地方政府的資金能否根本解決仍然是我們要直面的重要問題。
我們現在看到都是一些短期性的調整。政府層面也在推動PPP模式,但PPP模式的進展并不很順利,而且在實際操作中也存在著許多問題。因此我們認為,通過央行、政策性銀行推出一些定向的寬松政策給予支持,有可能是有效的解決途徑。
通縮待解
《英才》:當前是否面臨著較為嚴重的通縮?
朱海斌: 近期,CPI上升,PPI下降。我們判斷到年底,CPI大概能夠回升到2%左右,但整體來看,全年CPI肯定比政府既定3%的目標要低很多。
更大的問題是PPI連續41個月的通縮,而且最近的數據更是創下新低-5.4,因此經濟面臨著通縮的壓力。因為PPI直接對應的就是企業的實際融資成本,以及企業經營的利潤情況,所以這兩方面都是比較負面的。
如何降低企業實際融資成本仍是擺在央行面前的核心任務。首先,央行仍然有進一步降息的空間。另一方面,我們的存款準備金率仍然非常高,而且最近幾個季度外匯儲備和資本流動均出現了比較明顯的變化。因此無論對于貨幣還是信貸,進一步的降準同樣勢在必行,能夠緩沖資本流動以及外匯儲備的一些變化。
《英才》:貨幣政策的實施是否有效的為實體經濟注入了強勁動力?
朱海斌:傳統的貨幣政策:降息、降準,應該說效果還是有,但并不明顯,因為傳統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出現了一些問題。這也解釋了為何央行在去年前十個月中遲遲不降息降準。原因在于,目前整個經濟體制發生了變化,貨幣政策的傳導體系也受到影響。一些創新型貨幣政策工具的應用,尤其一些定向性的,將成為新的趨勢。
《英才》:貨幣政策應該如何創新?
朱海斌:今年的降息確實帶動了銀行整體平均利率的下滑。但整體來看,銀行的平均借貸利率的下調比基準利率下調要來的少,它不是1∶1的傳導;其次,受益于利率下行的主要是一些大的企業(包括大國企、大民企),也包括地方政府。但很多小微企業卻由于風險較大,實際利率出現升高。除了央行降息之外,其他一些配套的措施也應該跟上,這樣才能真正把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給降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