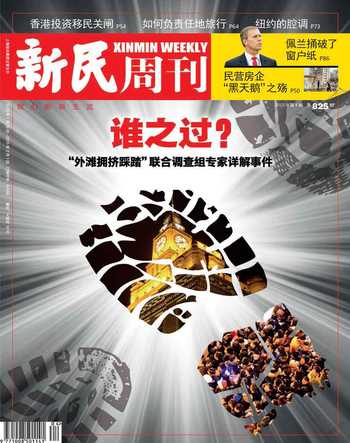世界上最好的館長
口述/雅克·里夏 整理/闕政






他1914年出生在土耳其,上世紀20年代因為希土戰爭隨法籍父母逃往巴黎。在那里,電影讓他著了魔。
1936年,他和朋友一起創建了世界上最著名的電影資料館:法國電影資料館。后來法國電影新浪潮的名將,都自稱是“電影資料館的孩子”。
1974年,他因為對電影事業的巨大貢獻,獲得奧斯卡終身成就獎。如今,巴黎還有一個廣場以他的名字命名。
他就是亨利·朗格盧瓦(Henri Langlois),被特呂弗譽為“世界上最好的館長”。
今年1月,19歲就開始擔任朗格盧瓦助手的法國著名導演雅克·里夏(Jacques Richard)受上海師大“人文·法國·電影學堂”和法國駐滬總領事館之邀來到上海,不僅帶來了他耗時7年拍攝的紀錄片《亨利·朗格盧瓦:電光魅影》、朗格盧瓦唯一導演作品《地鐵》、多部法國電影新浪潮代表作修復版,還帶來了塵封一個世紀的故事——電影資料館的前世今生,“朗格盧瓦事件”的始末,朗格盧瓦電影博物館火災的真相……
在中華藝術宮,雅克·里夏接受了《新民周刊》的專訪,聊起那個法國政府眼里的無政府主義者,那個呼朋喚友的少數派,那個孤獨的反叛者,那個膠片瘋子,那個永遠單純的少年……每一個,都是最真實的朗格盧瓦。
朗格盧瓦曾說:“熱愛電影,就是熱愛生活。”雖然他一生只拍了一部《地鐵》,但雅克·里夏說,當年電影資料館每天放5場電影,每年365天,“這就是永遠放不完的朗格盧瓦作品了。”
為了膠片什么都干得出
1936年剛成立的時候,電影資料館只收藏了10部電影,其實更像一個私人協會,它的前身是朗格盧瓦在1935年組織的“電影圈”俱樂部。
收藏、保護電影膠片不是件容易的事,有時候發行商打電話來問他:現在我手里有200個片子你要不要?如果要,就得馬上找卡車去救下來。那個時代很多電影商為了防盜版,電影上映以后就要銷毀膠片,有些導演就會把拷貝送到資料館保存。
朗格盧瓦自己為了收集好片子也是動足腦筋,甚至顯得瘋狂——他會去跳蚤市場,會問各種大收藏家買,也會借了不還。比如他很喜歡讓·維果(Jean Vigo),覺得他是默片向有聲電影過渡時代唯一一個能夠和諧處理畫面和聲音的導演,是個電影詩人。朗格盧瓦問別人借來維果的原創攝影劇本,沒還。人家問他要,他說不知道放哪兒去了,催急了就給對方送去一張廢紙,上面寫著:“維果不屬于你。”但是別人問他借《黃金時代》(L'age d'or,1930)的拷貝,他卻不肯,反問對方:“你去問盧浮宮借《蒙娜麗莎》看看,會借給你嗎?”
當時要收片子,還有一種辦法就是跟收藏家交換。有一次朗格盧瓦答應換給對方一部《匿名者》,后來又賴掉了,理由是“我們這里很多片子都是‘匿名’的,太難找了”。
到1944年的時候,電影資料館已經有了5萬部藏品,這還是經過了納粹的鐵蹄蹂躪。二戰的時候德軍占領巴黎,下令毀滅所有1937年前的電影拷貝。朗格盧瓦和他的工作人員帶著這么多拷貝東躲西藏,藏在朋友的城堡、花園里,一旦被抓到就會以同謀罪論處。他還聯絡了德國檔案館的人,讓對方通風報信給他一些高級機密,才得以躲過德軍突襲。有一部電影《藍天使》,膠片非常罕見,因為希特勒的納粹黨衛軍長官很喜歡女主角瑪琳·黛德麗,提出要拿《藍天使》跟朗格盧瓦交換一部有關馬其諾防線的紀錄片,朗格盧瓦在《藍天使》安全運到瑞士以后,給了對方一部和軍事無關的紀錄片交差。
戰后他的朋友很不理解,說你冒著這么大風險藏在我們家的片子,為什么名字叫“一個小男孩在公園散步”?其實朗格盧瓦是給很多電影改了一個看起來“無害”的名字,“男孩在公園散步”可能就是非常重要的《戰艦波將金號》,或者卓別林的《大獨裁者》。
即使后來電影資料館到了破產的邊緣,朗格盧瓦還是一有點錢就去買片子。有一次他和一個朋友去洛杉磯買片子,朋友問他回程也是一起走嗎?他說我已經把回程的機票賣掉了,反正領事館會把我遣返的。朗格盧瓦說過:“我不介意自己成為一個游民,但我想完善資料館。”
就像一個“電影大使館”
當然全世界有很多電影收藏家,也有許多保護膠片的人,但朗格盧瓦和他們最大的區別是:他不把膠片當文物,他要和大家分享這些經典影片。他成立資料館的動因也非常單純,因為他童年的時候看過很多電影,想把美好的時光保留下來。
朗格盧瓦本人受超現實主義繪畫藝術影響很深,他喜歡默片,喜歡驚世駭俗的視覺奇觀,把電影看得更像是造型藝術,并且覺得電影自打開始說話以后,臺詞和畫外音就把畫面殺死了。
所以他為電影資料館組織的主題影展,也和普通人很不相同——1963年的時候資料館的放映廳已經搬到了“夏悠宮”,一天放5部電影,天天如此。同一天里,朗格盧瓦選的5部電影可能看起來一點關系也沒有,但是在他眼里這幾部電影絕對有關,或者是一位導演對另一位有潛移默化的影響,或者是一位對另一位作了致敬……他在排片的同時就像在做電影評論一樣,蘊含了他的電影觀。
實際上,電影資料館不僅是膠片的庇護所,也是自由藝術家們的天堂。當年資料館的排片,在紐約也可以看到,有國際影響力。但是如果有年輕人拿著他們剛拍好的電影過來,朗格盧瓦就會把原定的希區柯克《精神病人》播映取消,改放他們的新作——你無法想象一個年輕畫家,這周才開始畫畫,下周作品就被掛到了盧浮宮,掛在畢加索的畫邊上。但是在資料館,這一切都是可能的,新導演和經典導演都被放在平等的位置上。所以資料館成了一個年輕電影人出人頭地的重要場所,朗格盧瓦就像是給小孩喂食的父親,你會看到后來的“法國電影新浪潮分子”都在那兒:侯麥、里維特、戈達爾、夏布洛爾、特呂弗……特呂弗說過,“我們都是電影資料館的孩子。”
我自己的第一部電影《否定之否定》,也是在電影資料館首映的,滿座,朗格盧瓦還親自為我介紹,說:“拍得很好,避免了最壞的情況。”當年我的想法也是拍片要顛覆,要驚世駭俗。如今帶著距離感再看,其實有點失敗。但朗格盧瓦很高興看到年輕導演走到攝影機后面,很高興他們可以成為既定規則的破壞者、顛覆者。他獨具慧眼的影展,讓很多日后非常著名的導演首次進入觀眾視野,比如英格瑪·伯格曼和黑澤明的作品首次歐洲公映,都是在電影資料館。
很長一段時間里,電影資料館既是電影人們在巴黎的小家,也是經常招待國際朋友的一個“電影大使館”。希區柯克把他的電影道具——《精神病人》里面那顆著名的骷髏頭,送給資料館收藏;美國導演尼古拉斯·雷病了,資料館會幫他付賬單;資料館窮得揭不開鍋的時候,敬重朗格盧瓦的藝術圈朋友會帶20公斤魚子醬過來開party……
最讓人懷念的還是當年資料館那種自由的放映氣氛:看電影允許抽煙,基本上沒有什么不允許的。有些人有他們的專座,有些固定只坐第一排或者第三排。放貓王的電影,底下會有脫衣舞女郎上臺熱舞,大家一起叫好……也有不叫好的,比如有一次放一部日本片,但是字幕只有捷克語,觀眾叫嚷起來,朗格盧瓦就說:“你們都是傻子嗎?看畫面不就好了,狗都看得懂!”還有一回放約翰·福特的《青山翠谷》,非常火爆,里面400個位子坐滿,外面還有400個人等著進場,但是一個老太太走出來,生氣地說要退票,理由是:“名字叫‘青山翠谷’,片子為什么是黑白的?”——各種奇葩的事兒都有,這就是電影資料館,一個非常生動的地方,一個大家生活的據點。
1968年的“五月風暴”
不過,有人爽,也有人不爽。朗格盧瓦讓很多人不爽——有些人想要取代他;國家又覺得他憑一個人的力量在做資料館,完全不受掌控。到了1968年,巴黎就爆發了“朗格盧瓦事件”。
當時法國文化部部長安德烈·馬爾羅(André Malraux)想要以“賬目混亂、管理不善”為由撤掉朗格盧瓦的職務,另派自己的助理出任電影資料館館長。得知這個消息,新浪潮的導演們都走上街頭抗議,很多國際知名導演發來電報或者信件,奧遜·威爾斯、卓別林……都說如果朗格盧瓦不能復職,就要把自己的片子拿回去。許多默片時代的大導演,他們的片子在本國已經不盛行了,被遺忘了幾十年,但朗格盧瓦仍然會在資料館組織影展,這都令他們非常感動,不遺余力地支持朗格盧瓦。
后來沖突進一步升級,成為聞名世界的巴黎“五月風暴”。越來越多的公民走上街頭,打出“去他媽的戴高樂黨文化部”、“不要電影警察”的條幅。連當年的戛納國際電影節也因此停辦。迫于輿論壓力,最后當局不得不撤回解雇令,恢復了朗格盧瓦的職務。
風波平息之后,特呂弗的《偷吻》在資料館首映,電影第一個鏡頭就是法國電影資料館,這是一個幸福的時刻——但很快法國政府就停止了給予資料館的資助。接著,資料館的工作人員從75個減少到了15個。很多學生不計報酬來做義工,做一些譬如檢票、運送膠片、寫信這樣的常規工作,幫助維持資料館的繼續運作。
1973年,我19歲,喜歡看電影,也很想當導演。當時覺得看電影挺貴的,就想:去資料館工作吧。那時候朗格盧瓦總要防著有間諜混進資料館,動他那些拷貝的心思,所以對我考驗了很久,才讓我做他的助手。他還對我說,你一年之后就不在這里了。我很擔心,但他的意思其實是覺得我很快就要去拍自己的電影了。
事實上正如他的預言,我在1975年就拍了自己的處女作。資料館對我來說就是最好的課堂——不光是能看各種各樣的電影,觀眾里還有很多本身就是從業人員。那時候我們總開玩笑說,如果你想拍個短片,只要去觀眾群里組織一下,就能組到整個劇組了。
朗格盧瓦本人更是令人嘆為觀止,他就像一部會走路的電影百科全書。他的辦公室也根本不像那些死板的公司,每天這里都有無數的事情上演,每天都像節日。圣誕節,會計師窮得只能在電影廳里辦公算賬,朗格盧瓦的老婆瑪麗卻拿著國王餅和香檳,呼朋喚友喊大家一起慶祝。
朗格盧瓦24小時都在跟人討論電影電影電影,電影就像他的宗教信仰。但他當然也有很多其他的愛好,喜歡欣賞美麗的女人,喜歡詩歌,也喜歡美麗的男人——我不是說他同性戀,他很神奇,喜歡跟年輕的男孩子躲在電影院的一個角落里,寫詩。他老婆看見了就非常不爽,要跟他發脾氣。有一次資料館開會,等朗格盧瓦等了一天他都沒來,后來他才說:“媽的!我老婆把我的褲子藏起來了!”
一方面他喜歡反叛者,喜歡有革命精神的年輕人,但是另一方面他又不是那種好為人師的人,他只是好像一直活在青春期里,你看他的眼神,很單純。他對日常生活充滿了很多詩意的想象。當你有這樣一個老板的時候,生活就會有很大的不同。
一群瘋子的作品
朗格盧瓦的妻子叫瑪麗·米爾森(Mary Meerson),她的哥哥也是個導演,朗格盧瓦曾經拯救過她哥哥的電影膠片,瑪麗因此對他感恩戴德,就像很多受到電影資料館恩澤的導演一樣,對朗格盧瓦有種“奴隸情結”,愿意為他做牛做馬。
我第一次見到朗格盧瓦的時候他已經很胖,胖得像條龍。他老婆更胖,一直弓著腰坐在那里,簡直像要折成兩半。樓下還有個工程師,自愿為資料館干活,穿著個白外套在那兒刷墻、修老舊的機器……整個感覺就像童話一樣。
朗格盧瓦和瑪麗都沒錢,也不領工資。有時候到了午夜,電影放映都結束了,他們會點一點當天的票錢,放進一個信封,帶著出去吃一頓大餐——這在一般企業看來簡直不可能。
我有時候沒錢了,去問朗格盧瓦要,他會從口袋里掏出一百法郎給我。過幾天又沒錢付電費了,再去找他老婆——他老婆頭發很長,又不喜歡洗澡,寧肯涂很多香水,耳朵不大好,敲門也聽不見,走到她面前篤篤篤敲桌子,大聲說:“找你有事!” 她才抬起頭來,也很大聲地說:“找我有事?借錢?不可能!電影資料館是沒有錢的!”我說要不我私人問你借吧?她說:“哦?私人?那又是另一回事了。”然后就從那個資料館的信封里掏出錢來給我……
但是你不要以為他們中飽私囊。瑪麗年輕的時候非常漂亮,畢加索、馬蒂斯都畫過她的肖像。后來資料館沒錢的時候,瑪麗就靠賣畫補貼,一張張全都賣了出去。朗格盧瓦也受邀去蒙特利爾大學教電影課,一個月去一次,薪酬不薄,都貼給了資料館。你想他年紀這么大,又很胖,每個月都要飛一次美國,再轉機到加拿大,實際上是很累,這也導致了他62歲就心肌梗死。
朗格盧瓦和瑪麗,其實是跟資料館不可割裂的兩個人,這就是我想說的。法國政府從行政角度無論如何也無法理解他們的所作所為——如果是國家博物館,肯定先要做預算,再撥款……但電影資料館是在沒有既定規則的情況下,一群瘋子做出來的這么一件作品,這也是它的復雜性所在,不能把它看作一個行政機構。
舉個例子來說,一位好萊塢著名演員過七十大壽,這在當年是個文化事件,資料館就把他請來法國,住五星級的“喬治五世”,送鮮花——但是如果你問朗格盧瓦要買花的發票,他十有八九是找不到的。
藝術家被官僚取代
每天都要找錢應付各種事務,終于把朗格盧瓦逼得筋疲力盡,他開始把重心轉向“朗格盧瓦電影博物館”——其實就在夏悠宮一個光線昏暗的地下室里。在那里朗格盧瓦設計了一個電影長廊,并不只是按歷史時間先后排列,而是像介紹繪畫一樣,演示各種不同類型電影在各個國家兼容并蓄的傳承和發展,各個國家的電影仿佛在他的陳列中達成了一種對話。
博物館里陳列著很多重要的展品,像是《飄》里斯嘉麗的裙子——但是朗格盧瓦并沒有在外面加上玻璃罩,也沒加任何注解文字,因為他覺得展品最重要是與觀眾交流,他希望觀眾去看,去摸,去發散自己的想象力,即使文盲也沒關系。
可惜的是,1977年7月22日,朗格盧瓦因為心臟病去世,年僅62歲。死的時候身無分文,公寓里沒有煤氣,也沒有電。
得知他的死訊,黑澤明、費里尼、希區柯克等導演都發來唁電。但是很快,政府官員就像老虎一樣撲了過來。他們把資料館不計報酬的義工們都驅逐了出去,正式接管了資料館,很快這里就充滿了學院派和公務員。這也是一個世界趨勢:藝術家被官僚取代。
在需要決定資料館何去何從的時候,很多著名電影人,像布列松、戈達爾,都希望繼承保護朗格盧瓦的理念,但管委會卻希望更現代化。這種爭論持續了好幾年時間,直到老電影人們老的老死的死,政府又一直想辦法讓更多的“自己人”混進管委會,終于改變了決定的走向:1991年,文化部委派了一個聽話的乖寶寶多米尼克·巴依尼(Dominique Paini)當館長,資料館也搬出了夏悠宮。
這之后的法國電影資料館,再也不能跟朗格盧瓦時代同日而語了。想當年,如果一部戲只有兩個人進場看,朗格盧瓦會說:“這兩個人就是未來的特呂弗、戈達爾。”現在呢?如果只有兩個人進場,工作人員恨不得把他們揪出去。現在資料館最常見的影展是阿莫多瓦、庫布里克、蒂姆·波頓、斯皮爾伯格……全都是世界知名的人物。但資料館的任務,應該是多發現年輕作者,或者已經被市場遺忘但仍然重要的老作者,而不是全世界本來就知曉的——那只是為了多賣票而已。
電影資料館應該是一個冒風險的地方,可惜附庸風雅的左岸知識分子們,他們只懂得欣賞1930年的驚世駭俗,不喜歡當代的驚世駭俗。
1997年那場奇怪的火災
1997年夏悠宮發生了一場火災,第二天我也到了現場,火災并不嚴重,消防水只是澆在屋頂上,博物館因為處于地下室,只有地面大約3厘米的積水,對藏品并沒有威脅。但是多米尼克以火災為借口,徹底收起了藏品,再也沒有按照原來的方式展出。
朗格盧瓦雖然在1968年時沒有失去館長職務,卻因此與不少人有了積怨。活著的時候已經令很多人不爽,有這次火災作為借口,他的博物館也銷聲匿跡了。
其實我很清楚,早在火災之前,朗格盧瓦電影博物館已經在一點一點地遭受破壞——有時候窗簾上積灰了,他們就會拿走,再也不掛上去。燈泡壞了,也不換。《天堂的孩子》的原始模型,改放了復制版。金屬支架不安全,撤了。好萊塢展廳不好看,也撤了。就這樣,博物館被微妙地損壞了,一點一點,完成了對朗格盧瓦的二次謀殺。
最可恥的是,后來拍過一部朗格盧瓦的生平紀錄片《公民朗格盧瓦》,制片人正是新館長多米尼克,那種感覺,就像殺人犯在致敬被害者一樣。
我不喜歡這部紀錄片,不只因為這個人,還因為他們故意人為地加了料——在拍攝朗格盧瓦保護膠片的場面時,故意加上了滴水的背景音,暗示他在一種不好的環境狀態下收藏膠片,但現實并不是這樣的。一邊贊美朗格盧瓦是先鋒,一邊暗示他保護得不好,新資料館才是更好的拯救者——這就是他們的邏輯。
如果你要了解拿破侖,應該去采訪跟拿破侖一起打仗的人。我拍《電光魅影》的時候采訪了100個人,都是和朗格盧瓦一起生活過的身邊人,大家庭的成員。我要站在更近的地方去看他,像素描一樣,一點點畫出他的頭發、眉毛,完整的形象……但是拍完了我才發現,自己和朗格盧瓦簡直越來越像,就像同時在畫自己的肖像畫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