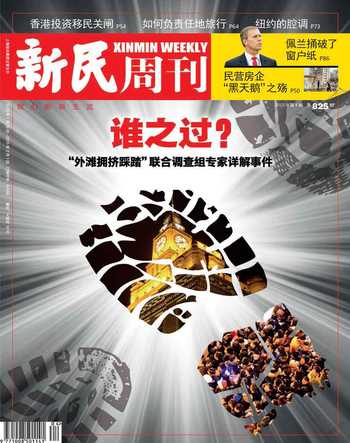震蕩政策市
沈洪溥

2015年1月19日,上海股市綜合指數暴跌7.7%,創7年最大單日跌幅,盤中最大跌幅逾8%;深證成指跌6.61%;金融股全部跌停,權重股近乎集體跌停;股指期貨主力合約跌停。誘因據說是受到政府部門的聯合打壓,具體而言,上周五,證監會通報券商融資類業務現場檢查情況,銀監會發布《商業銀行委托貸款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同時央行貨幣政策司官員又撰文稱要防止過度“放水”。
于是乎,這次的市場震蕩為我國股市是“政策市”的說法加上了新的注腳。“政策市”云者,當然是說我國股市對政策高度敏感。按照流行的說法,政府政策在股市中相當有影響,簡直達到了“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的地步。也正因為如此,每每股市跌得慘兮兮,一定有人高呼政府救市。這和普通人遇到危險時高喊娘啊、爹呀,本質上應該是一個意思。
不忙腹誹監管部門。從實證看,政策如今或許失去了想象中通天徹地的作用。
政府政策并不是助漲的主要依據。1999年6月15日的《人民日報》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明確指出當時股市“是恢復性上漲”,可之后市場稍一蹦跶后就開始連跌半年,又在2000年略折騰到2200點,一直萎靡到2005年的998點。而這輪上漲從1900點下方開始啟動,迄今指數漲幅超過70%,沒幾個人把原因說清楚,索性歸因于央行放水。但看中國人民銀行的貨幣供應量表,自去年6月份M2達到14%的高點以后,下半年整個M2始終平穩在120萬億左右,直到最后2個月才沖回122萬億。12%的全年貨幣增速在最近幾年不算高,對股指在四季度的拔地而起不具有足夠的解釋力。
另一方面,政策在止漲方面也并不總是立竿見影。如1996年,從當年一季度末開始市場暴漲,漲到7月底,管理層先后發布所謂“十二道”金牌,試圖為股市降溫,但調控措施并未能有效遏制市場的狂熱,在接下來的三個季度里,上證綜指上漲了124%,深圳成指暴漲了346%。市場一直漲到1997年中的1500點才稍息。而這個點位紀錄要到兩年后才被打破。
那么,既然政策并不是總靈驗,政府也并不是萬能,那為什么監管部門還總是擺脫不了股市下跌始作俑者的惡名呢?原因在于這個市場開始就沒立好規矩。政府抓住審批制不撒手,是上市公司質量低下的主要責任人,懲治壞公司不力,是“政策市”惡名的根本原因。
從中國股市建立那一天起,上市就要從監管部門拿“路條”。為了拿到上市資格,各省區一度還搞過分配額的游戲。上市如同分蛋糕,粉飾報表、掛牌不久就變臉的例子舉不勝舉。證監會一方面把控了審批權力,另一方面卻對迅速膨脹的上市公司質量承擔不了主要責任,幾個造假穿幫后影響較大的案例,也多數罰點錢了事,或者市場禁入了事。2600多家上市公司中,好公司寥寥,壞公司數不勝數。一次次的暴漲總要面對一次次的價值回歸,我國股市總也擺脫不了低水平重復的宿命,原因即在于此。
情況已經在改變。1月15日到16日召開的2015年全國證券期貨監管工作會議上,證監會肖鋼主席明示,要推進股票發行注冊制改革,引導長期資金入市,這是今年的主要任務之一。我們愿意相信,這次注冊制能夠真正落地。
同時,從經濟情境看,資本市場已經是提振經濟不可忽視的主戰場。當前,囿于準備金、存貸比等因素,銀行體系的信貸功能已經力有不逮,迫切需要啟動直接融資作為支持企業盤活存量、轉型升級的重要工具。想想看,如果中國股市從1849點漲50%,就對應著市值增加十幾萬億元,這里面,企業資本增加十萬億,融資能力會增強多少?再想想看,伴隨著投資者財產性收入增加幾萬億元,用于改善衣食住行,消費能力會增加多少。
這是支持股市上漲的戰略背景。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