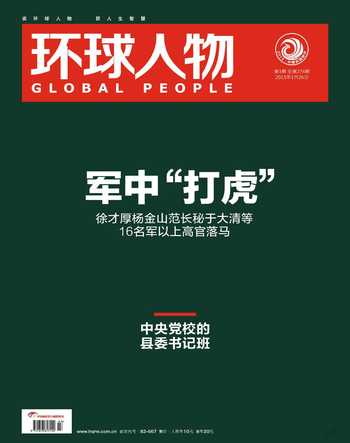用金融的邏輯思考生活
高小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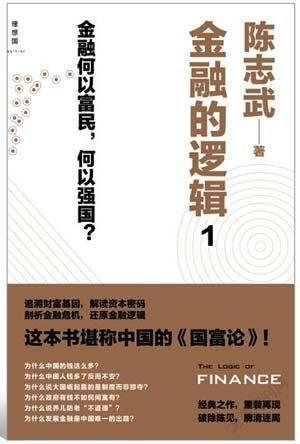
一般來(lái)說(shuō),經(jīng)濟(jì)學(xué)家的名氣主要局限在專業(yè)領(lǐng)域里,很少為普通百姓所知。但在中國(guó),一些經(jīng)濟(jì)學(xué)家就像明星一樣被人們津津樂(lè)道。比如吳敬璉、茅于軾、郎咸平……不過(guò),沒(méi)幾個(gè)人能說(shuō)出這些經(jīng)濟(jì)學(xué)家們的研究成果,他們只記得吳敬璉說(shuō)過(guò)“中國(guó)股市像一個(gè)賭場(chǎng)”,茅于軾說(shuō)過(guò)“經(jīng)濟(jì)適用房是最大的腐敗”,郎咸平說(shuō)過(guò)“我要當(dāng)財(cái)經(jīng)界的謝霆鋒”。在中國(guó),經(jīng)濟(jì)學(xué)家發(fā)表一篇高水準(zhǔn)的論文,遠(yuǎn)沒(méi)有在某論壇講幾句犀利的言論影響大。
陳志武也是一位明星經(jīng)濟(jì)學(xué)家,他也以敢言著稱,語(yǔ)錄有“目前中國(guó)股市還是一個(gè)基本為國(guó)有企業(yè)服務(wù)的市場(chǎng)”“最優(yōu)的國(guó)策是:少征稅,把錢留給老百姓去投資創(chuàng)業(yè),藏富于民”等等。人們?yōu)樗@些代表民意的言論拍手稱快,卻忽略了這位耶魯大學(xué)終身教授多年來(lái)在金融方面的學(xué)術(shù)研究。
2015年1月,陳志武的著作《金融的邏輯》修訂再版。它不以觸動(dòng)公眾敏感神經(jīng)為賣點(diǎn),而是在踏實(shí)地講述陳志武從1986年開(kāi)始與金融結(jié)緣后的一系列研究與思考。但《金融的邏輯》并不是一本專業(yè)著作,它仍在致力于向普羅大眾解釋金融的本質(zhì),教給大家如何將現(xiàn)代金融的思維方式融入生活。
從書的序言開(kāi)始,陳志武就一直在提醒讀者,中國(guó)許多根深蒂固的傳統(tǒng)文化觀念,與現(xiàn)代金融社會(huì)是相悖的。而中國(guó)金融市場(chǎng)發(fā)展的前提,就是改變這些觀念,讓人們用金融的邏輯思考和生活。
比如,“過(guò)去我們總認(rèn)為,國(guó)庫(kù)真金白銀越多的國(guó)家就越強(qiáng)大,要借錢花的國(guó)家是弱國(guó)。”陳志武用數(shù)字推翻了這個(gè)觀念:公元1600年左右,明末的中國(guó)國(guó)庫(kù)藏銀1250萬(wàn)兩、印度國(guó)庫(kù)藏金6200萬(wàn)塊、土耳其帝國(guó)藏金1600萬(wàn)塊、日本朝廷存金1030萬(wàn)塊。與之相對(duì),英國(guó)、法國(guó)等國(guó)則負(fù)債累累。而經(jīng)過(guò)400年的發(fā)展,當(dāng)年國(guó)庫(kù)藏金萬(wàn)貫的國(guó)家,除日本于19世紀(jì)后期通過(guò)明治維新而改變其命運(yùn)外,其它的到今天還都是發(fā)展中國(guó)家,而當(dāng)時(shí)負(fù)債累累的如今都是發(fā)達(dá)國(guó)家。“這一事實(shí)讓人們重新審視金融的功能和效用,之后才能真正接受金融的邏輯。”
還有一個(gè)例子更貼近生活:小王為了結(jié)婚要買房,但不想貸款。父母出了60萬(wàn)養(yǎng)老錢,姐姐拿出20萬(wàn)存款,小王再跟一個(gè)親戚借了10萬(wàn),湊夠了全款。這在中國(guó)很平常,但陳志武指出了問(wèn)題所在:第一,單純的血緣關(guān)系成了利益關(guān)系。第二,小王的父母只能靠?jī)号B(yǎng)老了。第三,小王以后可能同樣需要借錢給親戚或給自己孩子買房,形成惡性循環(huán)。在他看來(lái),這種建立在血緣基礎(chǔ)上的融資方式已不再適應(yīng)時(shí)代的需要,現(xiàn)代金融才是更有效的解決辦法。
雖說(shuō)不乏這樣生活化的例子,但總體看,《金融的邏輯》這本書的視角仍是宏觀的,金融危機(jī)、銀行國(guó)有化等都被囊括其中,從中也能看出陳志武這個(gè)湖南人的家國(guó)情懷。
2001年,中國(guó)股市出現(xiàn)震蕩,一路下跌。吳敬璉就在那時(shí)提出了“股市賭場(chǎng)說(shuō)”。其時(shí),39歲的陳志武正在耶魯任教,他也將目光轉(zhuǎn)向國(guó)內(nèi),開(kāi)始在雜志上寫專欄,介紹美國(guó)的證券法案、監(jiān)管規(guī)則等,論著陸續(xù)出版。他的觀點(diǎn)令人耳目一新,也引發(fā)不少爭(zhēng)論。對(duì)此,陳志武說(shuō):“我不是一個(gè)研究中國(guó)問(wèn)題的專家,這不是我的立足點(diǎn)。我更有興趣的,是人的發(fā)展歷程。金融讓我們得以自由,我想這是我未來(lái)思考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