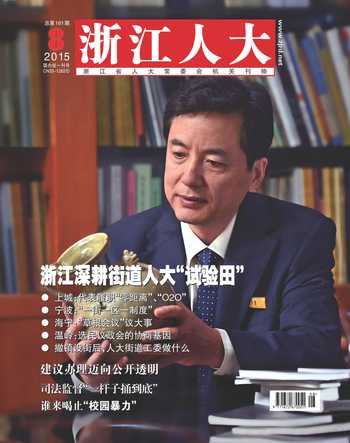誰來喝止“校園暴力”
何躍燕
“校園暴力”層出不窮
2015年6月21日,社交網絡曝出浙江省慶元縣多名初中生暴打一名小學生的視頻;同日,網曝四川省樂至縣一未成年女生被同齡人“扒衣拍裸照羞辱”;7月14日,江蘇省宿遷市泗洪縣又發生幾名初中生持木棍暴打一同學致其死亡事件。
辱罵毆打、強迫脫衣、持刀威脅、拍攝裸照,近年來“校園暴力”事件可謂層出不窮。
“慶元初中生暴打小學生”事件發生后,新浪大V、中央政法委宣教室副主任陳里第一時間在微博轉發了該視頻,并稱“這個視頻非同一般,希望當地公安機關、網絡運營商負起責任,給網友一個交待!”同時,他還專門設立一個微博話題“校園暴力舉報臺”。
法制網輿情監測中心統計顯示,2013年1月至2015年5月,有關校園暴力事件的公開報道量總體呈上升態勢。
馬娜娜在北京某培訓機構工作。據她回憶,她高中時代的同學分成兩撥,學習的學生是一個群體,不學習的學生往往著奇裝異服,聚在一起,經常打架。“他們依附于一些‘老大’式的人物,以年級為單位形成小群體。一旦群體里某人被欺負,其他人就會為‘兄弟’報仇。”
今年讀初中二年級的源源(化名),就遭遇到了“校園暴力”。有一次課間休息時,她趴在教室外的欄桿上看下面的同學玩耍,轉身時不小心撞到一個學校里“不好惹”的男生,引來對方的大吼大罵。源源做了一個無所謂的表情,被對方一下子抓住衣領,推到墻角打起來。
“當時我覺得無法理解,我跟這個同學沒有什么過節,只是一點小摩擦,對方就動起手來,而且我還是個女孩子。”后來她從其他同學那里得知,打她的男同學那天心情不好,借故發泄情緒。此后,源源走路說話都很小心,課間也不敢出來玩,生怕一不注意就惹到那些“不好惹”的同學。
2015年7月初,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通過民意中國網和問卷網,對1002人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73.3%的受訪者身邊曾經發生過校園暴力事件,43.7%的受訪者認為校園暴力的發生源于家庭不良的教養方式,50.9%受訪者建議加強家校聯系以杜絕校園暴力發生。
受訪者中,小學學歷的人占0.5%,初中學歷的人占3.1%,高中或中專學歷的人占13.6%,本科或大專學歷的人占75.6%,研究生學歷的人占7.2%。62.5%的受訪者表示自己中小學時代的學校存在“校園老大”式人物。
華東政法大學青少年犯罪研究所長期進行校園暴力的相關研究,副所長苗偉明表示,近年來校園暴力有越來越嚴重的趨勢,“數量增多,手段更為殘忍,帶有隨意性”。
懵懂少年何以頻頻施暴
有調查發現,“校園暴力”施暴者和受害者總是相對固定的,也就是說,每個學校或者班級有一些人總是被欺負,有一些人總是欺負別人。往往,欺負別人的人,許多都有來自家庭的原因。
“家庭教育缺失,導致孩子無法形成正確的價值觀。施暴兒童多是留守兒童、單親家庭兒童,他們從小缺少關愛和教育,是非觀較淡薄,容易形成‘有問題靠拳頭解決’的心理。”南京曉莊學院教師教育學院副院長袁宗金撰文分析說。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湛中樂認為,校園安全法制體系的缺失,導致校園暴力發生時受害者無法及時得到救助。“公安機關和校園治安管理部門缺乏有力銜接和聯動,導致力量薄弱的校園治安系統難以獨立防范眾多風險,公安機關‘遠水難救近火’。”湛中樂說。
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也指出,與校園安全相關的應急預案還不完善。“我們曾經承擔一個關于校園安全法律制度體系的課題,發現很多學校沒有健全的安全制度,即使有一些安全應急預案,也是擺在抽屜里,很少演練,缺乏操作性。”
“學校對校園暴力有無法推脫的責任。這絕不僅僅是管理不嚴、教育不力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它表明了當前的教育還沒徹底擺脫應試教育的陰影。”針對“校園暴力”滋生和蔓延,一些專家表達了上述意見。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認為,學生傷害案頻發與法律規則教育、生命教育和心理教育的缺失有關。
長期以來,學校過分強調考試分數,一再忽視對學生生命教育、德育教育和法治教育。有些學校,按規定設立的德育課、法治課“名存實亡”,這些課程常常被其他專業課擠占,成為可有可無的“雞肋”。
“學校教育的單一化嚴重偏離了教育規律,造成孩子德育知識和法律知識的匱乏。而對于一些可能影響學生身心健康的問題,一些學校也以簡單粗暴的方式處理。”熊丙奇表示,“學生在缺乏尊重的環境中成長,沒有形成生命尊嚴的意識,因此遇到挫折時,走極端的學生越來越多,動輒采取暴力方式處理同學間細微的矛盾。”
國務院關工委委員、中國少年兒童新聞出版總社首席教育專家、“知心姐姐”盧勤分析認為,“青春期暴力傾向的孩子因為內心的虛弱,心理的無力,所以在影視等作品中看到暴力會有印象,會模仿。他們覺得暴力是‘酷’、‘厲害’的表現”。

而當“校園暴力”遭遇“網絡暴力”時,暴力會被無限地放大,極易被未成年人效仿,導致孩子不自覺地拿起暴力武器,以期獲得存在感與成就感。以成人設計的網絡游戲為例,其中好多槍戰游戲,規則就是一切都靠暴力解決,誰的武器厲害,誰就是老大。
“在看到未成年人身上存在的問題時,不能忽視社會背景。”新華社的評論如此寫道:“留守兒童、獨生子女、貧富差距、分數崇拜,這樣的一些問題,生硬地出現在我們面前,也生硬地影響未成年人。換句話說,僅僅是教育問題,未必就會導致極致性的后果。但當教育問題疊加社會問題之后,也就無形中提升了惡劣事件發生的幾率。”
拿什么狠剎“校園暴力”之風
暢銷書《中國人的心理誤區》作者、石家莊心理醫院院長張彥平教授認為,“校園暴力”給青少年造成的危害,遠不止皮肉的創傷,更嚴重的是會造成孩子們心靈的扭曲。“如果任由這種勢頭發展,無疑會在青少年中造成一種不良的暗示:邪惡比正義更有力量,武力比智力更有價值。這是相當危險的。”張彥平說。
教育部政策法規司司長孫霄兵2015年1月8日在中國教師發展基金會校園安全專家研討會上透露,《校園安全條例》正在起草中,“校園安全需全社會重視,只有社會安全,學校才會安全。”
一些教育主管部門負責人表示,學校在為學生構建一道“安全墻”的同時,還應當加強對學生自我保護意識的教育,比如身體不讓能別人隨便觸碰、遠離陌生人等,危險襲來時學生能夠有警覺和防范意識,并且能夠懂得緊急情況下如何使自己受到的傷害最小。
陳里則認為,社會正能量的缺乏,加劇了“校園暴力”的發生。他在微博中呼吁:“年輕一代的健康成長不僅需要法律保障,更需要教育、文化藝術等方面長期的教育培養和熏陶。一個時期以來,社會生活中的一些暴力現象很多源于文化藝術暴力的教唆誘惑,整治文化藝術市場,清除文化暴力教唆誘惑,是一項迫切而又長期的任務”。
法律不彰,則道德不力。有評論指出,一些“校園暴力”事件令人發指,但依據我國現行的法律,學校多以嚴肅教育批評,責成家長嚴加管教作結。正是對施暴者處罰過輕,甚至免于處罰,這導致很多未成年人動輒對他人甚至自己的同伴施以暴力。
有專家指出,我國未成年人保護法對“校園暴力”的制約和打擊過于落后和偏輕。刑法對未成年人的刑事責任年齡劃分是14周歲以下完全不負刑事責任。現實的情況卻是,如今的孩子成熟比較早。“現在的孩子12、14歲什么都知道。”
“一直以來,我們把刑事責任的承擔看得過重,認為一旦承擔刑事責任就意味著對一個人的否定,有嚴重的后果。因此,我們一直傾向于認為懲罰并非應對犯罪的一種有效手段,14歲以下的兒童要以關愛為主。”
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法研究所研究員、人權研究中心副主任柳華文撰文指出,其實刑事責任就是對一個人行為負責任的方式。對于18歲以下的少年兒童來說,我們可以采取封存犯罪記錄的前科消滅制度,不讓被司法機關處于刑罰的孩子帶上污點生活,希望他可以改過自新。“因此,對待青少年可以有一些特殊的方式,但是責任還是要負的。”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少年兒童研究所所長、教授童小軍同樣認為,對未成年人,不能“一刀切,一味地保護”,因為的確有一些未成年人的行為太惡劣,超出了我們要好好保護的范疇。
柳華文說,如果14歲以前不負任何刑事責任,這對預防和懲罰未成年人實施的一些嚴重危害他人和社會的行為是不利的。柳華文建議,應加強相關的立法,包括在刑法上考慮刑事責任人的年齡的重新定義和細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刑事責任人的年齡,但是降低之后更要有一些配套規定,促使違法犯罪的青少年能夠金盆洗手,重歸社會。”柳華文說。
“對于校園暴力,這不僅僅是刑法的問題,也是一個社會法的問題。除了追究違法犯罪的刑事責任、民事責任和其他法律之外,還要考慮對受害人的保護。對于受害人來說,我們應該有一些制度上的安排,比如說必要時提供心理輔導幫助,促進其身心康復,讓他們能夠重新恢復正常的生活。”柳華文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