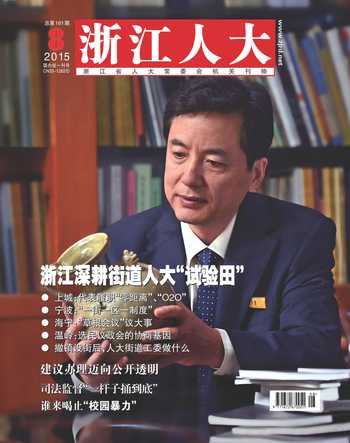“農(nóng)民偷拍官員獲罪”中的辯證法
郭文婧
農(nóng)民汪冬根和兒子汪金亮偷拍縣長收禮事件結(jié)果“出爐”。據(jù)7月19日《南方都市報》報道:法院認(rèn)定汪冬根構(gòu)成了敲詐勒索罪、詐騙罪、尋釁滋事罪,判處汪冬根有期徒刑六年,并處罰金一萬五千元。汪冬根當(dāng)庭表示不服判決,將堅持上訴,要求調(diào)查縣長陳虹中秋節(jié)收禮事件。汪金亮涉黑案正審理中,尚未判決。
偷拍者有罪,收禮縣長豈能無過?網(wǎng)友情緒很自然聚焦于此,這是可以理解的,更是需要重視的。但從法治的角度,法院只能審判已經(jīng)立案起訴的案件,被偷拍的官員是否應(yīng)該得到處理,甚至也被定罪,則應(yīng)另當(dāng)別論,將矛頭簡單指向法院顯然是不妥的。至于法院判決,是嚴(yán)格依據(jù)法律確保了公正,還是或明或暗地偏向官員與政府,既然汪冬根堅持上訴,我們相信法律最后自有公斷。然而,在民權(quán)得到保障、高舉反腐旗幟的當(dāng)下,此事中的“辯證法”顯然是值得琢磨的。
監(jiān)督官員和政府是每一個公民的合法權(quán)利,偷拍只是監(jiān)督的手段之一,本身并無原罪,關(guān)鍵是要看偷拍行為本身是否侵害了他人的合法權(quán)益,是否違反了法律禁止性規(guī)定,更要看偷拍所得的證據(jù)如何使用。既然出于監(jiān)督官員和政府的目的,偷拍所得的證據(jù)就不能“自用”,而是應(yīng)該交給紀(jì)檢監(jiān)督部門,或者交給新聞媒體以行輿論監(jiān)督之實。如果用來“自用”,無論是否向他人索要報酬,是否自己從中受益,至少就具有了犯罪的主觀要件。
對官員來說,公權(quán)非私權(quán),行使的基本要求就是為公。官員因為有了把柄在別人手里,“怕自己政治上受到影響”,不得不褻瀆公權(quán),這根本就無關(guān)威脅和恐嚇,而是涉嫌徇私枉法,是瀆職犯罪。官員在行使公權(quán)的時候遇到所謂的“敲詐、威脅和恐嚇”,除了報警不應(yīng)該有其他任何私意妄行。
從實體公正的角度,民與官之間的事情,特別是涉及到公權(quán)行使的問題,本身既是對當(dāng)事人的一個交代,更是對公眾的一個交代。那么,無論是公安的偵查,還是組織的調(diào)查,甚至是結(jié)論的出籠,至少都應(yīng)該并行。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為如果不同時對官員進行,就有發(fā)生權(quán)力干擾司法的可能,從而影響司法公正;另一方面,公眾的情緒不容易得到平慰,從而傷害黨和政府的公信力。而在汪冬根偷拍官員的事件中,問題正是出在農(nóng)民已經(jīng)定罪、官員仍然在位。

官員特殊的身份,決定了需要被動監(jiān)督,更需要主動監(jiān)督。站在監(jiān)督部門的立場,任何線索都不應(yīng)該放過。每次線索的厘清與排除,都應(yīng)該是一次對官員進行放大鏡下的檢驗。汪冬根偷拍縣長收禮,視頻里涉及8起,紀(jì)檢部門顯然就不應(yīng)該只就這8起說事兒,畢竟這只是中秋節(jié)一天拍下的。不厘清整體的真實狀況,顯然難以服眾,因為公眾是善于聯(lián)想、善于“舉一反三”推斷的。
農(nóng)民偷拍官員獲罪,對政府和官員來說,是一次公共危機事件的另一次“發(fā)酵”。危機,危險中有機遇,是釀成對官員和政府公信力的再次傷害,還是借此喚回人心與信任,關(guān)鍵就在于能否辯證地看待和處理。無疑,事件本身需要徹底厘清,其中的“辯證法”更值得好好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