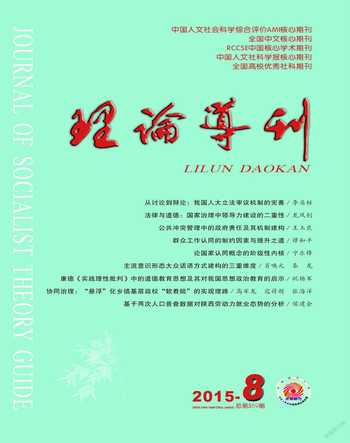法律與道德:國家治理中領導力建設的二重性
龍鳳釗
摘要: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強調指出,國家和社會治理必須堅持法治與德治相結合的原則。就公共部門的領導力建設而言,作為影響力的領導力包括權力性和非權力性兩個方面,表現為領導行為的拘束力和感召力兩種,它們分別來自公共組織的“法”和領導者的“德”,從內外共同規范領導者的領導行為,并制約領導權威的建立和領導績效的提升。為此,需要正確把握領導力建設在制度形態、作用機制、權威類型、具體方法等各個方面的二重性問題,適當區分和平衡它們的關系既是領導科學,也是領導藝術。
關鍵詞:國家治理;領導力;法律與道德;二重性;領導績效
中圖分類號:D920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7408(2015)08-0008-05
2014年3月,習近平在第十二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安徽代表團參加審議時,談及推進干部思想作風建設,提出“既嚴以修身、嚴以用權、嚴以律己,又謀事要實、創業要實、做人要實”的重要論述,即,“三嚴三實”。2015年4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關于在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中開展“三嚴三實”專題教育方案》,對2015年在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中開展“三嚴三實”專題教育作出安排。從公共管理角度,這可以視為領導干部領導力建設的重要舉措。要解決“不嚴不實”問題,需要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通過注重道德規范的作用來提高領導力,建立法律和道德相統一的激勵約束機制。
一、問題的提出
1為什么要突出領導力建設?之所以要在國家治理中突出領導力建設的問題,是因為治理理論面對的中國歷史境遇的特殊性。治理,作為一種新的管理范式,在西方原本是指“公共治理”(Public Governance),有“去國家化”之意。在我國,由于民族國家“現代性”歷程之首要任務是“救國救民”和“民族復興”的集體性使命,強調“國家”在治理中的主體性。即使如此,“國家”也只是公共領域中的一個部分,是特別強調領導與服從的權力分配的部分。因此,“國家治理”是公共治理的種概念,需要用公共治理結合各個國家的特殊情況來把握。在中國,特殊情況就是政黨的啟蒙與領導。因為面對“一盤散沙”的中國社會,必須有一部分“先進的中國人”作為“先知先覺”者(孫中山語),通過“以黨治國”的路徑和體制來領導人民。
然而中國國民黨并沒有實現中華民族的獨立自強,只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才最終實現“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從舊民主主義革命到新民主主義革命,再到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中國經驗表明,國家治理需要一個作為領導集團的政黨,而該政黨的領導力與先進性又至關重要。歷史地看,領導力理論也可以對蘇聯的革命和建設歷史做參照性的解釋:在蘇俄革命中,列寧探索出在落后國家中實現社會主義革命,必須要有一支具有強大領導力的政黨來克服群眾的分散與落后的特點;而到后面的建設時期,由于蘇共領導力與先進性的削弱,導致了國家的解體。當今中國,我們提出“兩個一百年”的“中國夢”,又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沒有一個強大領導力的執政黨及其干部隊伍是不行的。在此歷史邏輯下,中國的國家治理中執政黨的領導力建設就顯得尤為重要。問題是,這種“加強領導”如何通過個體的領導力建設來實現?這需要從個體行為的法律與道德約束來回答。
2如何把握法律與道德的關系?在國家治理視野中,如何處理領導力建設中法律與道德的關系問題,要從領導力的法權屬性來分析。本文認為公共部門的領導力本質上是一種“公權力”,作為“權力”(power)與私人部門管理者的權利(right)有本質區別。換言之,領導力建設本質上是公權力的規范性問題。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從我國對“法治”與“德治”關系的認識發展歷程說起。1978年12月,鄧小平明確提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建設。”[1]他的一系列法制思想,發展成為我國“依法治國”方略。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人們發現只強調法制是不行的,道德失范問題不僅表現在領導干部身上,也出現在社會的各個領域。任何一個社會都不可能只是純粹的法律之治。同時,隨著經濟發展和民族自信力提高,人們嘗試從傳統儒家的國家治理典籍中尋找“本土資源”。[2]到2001年1月,江澤民在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第一次明確提出了“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緊密結合起來”。[3]
但是,“德治”的提出卻遭到學界一些同志的反對,尤其是法學界很多人將其視為與法治對立的治理模式,[4]在政治實踐中也未能與法治并駕齊驅,司法實踐中更是法條主義盛行。這主要是因為人們將“德治”視為“人治”的變體,把“德”理解為領導者的個人品德,而不是作為社會規范的道德。實際上,法律規范與道德規范之間也并不涇渭分明,而是互動互補,你我難分。法律的道德化和道德的法律化是永不停歇的過程。20世紀中期,純粹法學派的哈特(HLAHart)和自然法學派的富勒(LLFuller)關于法律與道德的“世紀之爭”也最終無果而終。顯然,狹隘的法治觀念無法容納德治的存在和發展——既難以延續傳統治理方式,也無法嫁接西方治理理論。
要想統一法治與德治的關系,還須有新的政治理論框架才行。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隨之,2014年10月,十八屆四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 “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國家和社會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發揮作用。必須堅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中華傳統美德,培育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道德,既重視發揮法律的規范作用,又重視發揮道德的教化作用,以法治體現道德理念、強化法律對道德建設的促進作用,以道德滋養法治精神、強化道德對法治文化的支撐作用,實現法律和道德相輔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二、領導力的兩種制度形態①
1法律:作為正式制度。領導力作為一種公共權力,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屬于“必要的惡”。受法律制約的領導力才是強大和可持續的,否則無論對領導者個人還是公共組織來說都是危險的。任何公共組織既要提升領導者領導力,也要防止其腐敗。孟德斯鳩指出,“一切有權力的人都愛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變的經驗……權力不受約束必然產生腐敗。”[5]公權力要“關在制度的籠子”然后“戴著鐐銬跳舞”。但是目前,管理學界關于領導力的研究基本都是圍繞如何提升領導力展開的。
在管理實踐中,唯有公共組織的法律規范健全,領導力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生成和發揮。無秩序的組織將趨向解體,一片混亂之中根本無法實施領導。所以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指出:要“發揮法治在解決道德領域突出問題中的作用。”由于領導力是一個抽象概念和內在權能,法律并不能直接作用于它本身,只能通過規制領導行為來約束領導者及其領導力。因為法律只調整人的外在行為與人際間的交互關系,而不涉及到人的內心活動與主觀思想,也不能針對具體的個人。馬克思就曾說:“對于法律來說,除了我的行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調整的對象。”[6]以法律行為理論解釋領導者的職權行為,才能抓住它的法權本質,并為評估領導績效提供可以具體操作的方法。
一般來說,越是規范化、法治化的公共組織中,領導行為的法律效力或法律屬性就越加明顯。對于政府部門和事業單位(法律授權或者政府委托),任何具有法律效力的領導行為(包括外部行政行為和內部行政行為)都必須遵循法律上的合法行政原則和合理行政原則。裁量行為必須限定在合理范圍之內,決策行為必須講究誠信,并有適當法律依據和正當理由,在必要時候還需作出說明或聽證,否則即為違法或恣意。而前提是通過法律對領導行為的條件、方式、期限、對象和效力等作出規范。實際上,在法治社會中不懂法、不信法已成為某些領導干部的軟肋。不僅如此,對領導力的規制,行政法本身也有缺陷。傳統的行政法對公權力的規范只及于職權部分,實行“職權法定”原則。但是職權之外附著、派生的公共影響力卻缺乏有效規制的辦法。況且,職權與非職權影響力在領導者的領導力中往往也是難以界定的。
2道德:作為非正式制度。領導力是一種公權力,但卻是一種個人化的公權力,而不是抽象的職權本身。領導是“一種基于信任、義務、承諾、情感以及對善的共同觀念而產生的人與人之間復雜的道德關系。”[7]所以,領導不同于管理,不能等同于簡單的規則之治,僅從職權法定原則不能解釋領導力的全部內容。因為人們服從的不僅僅是具有強制力的法律,還包括具有感召力的人格力量。與僵硬的法律相比,道德與領導力具有高度的相關性。“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離婁上》)“治國理政,不但需要法律與制度的建設,更加需要執政者道德素養的提升。”[8]
與遵守法律義務一樣,道德規范也使主體具有某種道德義務。道德“以人們的自我評價和他人評價的方式為特點調整人們的內心意愿和行為,它是靠社會輿論、社會習俗和人們的內心信念來保證實行的”。[9]領導行為的內部規范,更多的需要領導者的自省與自覺,但又不完全依賴自律機制,也可通過輿論、評價、反饋和回應等方式對行為者作出“道德強制”或“道德壓迫”,同樣具有某種程度的強制。其區別于法律規范在于,道德規范的功能機制沒有那么迅速和強硬,也沒有專門的機關和人員來保證實施,其依賴非正式的方式實現。因為“領導者可以將權力用于好的目的或壞的目的,而且,領導者的個人價值觀和道德準則可能是決定其如何運用各種權力來源的最重要因素。”[10]98所以將道德上“自我約束”完全視為個人事務,既不符合公共管理的需要,也不符合倫理學的原理。
社會輿論對領導者的道德評價構成他的威信,對于領導者來說是一種無形的影響力,又反過來約束他的行為,甚至成為他的一種“負擔”,但領導者又總是極力追求這種威信。道德的這種內在約束機制,是一種自主性的軟約束,看似柔性,實則有力,恰有“作繭自縛”的妙處。這類似法官在實踐中積累起來的個人威信是司法權威的一個重要構成部分,但這一威信既非常崇高,又非常脆弱。一旦有道德上的污點,不但職位不保,個人的威信和榮譽也會喪失殆盡。這種不成文的法官職業道德規范具有遠遠超出法律規范的約束力。實際上英美國家歷史上極少有法官因品行不撿而去職。同樣,我國傳統社會中的鄉紳、士人,多因品行、學問和地位建立個人權威,使之成為鄉土中國的非正式領導者,與之相應所形成的道德約束力也非常強大有效。無論是法官的職業道德,還是鄉紳的倫理道德,以及本文所述公共組織的領導者的道德,都形成了一種強大的“道德制度”(morality)。對此,美國法學家羅斯科·龐德(Roscoe Pound)認為,“通常意義上的道德規范是指由個人組成的群體的習慣或風俗所支持的行為標準。基督徒的道德規范就是與基督教教義一致并被基督教所贊許的行為。儒家的道德規范就是儒家思想所推崇的行為。從這個方面來說,‘道德規范不是一種觀念而是一個實在的體系’。……它無須被社會壓力具體地加以支持或實施。”[11]需要強調的是,道德不同于品德。道德是社會規范,而品德是個人素質。
三、領導力的兩種生成機制
1領導力形成:法定與形成。法律與道德之所以構成領導力的兩個基礎,是因為其實質上是領導力形成與發揮的主要依據并具有規范和約束的作用——通過法律授權成為正式領導者,或者在實踐中因“德高望重”的威信而成為非正式領導者——兩種形成方式:“法定”的或“形成”的。前者已經成為一個法律原則:職權法定原則,在正式組織中實行“無法律無行政”原則,領導行為本質上是執法行為,所以政府部門是執法機關。在非正式組織中,道德所形成的權威也能成為支持領導行為的依據,并受之約束。法律與道德都為領導者采取領導行為提供“合法性”,而不論這種合法性是正式授權的還是自然形成。
關于“法定”。本文所用“法律”是廣義的“法”(law),而非狹義的“法律”(legal),指在公共組織管理活動中具有規范功能的所有規則、制度。凡是“大多數政治優勢者所確立的法律,或者,大多數我們徑直而嚴格地使用‘法’一詞所指稱的規則,是普遍地強制約束政治社會成員的,或普遍地強制約束一類行為主體的”[12]規范。它有兩個特點:一是普遍性的要求或禁止某一類行為;二是對所有組織成員具有強制性效力。這兩個規定性區別于領導者的個別的“命令”。
關于“形成”。它強調的是自然積累的生長過程,更多是指因道德、才能等非正式過程而具有的影響力。比如,某人可以因為上級的任命而擔任主任、處長、所長等職務而成為了領導者。但這并不是一個領導力的形成過程,該領導要具有真正穩固的領導力,還需通過道德、才能的證明來慢慢“形成”。在任何社會,“我們都希望所有的領導是誠實、高尚、真實、公平、有道德感的……”[13]無論何時何地,選拔和接受一個領導者都有一定道德最低限度。簡言之,職權可以“取得”,但是領導力只能“形成”,在此過程中,道德感至關重要,關系到領導力的正當性和有效性。
2領導力發揮:拘束力與感召力。將領導力的核心界定為影響力,已是公共管理學通識。但是反過來不能簡單的說影響力是領導力。“從權力等于影響力這個角度上說,不僅領導具有權力,一般的人也具有。只要一個人(或人群)對其他的人(或人群)具有不同的征服力、感召力,他的身上就具有了權力。”[14]影響力是一個非常寬泛的概念,還包括其他含義和用法。比如文藝作品、影視明星的影響力等等。在邏輯上,用外延更廣的“影響力”來定義“領導力”,盡管通俗易懂,但并不準確。本文認為,可從領導力的行為效力、作用機制來理解和劃分為——拘束力和感召力——即剛性領導力和柔性領導力。前者是因職權而獲得的領導力,以法律為基礎;后者是因威信而形成的領導力,以道德為基礎。
拘束力,是領導者可以約束、強制被領導者的管理行為。領導力既然是“力”,即有強迫、壓制之意,具備不以他人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強制作用。在管理活動中,因為分工而有領導者與被領導者,并以領導行為來聯系,這種互動具有一定的法律屬性。因為“法律是人們用以調整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行為規范,它反映一定的社會關系……”[15]98所有的社會關系都是或可以轉化為法律關系或者法權關系,并以權利和義務來調節領導者與被領導者之間的這種單向或雙向的影響與被影響關系。脫離法律來理解領導力,往往會陷入經驗主義的泥沼而不能自拔。“法律效力作為法內在的一種‘力’,此種‘力’是從何而來的?這就涉及法律效力的來源問題”。[15]153
感召力,表現為“魅力”(柔性)和“威信”(剛性)兩種,是領導者在實踐中依個人道德、才能、經驗等個體性因素建立起來的領導力。儒家經典《論語》指出,“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要達到這種效果,就離不開感召力的作用。作為非正式領導力,它是非權力性影響力,因而具有個人差異性,相對缺乏穩定的可預期性。沒有感召力的執法行為并不能稱之為“領導”,更難以成為領袖。領導作為一門藝術就在于它的感召力塑造。領導力建設強調領導者個人的才能與道德的感召力,關注公共組織的目標、愿景。所以,2008年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麥凱恩說,美國“并不需要一個管理者,而是一個領導者。”我國學者也提出,“領導不同于管理,也不同于統治與支配。領導在道德維度上的展開,證明領導包含著超越個人利益的道德關懷和正義訴求。”[16]
四、領導力的兩種權威類型
1職權與威信的區別與結合。領導對應的是服從。根據服從形成的基礎,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區分了三種權威類型:傳統型權威、魅力型權威和法理型權威。其中,魅力型(charismatic)權威,來自個人非凡品質,即本文所說的道德范疇;法理型(legalrational)權威則來自法律的規定,其建立在一套非人格化的規則基礎上。領導力建設應當在法理型權威基礎之上,增強魅力型權威。
沒有法律授權的人也可能因個人才能和道德而樹立一定的權威,自然地成為實際上的領導者;反之,一個有法定職權的人,也可能因道德低下而制約職權的正常發揮。權力(power)與威信(authority)既有聯系,又有區別。“這里所說的權威,是指把別人的意志強加于我們;另一方面,權威又是以服從為前提的。”[17]但是,服從可以建立在不同的基礎之上,有懾于強制、處罰的服從,也有發自內心崇敬和支持的服從。人們對權力的遵守有被迫的成分,但對威信的服從則屬于認同和擁護。
領導權威還與公共組織的發展階段與特點有關,越正式的組織越依賴法定職權所形成的權威。在組織結構簡單,人數較少的情況下,依靠領導者的個人領導力(才能與道德)就足以管理,這種組織的制度建設較為原始甚至沒有成文的規則。當組織發展到較為復雜而龐大,人數超過個人經驗范圍,無論是個體的領導還是集體的領導都無法準確有效駕馭時,就必須通過制度建設來組織和管理。這時候特定的職位和職權就產生了。公共組織的發展總體上呈現出制度化、法律化的趨勢,現代國家就是具有最高權威、最制度化的公共組織。
2注重領導權威的道德力量。
在英語術語中,甚至將“leadership”區分為“followership”和“headship”,前者為魅力型領導,它的下屬是“follwer”(追隨者),后者為強制型領導,它的下屬是“obedient person”(服從者)。強制型領導由職權而產生,但魅力型領導是因其在承擔領導職能之后的表現而逐漸獲得的影響力,并非一次完成也不能盡止。職權是有限的,但是影響力卻可能無限。因此,現代企業和公共組織更加注重人性化的管理,弱化強制性命令的同時增強激勵性的領導,僅靠法律規則的規范既難以實現人性化、個性化的管理目標,也增加了管理的成本和風險。
領導力需要建設,道德權威需要經營。那種認為身居要位就自有權威的想法是錯誤的。“僅依靠硬權力,很難使人信服。領導用以征服人,獲得影響力的因素常常還有他的道德和恩澤。只會發號施令的領導不是好領導,領導權力不等于領導的威信。”[10]81馬克斯·韋伯認為,領導的合法性也可以依賴于“對某個人以及他所揭示或規定的某規范或秩序(個人魅力權威的表現形式)所具有的特殊神圣性、英雄主義或非凡個人品質的效忠”。[18]所以,科林斯、馬可夫斯基認為“一個人要成為卡里斯瑪型的人物,就必須具有某些超常的品質,這類品質可以通過表演和社交虛構出來,但是,一個卡里斯瑪的領袖所進入的是一個充滿壓力的舞臺,他或她的表演必須達到角色的要求,否則就會湮沒消失”。[19]關于這個,羅伯特·霍斯(Robert House)提出了“1976年魅力型領導”(harismatic leadership)理論;美國管理學家切斯特·巴納德(Chester I Barnard)提出了“權威接受論”(the acceptance theory of authority),[20]認為領導者的權威不是來自上級或組織的授予,而是來自下級的認可。這些理論都在說明人格魅力之于領導權威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個人的道德行為還影響集體的道德權威和合法性。在信息化時代,領導者言行在輿論的道德評判中放大和歸結為(無論良好還是卑劣)執政黨的整體道德形象。這是對領導干部進行道德教育和規制的重要理由。

關于這一點,萊尼克(Lennick)和基爾(Kiel)強調,出色的道德技能不僅是個人領導力的核心元素,而且更是一種管理優勢。道德性弱智(moral stupidity)會使組織蒙受重大損失。因此,與智商、情商相比,“德商”(MQ,Moral Intelligence Quotient)才是管理成功的核心。所以德商可定義為:決定如何將普適的人類原則運用到我們的價值觀、目標和行動中的能力。[21]現實中,無論是企業管理還是公共管理,因領導者道德行為失當而導致的失敗比比皆是。對于執政黨來說,加強“官德”建設無論對組織還是領導者個人都是極為重要的。
五、領導力的評估和提升方法
1領導力的評估方法。領導力的評估和提升涉及到領導績效的概念。領導績效,或領導工作績效,是指領導者在公共管理活動中,發揮領導力,采取領導行為進行管理的績效,領導績效直接表明領導力的高低及其效率。影響領導績效的因素有很多種,本文從領導行為規范的角度,只考察法律與道德兩種。法律和道德設為自變量,領導績效為因變量,法律和道德與領導績效是正相關的關系。假定,所有公共組織都建立在一定法律規范基礎之上,非正式組織也有不成文的法律規范,完全沒有規范的組織不存在或將解散。同時,社會存在一般的道德水平,領導者總是建立在一定道德素養之上,完全沒有道德的人不能成為領導者或者將喪失領導者地位。一般的,越是正式的組織,其領導力的法定性越強,守法維度的值更大,可稱之為“法律值”;反之,在非正式組織中,非正式權力的影響越大,越依賴道德的維度,可稱之為“道德值”。組織的法律屬性與正式權力呈正相關關系,與非正式權力呈負相關關系。
如上所述,法律值與道德值在公共管理中不存在負值,最低為零,領導績效為二者的乘積。以法律為橫軸,以道德為縱軸,可建立一個法律值與道德值的領導績效坐標圖。如圖1:
設:
X=法律,Y=道德,Z=領導績效。
則:z=x·y,(x≥0,y≥0)
如果:x2>x1, y2>y1
那么:z2> z1
圖中,設n為正式組織的法律最低值,設m為普通領導者的道德均值。
圖1領導力的大小比較
如圖所示,由于y1 2領導力的提升方法。在公共組織的管理實踐中,不僅要評比兩個領導者或者同一個領導在不同組織與時間點的領導績效大小,而且還要進一步研究如何提高。也就是說,對領導績效的研究,必須注意從靜態的比較到動態的發展。法律與道德這兩個自變量的任何變化,都可能導致因變量領導績效的變化。道德值變動情況包括:公共組織領導者的更換(換人)或領導者道德的變化(提高或降低)兩種;法律值變動包括法制狀況的進步或倒退。 在圖2中,假設某領導者領導力為點a1(x1,y1),如果分別取值為x1=1,y1=3,則領導績效為a1=3。另一領導者領導力為點b1(x2,y2),如果分別取值為x2=3,y2=1,領導績效b1=3,此時兩者的領導績效相等。推論可知,如下圖所示,在曲線L1之上,任意兩點的領導績效相等,這一條曲線可稱之為“等績效曲線”(無差異曲線的運用)。該曲線上的任意兩點,領導績效是相等的,欲提升績效,只能從L1向L2方向移動。反之,則績效降低。 [JP+1]如上所述,圖2也指出了提升領導績效的方法:或增加法律值,或提高道德值。第一種方法,如在領導者及其道德水平不變的情況下,需要加強組織的法律建設,讓管理活動走向規范化、制度化,健全規章制度,加強執行力度,使得組織生活更加法治化。這提示公共管理的制度建設對于提高領導績效的重要性。第二種方法,如在既定的公共組織內,法制狀況不變,要提高領導績效,就需要提高領導者的道德值。具體來說,一是更換道德更高的領導者;二是使現任領導者的道德經過學習得以提高。對組織而言,需要注重提高領導者的道德素質,選拔道德水準更高的人擔任領導職位;對于領導者個人而言,為了不被淘汰和提高領導力,需要不斷提高自身道德素養。 [TP8Q7.TIF,BP#][TS(][JZ]圖2領導績效的提升 由圖2也可看到,單方面的提高法律值或道德值,都不能使得領導績效進入第1區(領導績效最佳區位),只有進入第1區的領導績效才是兩方面都高于普通水平的領導績效。如果法律值或道德值減低,則可能導致領導績效回到第2、4區之中;如果二者都降低到普通水平之下,則領導績效落入第3區(領導績效最差區位);如果法律值與道德值中任何一項為零,則領導績效為零,即無績效。法律值為零,表明組織不存在或解散,因此不存在領導績效;道德值為零,表明因領導者無道德而完全喪失領導力,導致績效為零。 六、結語:做守法、尚德的領導者 回到前文的議題,“三嚴三實”要在國家治理的框架中來理解,對于法治與德治作為不同層面的治理方式,其間的爭論主要是理解的誤差。“治國”是一種公共性的活動。“法治”是“依法治國”的簡稱,所謂“依”指作為普遍的、客觀的原則和準則,關鍵在守法。“德治”是“以德治國”的簡稱,所謂“以”,為“用以”的含義,是個體性、主觀性的范疇,關鍵在尚德。這不是文字游戲的狡辯,而是國家治理的主體、規則、方式和目標多元化的特點。依法治國是法律的統治(rule of law),治國理政的一切行為必須以法律為準則,實行依憲執政,依法行政;以德治國是道德的教化,講求在治國理政中倡導個人的道德自覺,通過內在的、非強制的方式形成公序良俗,以德從政,以德履職。 對于公共組織而言,應注重法律與道德兩方面的績效考核,評估領導者對推進本單位的規章制度建設和作風建設方面的成績。對領導者而言,守法,有積極與消極之分,消極守法為不違法,積極守法為自覺適用法律,推進法制,在本人工作范圍內促進組織的法制化;尚德,有個體與集體之別,個人之德為私德,集體之德則以個人行為服從社會道德、集體良俗,并且將二者統一起來,即法諺所說“守法即美德”。 注釋: ①因為領導力本質為公權力,因此領導力建設是公權力的規范問題。作為制度的規范,有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實施機制。參見:道格拉斯·諾斯. 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M]. 陳郁, 羅華平,譯.上海三聯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7。 參考文獻: [1]鄧小平文選[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6. [2]朱蘇力.法治及其本土資源[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3]江澤民文選[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96-202. [4]李德順.德治還是法治——不可回避的選擇[J]. 黨政干部學刊, 2007,(6);張中秋.法治及其與德治關系論[J]. 南京大學學報, 2002,(3). [5][法]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M].嚴復,譯,上海:三聯書店,2009∶169. [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21. [7]Ciulla,J.Editor, Ethics,the heart of leadership[M]. Praeger,Wesport,CT, 1998∶169192a. [8]蕭鳴政.關于領導干部道德測評的問題研究[J]. 北京大學學報, 2013,(6). [9]張文顯.法理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468. [10][美]理查德 L·哈格斯, 羅伯特 C·吉納特, 戈登 J·柯菲. 領導學——在實踐中提升領導力[M].朱丹,譯. 北京:機械出版社,2012. [11][美]羅斯科·龐德.法理學 [M].封麗霞,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175. [12][英]約翰·奧斯丁.法理學的范圍[M].劉星,譯.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29. [13][美]德波拉·巴瑞特.領導力溝通[M].鄧天白,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15. [14]車洪波,鄭俊田.領導科學[M].北京:對外經貿大學出版社,2013∶74. [15]付子堂.法理學初階[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 [16]劉建軍.領導學原理——科學與藝術[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185. [1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41344. [18]Max Weber. Economy and Sos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M]. Edited by Guenther Roth & Claus Wittic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 Vol.1 , p.215. [19][美]蘭德爾·科林斯, 邁克爾·馬可夫斯基.發現社會之旅——西方社會學思想述評[M].李霞,譯.北京:中華書局,2006∶205. [20][美]切斯特·巴納德. 經理人員的職能[M].王永貴,譯. 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13. [21]劉松博.領導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87. 【責任編輯:黎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