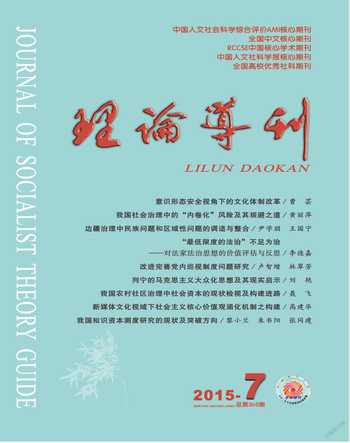“最低限度的法治”不足為治
李德嘉
摘要:學界有一種看法,認為法家的法治思想類似于西方的形式法治思想,可以稱之為一種“最低限度的法治”,希望能從中探尋法家法治思想的現代價值,使之實現現代性的轉化。然而,將法家的法治思想類比于西方的形式主義法治,不僅是對西方形式主義法治觀念的誤讀,而且忽視了法家法治思想中導致極權的思想因子。法家思想遏制社會自治的發展,忽視家族倫常對于社會治理的意義,其中的法治主張并非沒有價值因素,但隱藏在其形式主義法治主張背后的是國家至上、君權至上的價值預設。因此,忽視社會自治與道德價值的法家式法治并不是能帶來良善的社會治理方式。當下的法治中國建設需要從古代法家的法治思想中吸取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重視對社會自治力的培育,尊重市場和社會的自我發展規律。
關鍵詞:形式法治;工具價值;法家法治思想;價值評估;社會治理;良法之治
中圖分類號:D92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7408201507-0037-04
近年來有學者以形式法治的思路來反觀傳統法家的法治思想,他們驚奇地發現,如果剝離價值因素來看法家,法家思想與西方形式法治之間似乎存在著種種暗合。有學者以類型化的思路分析了法治的不同模式,指出法家法治實質是非民主的形式法治,法家關于法律公開性、穩定性、普遍性等問題的討論是在探討法律的內在價值,與富勒所提出的法治八項原則有相通之處。[1]還有學者認為法家所提出的實際上是一種“最低限度的法治”,論者認為法治與現代西方形式法治的區別僅在于立法的主體是君主還是人民,如果時空變換,在法學方法論上君主與人民兩個概念發生邏輯上的轉化是相對容易的,因此,普世主義的視角可以為法家思想的現代轉化提供一種有效的進路。[2]這種將法家思想與現代形式法治相類比的見解有助于人們重新認識法家思想的重要意義,就探尋法家思想的現代性轉化的途徑而言,不失為一種頗有啟發的思路。然而,這種“最低限度的法治”實際上是一種脫離了歷史實踐和社會價值基礎的純粹邏輯上的產物,不僅不能回答法家思想為何在歷史實踐中導致了極端專制主義的暴秦,其自身也根本不能實現社會的良好治理,因此會陷入理論上的困境。
一、形式法治的內涵[HT5",85XH]
主張“最低限度的法治”的論者往往援引拉茲的法治觀作為對形式法治內涵的說明,并以法家關于法的屬性的討論來與拉茲或富勒的形式法治的若干原則相互印證,以指出法家所主張的法治其實與形式法治相容,是一種工具主義的法治論。這種說法不僅片面理解了法家所欲實現的法治,而且對拉茲的形式法治也有誤讀。
拉茲曾開宗明義地指出,他的法治觀是一種形式的法治觀。他認為法治并不要求法律應如何制定,是否合乎民主立法的原則,也不涉及基本權利、平等或正義。拉茲在富勒八項法律內在道德的基礎上提出了法治的八項原則:法律必須是可預期的、公開的和明確的;法律必須是相對穩定的;特別法應該在公開的、穩定的、明確的而又一般的規則指導下制定;司法獨立應予以保證;自然正義的原則必須遵守;法院應對各項原則的實施享有審查權;訴訟應當簡便易行;刑事執法機構不能利用自由裁量權歪曲法律。[3]214218拉茲容易被誤解和飽受爭議之處在于,他對法治的性質做了形式化與工具化的解釋。他認為,法治是法律所固有的美德,法治既可以服務于良好的目標,也可以服務于邪惡的目標,因此法治是一種工具性的美德。[3]225226正是由于拉茲對法治采取了這樣一種工具性的觀念,因此,也常常被人們誤讀為是一種價值無涉的法治觀念。有人批評這種價值無涉的法治觀念說:“將價值要素從法治概念中抽離出去,也會使得這樣的概念喪失其內在的自我識別、自我評判的道義能力或道德力量。”[4]所謂“最低限度的法治”也正是在這一點上將法家與形式法治進行比較的,認為法家的法治思想也可以脫離一般的價值基礎來討論,我們可以不考慮任何價值因素而實施法家的“依法而治”主張,似乎只要我們做到了法家的“緣法而治”也就實現了“法治”。
[JP+1]其實這種理解存在著“直把杭州作汴州”的混淆時空與社會背景的解讀,所謂形式法治并非不關心實質價值,或者覺得沒有實質價值一樣可以實現良好的社會治理。在形式法治之說發展的時代,西方人關于人的尊嚴、自由等問題已經達成了基本的社會共識,形式法治所需要解決的問題不是如何保證人的尊嚴或自由的問題,而是在價值多元的社會中,只有通過嚴格的法律程序才能實現對多元價值的保護。因此,在形式主義的法治看來,法律的實質價值并非沒有意義或不存在,而是不應該是法治所考慮的問題,應當是政治哲學、道德哲學考慮的問題。拉茲就專門分析了法治的價值問題,并把法治的價值概括為三個方面:一是遏制專橫的權利;二是保護個人自由;三是尊重人的尊嚴。拉茲認為,法治是一種消極的價值,法治的作用在于將法律追求其他崇高目標時可能對人的自由尊嚴造成的損害降低到最小。[3]228由此看來,形式法治并非真正的價值無涉,只是他們認為法治本身只具有工具的價值,但是法治作為一種工具,必然有其可欲的價值或是作為目的的價值,那就是遏制權力與尊重人的尊嚴與自由。在自由主義的基本社會共識下,這些目的性的價值恰恰是不言而喻的。在還原了形式法治的社會背景之后,我們發現,其與法家法治的基本分岐恰恰就在于法治的目的性價值,在法家看來法治的目的性價值在于富國強兵,個人的自由與尊嚴恰恰可能是實現富國強兵的障礙。[JP]
完全無視目的性價值的法治主張在西方的歷史上也曾經出現過,而且和形式法治之間的關系密切,以至于有人將其與富勒、拉茲等人所主張的形式法治相互混淆。塔瑪拉哈將形式法治分為三種:其一是依法而治理論rule by law,其二是形式合法性理論,其三是民主與形式合法性理論。[5]其中依法而治的形式法治觀對法律和法律體系沒有提出任何要求,只是認為政府的行動必須有法律授權、依法實施。比如,二戰前德國的“依法而治”理論就僅僅強調行政權力和行政行為具有合法律性、合職權性、可控性和可預測性,建立行政法院對行政行為加以控制和審查。[6]這種“依法而治”理論實際上就與只強調法律被遵守的“最低限度的法治”相類似,在這種理論的概念中,法治只具有工具價值,而從來不用考慮法治所欲實現的目的價值。歷史的實踐已經證明,這種完全工具意義和形式意義的法治,最終導致法治國家蛻變為“法律國家”甚至與法治風馬牛不相及的“暴力國家”。[7]
二、法家法治與形式法治的區別[HT5",85XH]
明確了形式法治的內涵之后,我們發現法家法治和形式法治的區別并不在于法治的形式要素上,而在于形式法治所欲保護的價值上。形式法治不僅將人的尊嚴視作法治所欲保護的價值之一,而且認為自由而理性的個人是實現法治的基礎。在這一點上,法家法治與形式法治截然不同,法家法治所欲實現的價值從來不是個人的價值,而是國家的價值,在法家眼中,民只是實現國家富強的工具,從來都不是國家所欲成就的目的。有學者以為,雖然法家重視富國強兵等國家價值,但民作為富國強兵的基本要素,依然可能得到法家的認真對待。[8]這種看法是只見到了法家重視民的表面現象,盡管法家重視民的作用,而且是“民本”思想的提出者,比如管子就曾經說:“政之所以興,在順民心;政之所以廢,在逆民心。”又說:“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今天有學者認為管子所言的“以人為本”是法家重視民心向背在政治中的重要作用,是利民愛民的重要表現。這種觀點其實是沒有從完整的邏輯結構上去理解法家的思想,說法家有利民的思想則可,說法家有愛民的思想則難以成立。章太炎先生在《原道》一文中非常深刻地指出了法家思想的本質所在,章太炎先生批評法家韓非的思想是一種國家主義的視角:“有見于國,無見于人;有見于群,無見于孑。”[8]法家思想中的“愛民”“利民”充其量可以培養一群虎狼之民,牛馬之士,國雖治,政雖理,但是其國家的人民卻不能成為一個獨立的人。這樣一種國家主義的立場顯然與尊重個人價值和尊嚴格格不入,不僅不是人本思想的體現,反而是反“人本”的。
論者一廂情愿式地認為,法家討論人性惡的意義在于順應人情來構建制度,并且進一步說明順應人情的制度構建與人格尊嚴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系。[2]其實法家主要是利用人有趨利避害的心理,制定賞罰以驅使和駕馭民眾,同時,利用人臣欲求富貴之心而役使之,以成就君主之霸業。韓非子就說:“富貴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挾大利以從事,故其行危至死,其力盡而不望。”《韓非子·六反》[HT5",85XH]在法家看來,全國的百姓實際只有能為國效力才有其價值,如果百姓難以驅使利用,則根本就是國家的累贅。韓非假借太公望之口說:“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無求于人者,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無上名雖智不為望用。不仰君祿,雖賢不為望功,不仕則不治,不任則不忠。”《韓非子·外儲說右上》[HT5",85XH]如果一個人生性不好名利,并且又不肯為君主所用,那么這樣的人就難以以賞罰來管理,在法家看來就是難治之刁民。可見,法家之所以將人性認識為趨利避害的,其實完全是出于“使民”的目的。法家深刻地抓住了人性趨利避害之特點,然后以刑賞駕馭群臣,最終都是在為君主實現霸業而服務。法家談論人性之目的并非探尋制度與人性之關系,以追求一種順應人情的善良制度,而是利用此種趨利避害之心來役使百姓、人臣,最終都是在為國家之富強服務。熊十力先生在此評論說:“是天下臣民皆為霸王而生,為霸王而死,真微蟲螻蟻不若也。”
綜上所述,法家與形式法治的區別并不在于君主是否凌駕于法律之上或者說法律是否是約束行政而不約束立法,法家所提出法治的主張首先就要求君主遵守自己制定的規則,這樣才能實現賞罰標準的確立,也就是法家所說的“君臣貴賤上下皆從于法”。這樣看來,法家所主張的法治是既約束行政,同時又限制君主的立法行為。法家與形式法治的真正區別在于法治的目的為何,形式法治認為法治的目的在于維護已經成為社會共識的人格尊嚴與自由,而法家則認為法治乃是國家實現富強的工具。單純的形式上的“依法而治”或是所謂“最低限度的法治”并不能產生良好的社會治理效果,歷史證明,法家式的“最低限度的法治”導致了秦政,而西方歷史上的“依法而治”理論則使“法治國家”蛻變為“暴力國家”。
三、法家法治的制度之弊[HT5",85XH]
過去,學界對于法家法治之弊的認識主要集中于君主專制主義方面,以為法家之弊主要在于君主專制。法家之法治之所以難以推行,在于君主的權力不受控制,君主法外濫權的情形比比皆是,幾乎成為常態。如果在現代民主政治的基礎上,再來運用法家法治則就可以充分發揮法家法治思想之所長。其實,這種看法似是而非,法家直言君主之“勢”的重要,強調加強君主專制權力的能力,以法作為君主鞏固權力的工具,這些固然是法家思想不合于現代的重要方面。但君主專制尚不是法家思想制度設計的根本之弊,法家法治思想之弊在于其破壞了社會中家族基本倫理、取消了百姓的自治空間,將整個社會以“壹言”“壹教”“壹刑”的方式壟斷在國家的權力之下。這種制度設計中蘊含著一種極權主義的因素,希望將整個社會組織、社會自治力量以及百姓全部集中于以君主為中心的權力核心,目的是將整個社會、所有百姓都打造成耕戰的工具。如果不能認識到法家思想中的集權因子,則法家的現代轉化根本無從談起。即便是民主社會,依然要警惕集權思想所帶來的危害,在民主制度的條件下,民主制所產生的公意也可能成為推行集權的合法依據,民主所帶來的多數暴政將成為國家消滅一切反對力量和少數派的工具。從法家法治思想背后的集權因素出發,我們發現其制度之弊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其一,在“勢治”的基礎上推行“法治”,使法律成為權力的工具。法家以為“君之所以為君者,勢也”。《管子·法法》[HT5",85XH]所謂“勢”,就是法律上的權力和統治者所控制的勢力,也包括了暴力。慎到對“勢”的解說更為直白:“不肖而能服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不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可見,統治者之所以能維持統治,在法家看來,根本不在于統治者是否有智慧、是否有德行,而在于統治者是否權重位尊,換句話說就是,只有掌握權力才是維持統治的基礎。這樣的結論表面看來是大白話一句,只是對政治實際的概括和總結,深入思考會發現,掌握權力這一事實本身并不能論證統治的正當,法家根本沒有去回答誰應該掌握權力、怎樣的人才配掌握權力這樣的問題。在這樣的思維支配下,在法家看來,法就成為維持統治的工具,統治者“抱法處勢”就能夠維持統治,實現天下大“治”,“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或有學者為法家辯護,認為法家深刻地認識到了政治統治的“實質”,將道德劃于政治領域之外,頗有西方近代純政治學之色彩。這種觀點是片面理解了法家的思想,法家將道德剝離政治的前提是其尊君的主張,法家一面尊君,一面又將道德剝離政治,忽視政治的正當性的意義,實際上產生的結果就是將君主的利益作為統治的唯一目的。[9]216章太炎評說法家“有見于國無見于人”,此說還未為精到,法家實是有見于君而無見于國,更遑論人。蕭公權認為:“君主遂成為政治上最后之目的,唯一之標準,而勢治亦成為君主專制最合理之理論。”[9]216在“勢治”的基礎上推行“刑治”,本質是將刑作為統治的工具。韓非說:“君無術則敝于上,臣無法則亂于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韓非子·定法》[HT5",85XH]韓非還形象地將“刑”與“德”實則是賞比喻為虎之爪牙,虎之所以為萬獸之王全在于爪牙之利,若虎無爪牙,則反不如犬,君主之所以有權力,能維持統治則全在于“刑”“德”,他說:“明主之所以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韓非子·二柄》[HT5",85XH]
其二,法家之法治消滅社會,使國家以外無社會,君權之外無權威。法家認識到社會發展對于君主權力的抑制作用,因此,害怕社會發展,千方百計希望能破壞社會,維護君權的獨大。《商君書》中說:“國治,斷家王,斷官強,斷君弱。”《商君書·說民》[HT5",85XH]有人將“斷家”理解為“國家的政事由人民在家里來判斷”[10],似乎從這句話看出法家允許宗族自治的味道,實際上這樣的理解與商君的本意相差甚遠。所謂“斷家”的涵義是指:“王者刑賞斷于民心,器用斷于家。”如何做到“刑賞斷于民心”,則要使民眾相互約束,相互保證,互相揭發犯罪,也就是鼓勵百姓之間的互相“告奸”。商鞅認為,百姓互相檢舉揭發,便會使百姓不敢犯罪,甚至于連心里都不敢起犯罪的念頭。儒家以“親親相隱”的規定來保護家族內部的人倫親情不被國法所破壞,而法家則要使國法深入人倫親情之中,讓人們除了效忠君主,連自己的親人也不能存有私情。商鞅又說:“用善則民親其親,任奸則民親其制。”《商君書·說民》[HT5",85XH]所謂“任奸”,就是鼓勵家人之間互相揭發犯罪,目的是使百姓“親其制”,讓人不去愛自己的親人而愛國家的制度,將社會中的倫理親情全部消滅,剩下的只有“法制”和“君令”。用商君的話來說就是:“民勝法,國亂。法勝民,兵強。”其最終的結果就是使百姓成為君主的愚民、順民,除了效忠君主,百姓的心目中不存在其他的權威和領袖。在法家的思想中,君、君法以及君法所主導的社會秩序代替了儒家“天地”“親”“師”等社會權威,使君主成為唯一的社會權威,整個社會的價值體系、規范與秩序都嚴格依照君法來形成,這就是所謂的“以法為教”,而“以法為教”的結果就是讓君主的好惡、是非壟斷民間社會的價值取向和道德判斷,從而形成一個從價值體系、社會運行秩序到倫理規范、法律規則都為官方所壟斷的極權社會。
其三,法家通過人性的趨利避害,以刑賞控制人。法家利用人有趨利避害的心理,制定賞罰,以利益和威嚇驅使人民按照統治者的意思來行動,統治者所需要建設的事業就以重賞使民效死命,統治者所痛恨的事情就設置重刑使民不敢犯。同時,法家主張將法律作為政治生活的唯一標準,提出以法為教,實際上就是以法來統一全國百姓的思想。集中全國之民力去進行耕戰,如此來打造一個強大的國家。因此,法家強調“一賞”“一教”實質是使“富貴之門必出于兵。是故民聞戰而相賀也,起居飲食所歌謠者戰也”。《商君書·賞刑》[HT5",85XH]《商君書》就曾說:“利出于地則民盡力,名出于戰則民效死。”同時,法家主張“利出一孔”,以“一賞”的方式來實現對社會的控制。所謂“利出一孔”就是說君主要操控天下一切利益、資源,使“富貴之門,要存戰而已矣”。《商君書·賞刑》[HT5",85XH]百姓除了耕戰,為君主賣命,而不存在其他獲得富貴的機會途徑。
四、結語
西方與中國古代的歷史實踐表明,“最低限度的法治”并不意味著良善的社會治理,忽視了法治的目的的所謂“最低限度的法治”容易使法治的社會走向其反面。當下的法治中國建設正需要從中國古代法家的法治思想中進行反思,為法治的實踐提供正反兩方面的經驗。
首先,法治建設與社會治理方式的轉變是相互關聯的。法家“最低限度的法治”所代表的社會治理方式是集權式的,通過“利出一孔”的制度設計實現對社會的全面控制,加強君主的中央集權。在今天的法治建設中,我們應該注意社會治理方式的轉變和創新,激發社會組織的活力,這中間首先面臨的就是如何理順政社關系,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自我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法家所提倡的所謂“最低限度的法治”并不足以實現社會自我調節,其中的弊害尤為值得今天的人們所認真總結。當下的治理難題需要人們充分吸收中西古今關于社會治理方式中的經驗與教訓,從而實現社會治理方式的改進,實現社會組織活力的激發。
其次,注意協調法治與道德之間的關系。法治并不是脫離任何道德因素的純粹規則之治,現代法治本身就意味著包涵道德判斷的良法之治。然而法家之法治卻徹底剝離了道德的要求,并且以“賞罰”的手段消滅了民間社會的家族倫理道德。法家所行告奸之法破壞了家族親人之間的倫理秩序,一旦家族中的親情與信任被消滅,民間社會的基本道德秩序也會隨之淡薄。其消滅民間社會的道德倫常,目的是使百姓成為沒有價值判斷的耕戰機器,易于為君主所役使。在今天的法治建設中,我們應該同時注意對民間社會道德秩序的重建,重新思考法律與道德之間的關系。道德秩序的建立并不僅僅是公民教育的社會問題,同時也是一個制度問題。好的制度應該能為社會道德秩序的建立奠定基礎,反之,壞的制度卻能瓦解社會中的道德秩序。
最后,法家的法治思想也有值得今天借鑒之處。就法家法治思想的正面意義而言,法家之“法治”觀念對于政治的認識采取了一種冷峻而深刻的態度,其對于人性的描述也頗有見地,對于官吏的管理與控制的研究更是入木三分。比如,法家將人性惡的假設運用于吏治,尤其是在控制官員的權力上面。法家強調利用人性的自利性,通過權力的劃分使權力之間產生相互制衡的作用,來實現君主對官員的控制。商鞅對此說得十分明白,他說:“夫置丞立監者,且以禁人之為利也。而丞監亦欲為利,則何以相禁?故恃丞監而治者,僅存之治也。通數者則不然,別其勢,難其道。”[HTF](《商君書·禁使》)[HT5",85XH]所謂“別其勢,難其道”就是通過權力的分工與相互制衡來起到官員之間相互制約的作用。
參考文獻:
[1]高鴻鈞 先秦和秦朝法治的現代醒思[J] 中國法學, 2003,(5)
[2]王人博 一個最低限度的法治概念——對中國法家思想的現代闡釋[J] 法學論壇, 2003, (1)
[3]Joseph Raz The Authority of Law: Essays on Law and Morality[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214-218
[4]高鴻鈞 法治:理念與制度[M] 中國政法大學, 2002: 183
[5]Brian Z Tamanaha On the rule of law: history, politics, theory[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91
[6]鄭永流 法治四章[M]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98-112
[7]邵建東從形式法治到實質法治——德國“法治國家”的經驗教訓及啟示[J] 南京大學法律評論,2004,(5)
[8]章太炎 國故論衡[M]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115
[9]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M]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216
[10]高亨商君書注譯[M]清華大學出版社,201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