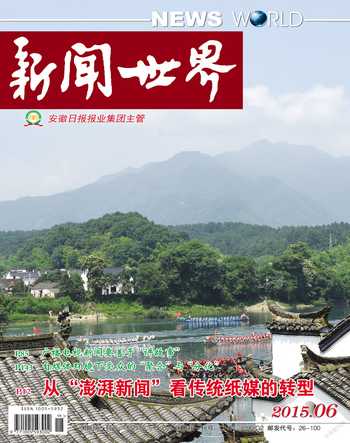試論媒介公共領域的娛樂化形態
閻安 鐘水兵
【摘要】以《非誠勿擾》為代表的真人秀節目開辟了廣播電視對公共領域介入的第三種形態——娛樂化形態。按照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概念,《非誠勿擾》在討論平臺、參與主體,以及理性批判的精神等層面已經具備了媒介公共領域的一些重要特征,盡管其在娛樂化浪潮中面臨“異化”的壓力,但仍提供了公共領域存在的一種新可能。
【關鍵詞】媒介公共領域電視節目非誠勿擾
我國廣播電視節目對公共領域的介入通常存在三種形態:一是輿論監督形態,即以新聞媒體為主體,通過新聞調查與批評報道對公共權力實施監督,以《焦點訪談》等為代表;二是論壇形態,即借助虛擬的、受眾參與式的廣播電視論壇,探討公共話題,吸納社會意見,與權力部門對話,以《實話實說》等為代表;三是娛樂化形態,即在廣播電視公共領域中植入一定的娛樂元素,寓“言”于樂,江蘇衛視的現象級欄目《非誠勿擾》堪稱此形態之代表。
一、《非誠勿擾》對媒介公共空間的另類建構
《非誠勿擾》始播于2010年。該節目以相親為形式,融合速配、訪談、才藝表演、真人秀等多種形態元素,更接近于綜藝娛樂節目。按照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概念,必須具備特定的討論平臺、參與主體,以及理性批判的精神,才有可能實現真正的公共領域空間。若從這三個方面入手,將《非誠勿擾》熱鬧喧囂、光怪陸離的娛樂外衣剝離,一個關乎城市、關乎社會、關乎公共利益和時代記憶的電視公共領域便會清晰浮現。
1、討論平臺:由“人生”觀照“民生”
廣播電視公共領域的起點在于一個可供公眾充分參與、交流的平臺。在這里,“世界看起來普通、世俗、所有的人都可以接近、了解、熟悉、辨別、理解、分享和交流。每個人都可以談論”①。說《非誠勿擾》建構起一個另類的公共領域,是因其不僅僅提供娛樂或服務,更提供了話題討論的場域。“節目形式上是交友,實際上卻是借助交友這個節目形式來形成對大家談話的一個刺激,在現場產生各種觀念價值的碰撞,激蕩出思想的火花,這種話題往往對人對己都能形成某種觸動。”②
在世界各地,相親都是一種復雜的社會交往活動。為與未來可能的伴侶深入了解,必須進行充分的溝通,因此,談話成為相親活動的主要互動方式。在形式上,《非誠勿擾》采取24位女嘉賓與1位男嘉賓提問應答的方式展開;節目現場另有主持人孟非和兩位點評嘉賓隨時介入討論。至于談話的話題,大多由男嘉賓的介紹短片引出,涉及職業、興趣、過往經歷等。談婚論嫁是一個特別復雜的話題,在主持人的引導下,由婚戀生發開去,小可及人生故事,大可至國計民生。比如,說起一個可樂瓶,便可能激發關于社會環保現狀的討論;有人說喜歡飆車,就可能聯系到“70碼”;有人說希望生三個孩子,便難免關注到計劃生育政策。這個節目最終呈現出來的東西,讓人們看到生活的真實狀態。就像一位老華僑講的,“我在海外生活了30年,這個節目,讓我們這些在海外漂泊的華僑真正能夠看到祖國的變化和祖國人們的現狀。”③
不難看出,《非誠勿擾》是一個討論平臺,是一個由對話組成的、能夠形成公共輿論的特殊交往空間。因此,在形態上,它更類似于一檔關于人生與社會的談話節目,它為社會提供豐富的話題,并誘發觀眾的理性思考。因此,可以認為它“創造了一個沒有空間限制的新的公共領域,這個領域不一定限制在對話中,它也向無限多的個體開放,甚至于個體只要呆在家中的私人空間里就行了。”④從“人生”到“民生”,那些具體而微的市井言談彰顯了節目的公共性,賦予其遠遠超過相親活動本身的社會價值。
2、參與主體:由私人領域折射公共領域
現代傳媒既是啟蒙的中介,又是公眾討論批判的延伸,它將公眾引向話題的討論,并且將討論的結果反饋給公眾,促進個體間的溝通交流。公共領域的參與主體由具有批判意識的公眾組成。他們必須具有一定特質:一方面他們是獨立、平等的個人,因此不存在利益集團或多數壓制:另一方面他們實際上是符合一定教育、收入條件的市民階層,敢于并善于在鏡頭前表達自己的個性觀點和不同意見。
《非誠勿擾》的男嘉賓輪番出場,而女嘉賓相對固定。從其職業、經歷和個性特點來看,顯得十分多樣化,由于她們常常語出驚人,屢屢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在現實生活中,相親交友是相對私人的行為,這與“真人秀”有所不同。對于站在《非誠勿擾》舞臺上的這群人來說,社會角色遠遠超過了家庭成員的角色,男女嘉賓從事五花八門的職業,有著紛繁復雜的社會背景和參差不齊的年齡,可以說,每個角色都有其特定的符號意義。現代傳播介入私人領域的后果便是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的“融合”,這一點在以往真人秀節目中已有充分體現。在現代城市,孤單的個人內心領域為社會力量填充和塑造,從而使個人內心領域變成“偽私人領域”。哈貝馬斯認為,現代社會的家庭正逐漸失去經濟功能、保護功能和塑造個人內心的力量。因此,個人獨立性越來越強,家庭成員成為形單影只的個人或數個人的組合,這和“真人秀”中群聚一堂的男男女女非常類似。
在鎂光燈下,攝像機前,很難再有私密的相親活動;為了博得主持人、觀眾和對方的關注,“出位”言行時有發生。一個顯露的趨勢是,盡管公共領域“理性匿名自我”和私人領域“情緒真實自我”的區分仍十分明顯,但公私領域的嚴格劃分已開始瓦解,私人領域逐步走向政治化和商品化。在節目中,一些原本相親時私聊的話題,如“剩女”、“啃老”、“婆媳矛盾”、“421家庭”、“月光族”、“蝸居”、“蟻族”、“房奴”等,因其代表了當代城市年輕人的普遍心聲,能夠引發社會“共鳴”而成為輿論熱點。開放、活躍且相對自由的參與主體使《非誠勿擾》呈現出與現實中相對私密且個人化的相親活動完全迥異的面貌。
3、批判價值:由觀點碰撞轉向理性表達
在“意見的超級市場”,公共空間理當成為人們表現其主體獨立性、選擇性、差異性和批判性的關鍵領域。作為公共領域和“真人秀”的《非誠勿擾》,“不但反映了業已存在的態度和情緒,還為這些態度和情緒體勾勒一個宣泄的場所”⑤,各種行為習慣和意見觀點的碰撞便在所難免。《非誠勿擾》在嘉賓選擇和現場把控上的寬容度為觀點碰撞和“不同意見者”存在提供了機會。孟非說:“我們只是多提供了一些思考問題的角度和看問題的方式,而不是輕易下結論。”“在一些可以討論的領域,當某些會引發碰撞的生活方式和態度在這個節目中呈現的時候,我們可以通過平等討論,積極引導”⑥。開播初年,女嘉賓馬諾爆出“寧愿坐在寶馬車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車上笑”的拜金言語,“富二代”劉云超則以玩證券、飆車、打高爾夫球等經歷炫富。這些原本屬于私域的話語因蔓延到公共領域而備受爭議。其實,“媒體實現多元對話的原則在于‘容納’不同意見者,更開放的呈現反對或挑戰權威的意見,免除排他性的霸權心態,尊重并凸顯不同社群的立場。”⑦《非誠勿擾》以拋磚引玉式的引導,形成了社會話題另類表達和對話交流的特殊場域,在這里,不同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因形形色色的觀點碰撞而一一呈現。無論是拜金女,還是炫富男,其出位的話語對于媒體聲音來說顯得“離經叛道”,卻常常是現實社會的投射,是現實生活中私人領域的相親活動普遍關注的議題,因此,其更易喚起觀眾的心理認同。在這個意義上說,這些微觀真實的“異見”表述構成了對既往中國一元話語體系的反叛,體現出《非誠勿擾》這個另類公共領域獨特的批判價值。
二、娛樂時代媒介公共空間的“異化”壓力
泛娛樂化是后現代社會一道引人注目的媒介景觀。在消費文化日趨強勢的當下,娛樂已成為城市人群重要的生活方式。消費文化說到底是一種娛樂文化,視聽媒體強調的快感、游戲、互動和體驗的特征迎合了消費者欲望宣泄的需要。在這種生產理念的支配下,新聞、社教、服務類節目無不呈現娛樂化特征,媒介公共空間難免變身為娛樂秀場。受資本逐利性和大眾文化娛樂狂歡本性的雙重驅動,媒介公共領域時刻面臨“異化”的壓力。真正意義上的公共領域,應是民主、平等討論重大社會政治問題的空間,而在娛樂元素融入之后,一些媒體也出現了過分追求平面化、市民化、大眾化的現象,放棄其作為社會公器的“話語權”,導致理性反思缺失、批判話語弱化、知識分子淡出,電視熒屏越來越淪為一種“偽公共領域”。例如,《非誠勿擾》在開播一段時間之后,便為迎合收視率而放縱嘉賓言論,雖為“少數派意見”提供了寬容的表達平臺,但原本相對理性的對話空間也存在淪為“出位”言論舞臺的危險。一些嘉賓為求一言驚人、一語成名,放縱自己爆出夸張、激烈的歪談、怪論、誑語,進行無底線的調侃,各種吸引眼球的擇偶觀點和怪誕行為相繼出現。其結果是國家廣電總局于2010年6月下發文件,對婚戀交友節目中的涉性低俗內容和傳遞拜金主義等非主流價值觀、婚戀觀的行為進行整治。
《非誠勿擾》是娛樂包裝下的對話空間,也是折射現實、溝通社會的娛樂秀場。在哈貝馬斯的論述中,公共領域有兩個重要的指標:質量——理性、批判性話語的質量或形式;數量——公眾參與的數量或者說公共領域自身的開放性。從這兩個指標看,媒介公共領域的娛樂化形態存在先天不足。由于節目形態的自身的局限,參與互動和討論的嘉賓數量有限;由于對收視率的追求,節目呈現為嘉年華式的狂歡儀式和視聽盛宴,而非純粹的議事場所或公眾論壇;由于諸多娛樂賣點和商業元素的植入,節目留給社會公共話題討論的時間相對有限,很難充分展開。顯然,《非誠勿擾》無法作為主流的、典型的公共空間存在,但這并不意味其中公共性的消亡,相反,在這個極速消費的時代,它為公共領域存在提供了一種新可能。
參考文獻
①戴維·錢尼:《文化轉向——當代文化史概覽》[M].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130
②趙允芳:《“這個舞臺,更像是一個社會大觀園!”——樂嘉訪談》[J].《傳媒觀察》,2010(11)
③⑥高慎盈等:《應該明白“我是誰”——對話主持人孟非》[N].《解放日報》,2012-4-20
④羅杰·西爾弗斯通:《電視與日常生活》[M].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99
⑤約翰·斯道雷著,常江譯:《文化理論與大眾文化導論》[M].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67
⑦張錦華:《公共領域、多文化主義與傳播研究》[M].正中書局,1997:41-47
(作者單位:閻安,南京政治學院新聞系;鐘水兵,成都軍區聯勤部錄像室)
責編:姚少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