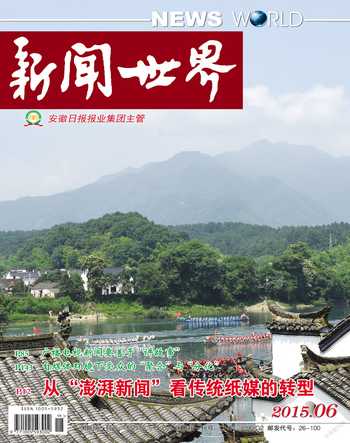近代中國自由主義者的抉擇
李慧琪
【摘要】本文試以現代化范式為基礎,并且結合新史學“一切都是當代史”和“一切都是思想史”的理論背景,運用相關新聞學、政治學的知識,通過以《大公報》在重慶談判前后的相關社評和相關言論分析,以小見大地反映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階層在面臨抉擇時的反應以及其所面臨的現實與理想間的差距。并且試圖以近代中國自由主義者在具體歷史情境下的實踐所提供的經驗和教訓為我們今天重新反省百年來的現代化進程提供參考。
【關鍵詞】大公報言論重慶談判近代中國自由主義
在中國近代自由主義運動發展的歷程中,20世紀40年代是一個歷史機遇,尤其是40年代的后半個時期。由于抗日戰爭取得了勝利,國共雙方的關系重新緊張起來了。在共產黨激進主義和國民黨保守主義對峙的縫隙中,自由主義者們認為他們的春天來了。這是因為,“在本世紀的大部分時間段落里,他們只能處于社會邊緣地帶默默地積蓄自己的能量”①,而到了這個特殊的歷史時刻,在這種特殊的歷史機遇的刺激下,他們“驀然產生了參政的狂潮,發展成了一股波瀾壯闊的自由主義運動”②。20世紀西方的各種思潮引入中國,從西方自由主義引入中國的那一天開始,在黑暗中艱難地探索著的自由主義者們就在等待這一機遇的到來。
當時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參政的渠道主要有兩種,一種是保持政治獨立,通過“文人論政”的方式批評官方政治,鼓吹個人自由和民主憲政。例如《大公報》的主編王蕓生、胡政之等;第二種是自由主義者聯合組黨,以獨立于國共兩黨的“第三種力量”進入政治體系內,例如民主同盟、民主建國會、民主促進會等政黨組織。這一時期的中國自由主義運動的實質性展開就是從這兩方面進行的。但是最終,一方面國民黨政權進行強硬的政治施壓,不斷迫害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終于導致了民主同盟在1947年11月宣布“自動解散”,1948年前后幾乎所有的民主黨派重要成員都流亡失所;另一方面,國民黨政權極力打壓民間自由主義辦報的組織,主要通過新聞檢查制度和報刊封禁制度來顯示其專制的權威,中國近代自由主義運動在歷史條件完全不具備的社會現實中走向了悲劇性的歷史結局。
重慶談判從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經過43天,國共雙方達成《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這一重大的歷史事件是這一機遇到來的先兆。隨著政協決議的被撕毀以及國共內戰的全面爆發,標志著中國自由主義運動遭到了空前挫折。③從自由主義運動在40年代中期萌發到最終的結束,作為標榜自由主義的第一大報,在這一時期《大公報》在這一具體歷史環境下自由主義者們的探索和掙扎以及最終的選擇仍然是十分具有研究價值的。
《大公報》作為“文人論政”重要的民間報業,其社論、新聞通訊以及“星期論文”對于自由主義運動而言是十分重要的陣地。筆者試以重慶談判開始(1945年6月)到1948年年初民主黨派的全面凋零這一時間內《大公報》關于自由主義道路探索的相關言論作為研究對象,分析其在這一時期內《大公報》的政治立場。
在《自由的歷險——中國自由主義新聞思想史》一書中,張育仁在解釋自由主義為什么在中國失敗時,提及了一點原因:觀念人物與行動人物的困擾和沖突④。張季鸞、胡政之、王蕓生等《大公報》報人從一開始接辦新記《大公報》就秉持“四不”原則——不黨、不賣、不私、不盲,超越黨派,超越政府,超越政治。從觀念上來講,他們不愿背棄堅守理性和崇尚個人自由的立場,他們應當始終站立在官方政治的對立面,保持對政府批評的姿態。但是他們還受到了儒家用世主義觀念影響,張季鸞在《上層知識分子的責任》一文中,這樣談到:“知識分子之為社會的活力,不在位高爵顯,不在財富傾城,而單憑了他們見解深闊,勇氣滂沱,而致一言興邦的偉績……成為今日中國知識文化中心之一的上層知識分子,必須脫去沉默旁觀的態度,堅握當前的政治責任,發為聲音,造成獨立健全的輿論,方能與政治相輔相成,并軌前進。⑤”從行動上講,他們不能容忍自己完全獨立于現實政治之外,要以筆為兵器,傳達民意、引導輿論,試圖以這種方式影響政治。但是在“國家中心論”的影響下,似乎總是有擁蔣的慣性。尤其是在40年代中后期,以民盟為代表的各民主黨派也進入了歷史的舞臺,他們對自由主義理念的踐行滿懷期待。但是他們忽略了一點,也是西方民主運動得以成功的條件,即只有確立了憲政、保障了言論自由、個人的權利被尊重,自由主義者們才有可能真正通過言論去影響政治,除此之外都是紙上談兵。起碼在當時蔣介石集權政府的統治下,這是不可能實現的。在40年代中后期,也就是在重慶談判開始之后的自由主義運動中,他們很快就被中國的現實狠狠地羞辱了。
1、對政治形勢判斷失誤
抗戰勝利后,國內的局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國共合作已經破裂。共產黨的武裝力量已經積聚,國民黨也在美國的支持下準備發動內戰、鏟除共產黨。在這樣的背景下,蔣介石政府為了拖延時間、調整兵力,三電毛澤東,邀請他來重慶共商國是。如果共產黨方面拒絕來渝,蔣介石政府也好以破壞團結之名發起內戰。但是對于政治家們的斡旋與伎倆,《大公報》似乎未曾察覺,對政治態勢的預估也從于表面。
《大公報》十分歡迎毛澤東來渝談判。在1945年8月14日的社論中,這樣寫道:“在我們歡慶勝利到來之時,國內也有一個令人興奮的新聞,就是蔣主席致電毛澤東先生,請其克日來渝,共商國是……果使國家的統一與團結完成于一席談,那真是喜上加喜,不但八年抗戰為不虛,且將奠定國家建設的千年大計!忠貞愛國的中國人,都在翹待毛先生的惠然肯來了。”⑥這篇社評高昂著滿滿的希望,完全從正面肯定了蔣介石的做法。也許《大公報》是為了營造一個國共和平共處的輿論環境,其實從客觀上也為蔣介石助力不少。接著,8月28日,毛澤東和周恩來、王若飛等一起抵達重慶。在29日的社論里,《大公報》表示:“毛澤東先生來了!蔣毛兩先生于昨晚重新握手,他們兩位一定有無限的感慨,他們兩位的會見,關系目前與國運及其遠大……說來有趣,中國傳統的小說戲曲,內容演述無窮無盡的離合悲歡,最后結果一定是一幕大團圓……現在毛澤東先生來到重慶,他與蔣主席有十九年的闊別,經長期內戰、八年抗戰,多少離合悲歡,今于國家大勝利之日,一旦重行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團圓!”⑦但實則,國民黨方面的態度是十分明顯的。國民黨中央機關報《中央日報》在29日的社論中,僅對重慶談判事件寫了稀稀落落幾十字的新聞稿。其主編的態度是:“重慶談判不會有什么結果,我們的發稿方針是盡量縮小此事的影響,力求穩當,只要不出亂子,不給共產黨以口實就行了。現在我們工作的重點,是利用談判爭取時間。⑧”
重慶談判還未結束,北方局部地區已經起了硝煙。與此同時,美國方面打算援助蔣介石,并且派來馬歇爾將軍“調解”國共矛盾。1945年12月22日馬歇爾抵達重慶。因為當時胡政之從美國訪問剛剛回來,《大公報》非常熱情地報道了這一事件,“馬將軍之來,時機甚好,對于中國統一團結之促進,必能發生良好的影響。”⑨
1946年初,馬歇爾組織成立了由周恩來、張治中和馬歇爾的三人小組,進行停止國內軍事沖突的談判。1月10日,國共雙方簽署了《關于停止國內軍事沖突的命令和聲明》,并且國共雙方分別發出了“停戰令”。1月11日,《大公報》發表了社評,稱“馬歇爾元帥是中國和平的接生婆,全國人民都特別謝謝他。”⑩但事實證明《大公報》完全沒有預估到之后的事實,十分盲目地相信了事態的表象。
重慶談判的成果是蔣介石被迫接受了“雙十協定”,準備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舊政協)。在31日的一篇社論中《大公報》表示:“政協會議得以終獲成就,各黨派的態度的妥協,都值得贊美。”⑾在充分肯定了會議結果之后,這樣說道:“最后,我們應該向國民黨道賀。國民黨領導國民革命,已大部分成功,領導國家抗戰已獲完全勝利。現在卸了一肩,減輕了責任。別的黨派相對的分了責任。以后國事若理不好,國人就不能專責國民黨了。由今天起,各黨派都要痛感責任,忠實于其本身的任務。”⑿王蕓生在事后回憶說:“寫這篇文章時,認為問題真的完全解決,因此就急忙安慰國民黨,給各黨派加壓力,實在把事情看得太簡單了。”⒀
很快,5月開始,內戰基本上就全面爆發了。此時,《大公報》的尷尬心情可想而知。21日,在《我們反對武力解決!》的社評中,這樣說道:“當前的國家局面,真令人太息痛恨!所謂和平談判,已沉悶得進入睡眠狀態;軍事行動的鑼鼓,卻加緊的敲打起來。……說‘政治解決’,高叫‘民主’,圖窮匕首見,還是武力解決!還是打!打!打!‘民主’,‘民主’,真是天曉得;中國的民主希望,已被你們打成炮灰了!”⒁
張育仁這樣評價道,“以“文人論政”為職業操守的自由主義者們,他們除了空懷自由主義的凌云壯志,從來就沒有搞清楚中國的“政治”到底為何物,更談不上懂得‘政治技巧’。”⒂
《大公報》在“重慶談判”問題上表現出來的一方面抵制內戰,另一方面有些傾向蔣介石政府的矛盾心態,是其“文人論政”特征的體現。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接受西方思想的熏陶,以筆為武器,言論救國。但是他們在整個政治舞臺上始終是配角,雖發揮了道德力量,但實際的政治作用則幾乎為零。他們最后被卷入險惡的政治浪潮,無力自拔,“道統”始終不敵“政統”。
2、“左右開弓”與“左右不是”的“中間道路”
在1945年,民盟一大通過了它的政治綱領。在1946年的政協會議上,這項方案也被國共兩黨所接納。當時的自由主義者們就開始謀劃獨立于國共兩黨之外的“中間路線”。當時《大公報》也在政治立場上選擇了“中間道路”,不親共產黨也不親國民黨。雖然在自由主義道路的探索上,《大公報》留下了光輝的一筆。可是在他們必須面臨的國家命運面前,仍然無法擺脫悲劇的命運。在具體的歷史情境下,《大公報》批評國共雙方,最終遭到了兩邊的打壓。
和共產黨方面起沖突主要是因為王蕓生在《大公報》上發表的那篇著名的《可恥的長春之戰》。
事件緣起于1946年美英蘇三國簽署了《雅爾塔協定》,其中的外蒙古和東北問題使中國人十分氣憤。《大公報》就此事發表了陳詞軒昂的社論,并且隨后,20多位著名的知識分子們發表了題為《我們對雅爾達秘密協定的抗議》的聯名文章,刊登在《大公報》的“星期論文”上。文章一經發出,各路知識分子、市民和學生進行了游行示威,并且提出了“反蘇”的口號。1946年4月13日,蘇軍即將撤離長春,國共雙方開始對峙起來。4月16日王蕓生發表了社論《可恥的長春之戰》,稱“進攻的戰術,常是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鋒。徒手的先鋒隊成堆成群地倒了,消耗了對方的火力之后,才正式作戰,請問這是什么戰術?殘忍到極點,也可恥到極點……蘇軍剛邁步走去,國家接防立腳未穩,中共的部隊四面八方打起來了,且已攻入市區。……流的卻是中國同胞的血!中國人想想吧!這可不可恥?”⒃這篇社論一出手,立即引起了中共的強烈憤怒,并反擊它:“……大公報里有好人的,但它的社論作者,原來是這樣一個法西斯的有力幫兇,在平時偽裝自由主義,一至緊要關頭,一至法西斯有所行動時,替吃人的老虎當虎倀……”⒄對此抨擊,王蕓生并未立即回復。5月30日,王蕓生發表了題為《論宣傳休戰》的社論,“我們努力維持可憐的人民立場,努力保持頭腦清明,心境平和……同一立場,兩面受攻,一面飛來紅帽子,使我們苦笑,另一面又罵你是‘幫閑’,罵你是‘法西斯幫兇’,更使我們莫名其妙。奉告一面,不可為淵驅魚,把天下都看作共產黨。奉告另一面,要爭政權,就不要作踐人心……”⒅
《大公報》引起國民黨的強烈不滿是因為其反對美國在戰后不遺余力地扶植日本軍國主義。
王蕓生等在1947年2月考察了日本,回來后發表了十多篇通訊在《大公報》上。文章中對親眼所見的美軍扶植日本軍國主義的行徑感到不滿。隨即,在《大公報》發表文章《麥克阿瑟手上的一顆石子》:“日本有句成語叫‘一石二鳥’,而今日本正是麥克阿瑟手上的一顆石子。他拿這顆石子預備打兩鳥:一是對付蘇聯,二是警備中國。”⒆這番言論對國民黨是沉重的打擊,似乎代表著《大公報》已經開始為共產黨說話了。國民黨中央機關報《中央日報》1947年12月30日的社評可以體現當時國民黨對《大公報》的態度:“至于大公報王蕓生之流,其主義為民族失敗主義,其方略為國家分裂主義。主義與方略具備,現在又有行動了。他的行動就是不左也不右,政府與共產、美國與蘇聯一起罵的,未必即是自由主義者。”⒇
隨后,國民黨“三查”王蕓生,王蕓生對國民黨的最后一絲希望也幻滅了。兩年前重慶談判時風光一時的自由主義分子最終只淪為了國共兩黨相互廝殺的政治棋子。
【本文系天津師范大學“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計劃項目”《立體時空中的活態歷史——天津地方新聞史新探(1886-1949)》成果,項目編號201410065008】
參考文獻
①②④⒂張育仁:《自由的歷險:中國自由主義新聞思想史》[M].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440、12、496
③左玉河,《最后的絕唱: 1948年前后關于自由主義的討論》[J].《四川大學學報》,2008(4):48
⑤《上層知識分子的責任》[N].天津版《大公報》,1940-05-10
⑥《日本投降了》[N].重慶版《大公報》,1945-08-14
⑦《毛澤東先生來了!》[N].重慶版《大公報》,1945-08-28
⑧王蕓生、曹谷冰,《1926至1949的大公報》[C].全國政協《文史資料選輯》第28輯,中國文史出版社,1962:89
⑨《歡迎馬歇爾將軍》[N].天津版《大公報》,1945-12-21.
⑩《歡迎停戰令下》[N].津版《大公報》,1946-01-11
⑾⑿《政治協商會議的成就》[N].天津版《大公報》,1946-01-31
⒀王芝琛:《一代報人王蕓生》[M].長江文藝出版社,2004:87
⒁《我們反對武力解決!》[N].天津版《大公報》,1946-05-20
⒃《可恥的長春之戰》[N].天津版《大公報》,1946-04-16
⒄《可恥的大公報社論》[N].《新華日報》,1946-04-18
⒅《論宣傳休戰》[N].天津版《大公報》,1946-05-30
⒆《麥克阿瑟手上的一顆石子》[N].上海版《大公報》,1947-10-04
⒇《社評》[N].《中央日報》,1947-12-30
(作者單位:天津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新聞系)
責編:姚少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