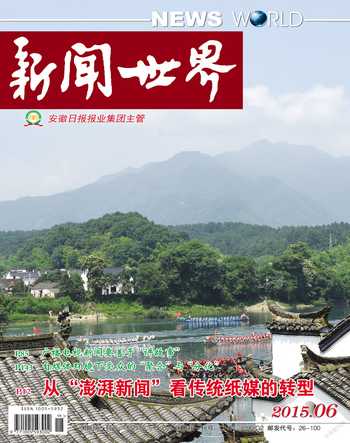虛擬社會造成的現(xiàn)實陌生化
趙新寧
【摘要】數(shù)字化媒體時代,由于其交互性、匿名性和可復(fù)制性等特征,使得現(xiàn)實虛擬化,人們極容易陷入一種虛擬與現(xiàn)實混沌不分的沉迷狀態(tài),虛擬與現(xiàn)實同時變得陌生化。本文借用文學(xué)語言的陌生化理論,分析了虛擬社會導(dǎo)致的現(xiàn)實虛擬化,情感陌生化和關(guān)系疏遠(yuǎn)化等結(jié)果,并對其進(jìn)行了哲學(xué)思考。
【關(guān)鍵詞】虛擬社會情感陌生關(guān)系疏遠(yuǎn)
“陌生化”的概念是由俄國形式主義美學(xué)的代表人物之一什克洛夫斯基提出來的。他認(rèn)為,藝術(shù)不是現(xiàn)實的反映,而是對現(xiàn)實的陌生化,藝術(shù)的目的是要人感覺到事物,而不是僅僅知道事物①。陌生化即通過對生活常態(tài)的非常態(tài)表現(xiàn),喚起人們新鮮陌生的感覺和體驗,打破對現(xiàn)實世界的習(xí)慣性知覺方式。
文學(xué)意義上的這種定義把陌生化作為一種手段,它涉及作者、文本、讀者與世界四個主體,在讀者與作者、讀者與文本之間產(chǎn)生一種陌生感和距離感,以此來增加文本的理論高度。
陌生化作為一種技巧性策略和經(jīng)驗性過程,它的形成和運(yùn)用具有一種動力帶的作用,一方面呈現(xiàn)出客觀學(xué)科的特點,另一方面,促進(jìn)實現(xiàn)社會學(xué)家主觀上提高理論學(xué)術(shù)抽象性的目的②。雖然陌生化屬于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范疇,但它強(qiáng)調(diào)的是反常規(guī)創(chuàng)作,具有比較廣泛的適用性。在這里,陌生化也可以作為一個媒介過程來運(yùn)用。
虛擬社會關(guān)系是伴隨數(shù)字媒體的發(fā)展而形成的一種新型社會關(guān)系,人與人之間呈現(xiàn)一種符號化、抽象化的溝通與交互狀態(tài),虛擬化生存已成為人們的生活方式,并改變著人們的思維方式、價值規(guī)范和交往方式,影響著政治、經(jīng)濟(jì)、社會和文化等整個的媒體生態(tài)環(huán)境。新媒體形態(tài)下的這種社會存在,對現(xiàn)實的人際關(guān)系賦予新的內(nèi)涵,使現(xiàn)實陌生化。
一、現(xiàn)實虛擬化
鮑德里亞說,“在通向一個不再以真實和真理為經(jīng)緯的空間時,所有的指涉物都被清除了,于是仿真時代開始了,人工指涉物在符號系統(tǒng)中復(fù)活了。符號是一種比意義具有更大延展性的物質(zhì),這不是模仿或重復(fù)的問題,也不是戲仿的問題,而是用關(guān)于真實的符號代替真實的問題,這是一個超穩(wěn)定的、程序化的、完美的描述機(jī)器,提供關(guān)于真實的所有符號,割斷真實的所有變故。”③
1、虛擬的表現(xiàn)
“虛擬”一詞,已經(jīng)廣泛應(yīng)用到社會經(jīng)濟(jì)生活中,尤其是計算機(jī)軟件行業(yè),電腦網(wǎng)絡(luò)數(shù)字化等虛擬技術(shù)迅速發(fā)展,出現(xiàn)了虛擬經(jīng)濟(jì)、虛擬企業(yè)、虛擬銀行、虛擬大學(xué)、虛擬政治、虛擬戰(zhàn)爭、虛擬共同體等。虛擬存在打破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虛擬空間和現(xiàn)實社會的界限也變得越來越模糊。
數(shù)字技術(shù)憑借便捷的交互傳播,超越了時空限制,構(gòu)建了一種符號化的影像。在這個過程中,信息接收者或發(fā)布者很容易產(chǎn)生一種實時信息交換的“擬真”的幻覺,虛擬的信息產(chǎn)品成為現(xiàn)實的替代品,不知不覺地隱沒了現(xiàn)實世界與虛擬世界之間的界限。
2、虛擬社會的特點
虛擬社會的主要特點是匿名化、低限制和弱聯(lián)系。匿名化是指每個參與主體都有屬于自己的數(shù)字化的ID,可以自由選擇自己的姓名、性別、形象甚至交往環(huán)境。低限制是指虛擬空間里的制約極少,任何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他人交往,克服了現(xiàn)實中身份地位等的不平等。弱聯(lián)系是指交往主體之間的溝通聯(lián)系較弱,主體隨時可以更換對象。
虛擬社會的這些特點,使個體的虛擬身份與現(xiàn)實身份的識別完全不同,不再具有現(xiàn)實中的唯一性、區(qū)別性和異質(zhì)性,造成了個體身份認(rèn)證的弱化,社會成員之間的互動變化基礎(chǔ)發(fā)生了根本性變化。
馬克思說,人的本質(zhì)在現(xiàn)實性上是一切社會關(guān)系的總和,人實際上是屬于一定的社會形式的④。人作為世界上唯一具有認(rèn)識自我的本性、唯一能夠認(rèn)識自我的存在物,唯一具有自覺自為意識的生物體,人在自我的意識中,將人與世界把握為“關(guān)系”性的存在,并進(jìn)行著認(rèn)識和實踐的“對象性”活動,力圖把世界變成對人來說是真善美相統(tǒng)一的現(xiàn)實。
然而,當(dāng)人們對虛擬社會與現(xiàn)實世界混淆不清的時候,人們實踐活動所獲得的經(jīng)驗,便難以區(qū)分是現(xiàn)實的真善美還是虛擬的認(rèn)知快感,在這個模式化的數(shù)字過程中有可能使人們的審美過程喪失想象的創(chuàng)造力。
虛擬技術(shù)把人們在現(xiàn)實中的身份和角色變成了符號,消除了人們在現(xiàn)實中的地位、相貌等顧慮,伴隨這樣的過程,人們的工作方式,休閑方式和交往方式等都變得符號化,主體的活動變?yōu)橐环N符號化的虛擬存在,由此產(chǎn)生的社會關(guān)系也是虛擬化的。拋開現(xiàn)實中的面具,人們的存在和互動便具有了模糊性。
這樣的實踐對象活動沖擊了認(rèn)識主體的認(rèn)知知覺,并對人的自我意識的認(rèn)識產(chǎn)生影響,使其難以獲得獨(dú)特的認(rèn)知經(jīng)驗。在這種境域之下,活動主體存在的關(guān)系是弱化的,那么,現(xiàn)實社會中各種機(jī)制體制也難以發(fā)揮剛性的約束,人們的責(zé)任感和義務(wù)觀念程度降低了,維系虛擬社會的組織和制度力量,較現(xiàn)實社會相比變得弱化,人際關(guān)系松散的趨勢就難以避免。
二、情感陌生化
辯證地來看,數(shù)字技術(shù)增強(qiáng)了社會支持網(wǎng)絡(luò),伴隨而來的消極影響也令人堪憂。以移動新媒體手機(jī)為例,越來越多的人患上了“手機(jī)依賴癥”,表現(xiàn)為人們已經(jīng)無法離開手機(jī)。
現(xiàn)在的家庭聚會、同學(xué)聚會等再也看不到傳統(tǒng)社交模式的模樣了,因為即使花費(fèi)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把想要見面的人聚在一起,人手一部手機(jī)的場面比比皆是,只為逃避暫時的冷場。網(wǎng)上非常流行的一句話是“世界上最遠(yuǎn)的距離,就是我在你旁邊,你卻在玩手機(jī)”,形象地表達(dá)了手機(jī)依賴導(dǎo)致的情感缺失。中國人的感情表達(dá)本來就比較內(nèi)斂,過多將自己陷在手機(jī)世界中,只是停留在“人機(jī)對話”的交流上,容易忽略現(xiàn)實生活中的人際交往,造成社交圈子變窄,生活圈子縮小,注意力的分散,孤獨(dú)感的增加。公共社交場合,只顧低頭玩手機(jī),面對面的表情、語調(diào)、眼神等直接交流被淡化忽視,甚至對面對面的社交產(chǎn)生恐懼和抵觸的情緒。
哈貝馬斯在交往行為理論中提出了生活世界的系統(tǒng)二元社會模式。他認(rèn)為,人們不但生活在進(jìn)行文化再生產(chǎn)的生活世界的境域中,同時還生活在負(fù)責(zé)進(jìn)行物質(zhì)再生產(chǎn)的系統(tǒng)中。現(xiàn)實的情景卻是,人們的生活過多地依賴于物質(zhì),造成“生活世界殖民化”,即“社會合理化的過程首先源于生活世界的理性化,由此導(dǎo)致體制層面的理性化,最后出現(xiàn)生活世界的體制殖民化。”⑤
移動新媒體作為社會物質(zhì)再生產(chǎn)的產(chǎn)物,人們對其的過度依賴正是“生活世界殖民化”的結(jié)果,對工具過度合法化而缺乏對工具的正確認(rèn)識和理性批判。使用行為本身具有一定的隱蔽性,隱藏了工具持有者內(nèi)心的原始真實的想法。大量未過濾的信息導(dǎo)致的了選擇焦慮癥,剝奪了我們自身的時間和注意力,持續(xù)的多任務(wù)狀態(tài),改變了人們的思維方式,降低了人們的思考能力,人際交流的情感陌生難以避免。
三、關(guān)系疏遠(yuǎn)化
無論對于傳統(tǒng)媒體還是新媒體,“關(guān)系”都是一種重要的生產(chǎn)力,其中交往主體的信任機(jī)制是關(guān)系維持的重要基礎(chǔ)。雖然媒體環(huán)境發(fā)生了變化,信任機(jī)制仍然是虛擬社會聯(lián)系的重要紐帶,但這種關(guān)系因新媒體形態(tài)的多樣化發(fā)生了變異。
其結(jié)果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基于血緣、地緣和業(yè)緣關(guān)系建立起來的主體間親密關(guān)系完全改變,網(wǎng)絡(luò)交往中主體呈現(xiàn)的無標(biāo)示狀態(tài)特征,極大地挑戰(zhàn)著傳統(tǒng)的價值觀念和倫理道德規(guī)范。
虛擬社會的人際交往,改變了人們的行為方式,并形成新的行為模式。人們在網(wǎng)絡(luò)中表現(xiàn)熱情,侃侃而談,在現(xiàn)實中卻反應(yīng)冷淡,沉默寡言,人與人之間的關(guān)系變得疏遠(yuǎn),信任感也愈來愈缺乏。
早在1997-1999年,Katz和Aspclen就做了全國性的調(diào)查,比較了網(wǎng)絡(luò)使用前后的社會參與程度。研究發(fā)現(xiàn),大量使用網(wǎng)絡(luò)會造成社會參與活動的下降,縮小社交圈,減少與家人的交流,同時增加個體的孤獨(dú)感,降低人際信任感。⑥
倪曉莉等人在《虛擬社會關(guān)系中的人際信任研究》一文中,以大學(xué)生為例,采用數(shù)據(jù)分析與統(tǒng)計方法,對其網(wǎng)絡(luò)使用環(huán)境下的人際信任、自我人格等心理因素進(jìn)行了調(diào)查評估,探索了虛擬社會關(guān)系中人際信任的影響機(jī)制。調(diào)查結(jié)果同樣表明,網(wǎng)絡(luò)使用過度,人際信任感低。
以微信所形成的社交關(guān)系為例,中國傳媒大學(xué)博士常寧將其解讀為,以利益需求為基礎(chǔ)的“臨時社交關(guān)系”:最易成為“僵尸關(guān)系”。微信平臺所形成的社交圈子形成了兩種關(guān)系,一種是真實的強(qiáng)關(guān)系,這種關(guān)系是由小圈子構(gòu)成,多是親朋好友,且是現(xiàn)實中的關(guān)系。這種強(qiáng)關(guān)系的穩(wěn)定性很高,即使不使用微信,依然通過其他方式聯(lián)系。另一種是基于某種利益需求臨時搭建的弱關(guān)系,這種關(guān)系越來越成為職業(yè)社交、工作范疇和營銷的工具,且范圍越來越大,它不依托情感來維系,只是為了滿足工作、社交或行銷的目的。
雖然網(wǎng)絡(luò)弱關(guān)系是人們獲得信息支持、社會資源、伙伴關(guān)系、補(bǔ)充給養(yǎng)真實社會關(guān)系的重要來源,但一旦沉溺于“符號虛擬人格”中,就混淆了真實角色和虛擬角色,容易迷失自我。
當(dāng)微信中工作營銷的需求越來越多,弱關(guān)系的比例就會越大,人們會因這些“被迫要看”的信息而身心俱疲,產(chǎn)生失落焦慮的情緒。這種臨時搭建的弱關(guān)系降低了社會交往主體之間的滿足感和安全感,破壞了關(guān)系的維系基礎(chǔ)。
參考文獻(xiàn)
①什克洛夫斯基著,劉宗次譯:《散文理論》[M].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4:10
②陳健、宋菲菲,《陌生化:社會學(xué)理論及其文本的運(yùn)用策略》[J].《齊齊哈爾大學(xué)學(xué)報》,2007(5)
③鮑德里亞:《仿真與擬像》[M].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330
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73、60
⑤阮新邦:《批判詮釋和知識重建》[M].社會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1999:67
⑥Katz J E, Aspclen P.Anation of Strangers?[J].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1997(12):81-86
(作者:河北大學(xué)新聞傳播學(xué)院研究生)
責(zé)編:姚少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