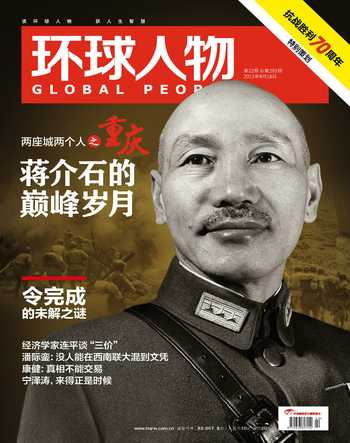康健:真相不能交易
李雪

康健,方元律師事務所主任,中華全國律師協會民間對日索賠訴訟工作指導小組副組長,二戰中國勞工對日索賠案律師團團長。
康健是最早介入二戰受害者訴訟的中國律師之一,但20年來,在媒體記者眼中,她一直是個謎一樣的存在,不少記者把她律所的名字都搞錯了。對于這些她從不在意。但對有些事,她非常在意,而且字斟句酌。
最近,有媒體報道了“三菱與中國勞工受害者談判團達成全面和解協議”的消息。正當引發國人叫好之時,康健言辭激切地潑了一盆冷水,條分縷析三菱偷梁換柱、避重就輕的種種作為,并表示“絕不急于求成而出賣道義和尊嚴”。
康健的律師事務所位于北京一個高檔小區,時值8月,院里的月季花開得正艷。進得門去,左手幾間深棕色的門緊閉著,靠墻一溜兒資料柜,柜頂摞著一些標牌,只能看到其中一個是:中國政法大學法律碩士實習基地。右手兩張老式黑色皮革沙發,背靠一個儲存雜物的小隔間。幾個工位占據了客廳的中心位置,飄窗上隨意擺著幾盆綠植,兩邊垂著半舊的窗簾。與一些時尚精致的律所不同,這里平實樸素,沒有絲毫多余的裝飾和自我標榜。
“康律師正在打電話,請您稍等。”招呼《環球人物》記者坐定,兩名工作人員靜靜地回到了電腦前,偶爾討論一句工作。一扇關著的門里,隱約傳來康健的聲音,底氣十足,滔滔不絕。其間,康健出來一次,分派了一些工作。她年近六旬,嬌小干練,微微燙過的頭發有些蓬松,半袖襯衫,齊膝黑裙,坡跟皮鞋。“不好意思,手頭有點事,再等我一會兒。”她客氣地道歉,又旋風似的回到屋里,繼續打電話。
半個小時后,康健走出來,把記者迎進了另一間辦公室。話題從近期三菱與中國勞工和解開始。就在報道后不久,8月3日,幾家二戰中國三菱受害勞工團體表示,雖然不盡滿意,但考慮到幸存者年事已高,時間迫切,“和解是可以接受的”。
2015年8月7日,康健在律所接受本刊記者采訪。
對此,康健堅決反對讓步。她首先對三菱的表態提出強烈質疑,“三菱把它當年跟日本政府共同策劃實施的強虜中國勞工的行為,輕描淡寫地說成被動接受勞工;把對勞工的奴役說成使用;把折磨致死的722名勞工輕描淡寫地說成死亡——改變了性質,曖昧了事實,這種謝罪能稱得上是真誠的謝罪嗎?!并且,三菱支付給每位受害者的10萬元也不是賠償,是為中日友好建立的基金。”
康健語氣堅定地說,“現在已經戰后70年了,如果我們還簽一個不清不楚的協議,我感覺日本又會翻案。所以,我寧肯擱置、寧肯退出,也不想以犧牲事實真相為代價解決這個問題。”
同時,她還提到了國內不同受害者團體之間的不和諧。現在,我國有數個中國受害勞工團體,主張、立場各異。“很早的時候,我們就提過希望國內各個受害者團體能聯合起來,一致對外。但是這種各立山頭很難避免,一方面日本對某些受害者代理人起了一些引導作用,另外一方面是利益問題。日本人在戰爭期間就愛搞離間活動,而中國人又很容易被人家離間。”
常年與日本政府、企業打交道,讓康健十分謹慎。正如她拒絕談自己的情況,甚至連出生年月也不愿說,偶爾跳出來一兩句,她立即回過神,“不要寫到文章里。”這種低調謹慎,一方面是性格使然,另一方面則是一種策略。“日本很注意收集情報的,他們也不叫間諜,就是會很細致地收集各種信息。我覺得,有些信息還是不宜散布,所以我不太愿意接受記者采訪。”
“日本人是很細膩的,壞事好事都會做得很極致。可是我們中國人老是盲目自大,缺乏那種細膩。歷史事件確認就得靠細膩,否則你這個‘歷史真相’就容易被推翻,這就是為什么我們這么看重對事實的確認,把事情細化到窮盡。”這種細,直接反映在了康健的工作中。每項調查不但要錄像,還有筆錄,而且細枝末節全要調查。調查一個人最少要問3次,一次基本上要問兩三個小時,回來再整理,所以要完成一個人的調查得40多個小時。“我們的起訴要求也是這樣很細的,起訴書有3萬多字。”
最早的民間對日索賠始于1995年,康健以律師身份介入此類訴訟也始于這一年。那年,康健參加聯合國第四屆婦女大會,日本女律師大森典子提出要給中國山西慰安婦訴訟提供法律援助,想請她幫忙調查。康健同意了,“我想只不過協助調查,而且這事應該很簡單,調查一次就完了。”
直到1996年第一次去日本出庭,康健才覺得這個事情得嚴肅對待。“作為中國人,我覺得日軍強奸婦女的這種罪行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去了以后,我才感覺到,日本官員雖然曾在公開場合表示反省,但在具體事實上,他們從來都是回避的——對他們而言,反省只是一個空洞的中性詞。”
康健沒想到,自己一干就是20年。20年間,為了調查慰安婦和二戰中國勞工,她跑遍了北京、天津、上海、山西、河北、山東、河南、海南、遼寧。“那時候,一方面是人不好找,另一方面,交通也非常不好。有一次,我們去山西一個非常偏遠的山區做調查,因為車的底盤低進不去,我們租了面粉廠一輛五十菱卡車,路太顛,只能用手緊緊地抓著車。調查完再出山的時候,手磨出三個泡。”
20年間,她參與了3件慰安婦案,11件勞工案,其中有5件作為輔佐人,“輔佐人坐在代理席上,在法庭上可以向對方提問,也可以發言辯論。”一個案件持續的時間最短是6年,一般是9年,康健告訴記者:“按照國際慣例來說,這個時間是比較正常的。一旦我堅持不住了,我們律師團里還有年輕的律師。”2010年,二戰中國勞工對日索賠案律師團正式成立,一共有8名律師。
康健義務打官司,幾乎耗盡了自己的收入。有時候勞工為了打官司從外地到北京的路費、食宿費,都是康健出。因為在這上面投入太多精力,她也會失去一些“名利雙收”的機會。不過她并不糾結,“我這人比較一根筋,只要投入了,我就不去考慮旁的東西——干這個必須得自甘清貧。有一點,我特別自豪:我沒破產。家里人也不指望著我掙錢,就是怕我太累了。”
如今,中國民間對日索賠已有30多起,涵蓋了大屠殺、慰安婦、武裝轟炸、勞工、毒氣彈、細菌戰等。雖然極少有勝訴的,但相關案件得到的媒體關注度也越來越高,越來越多的人了解到那段歷史。
作為律師,康健無疑是理性、堅韌的。但在調查中,慰安婦、勞工的遭遇,卻讓她唏噓感慨。在山西調查慰安婦時,康健遇到了一個姓侯的老太太,這么多年了,她怎么都忘不了那位老人。“13歲那年,她和父親被帶到日軍據點,因為有人告發她父親與八路軍有聯系。3名日本兵先是拷打她父親,然后把他捆了塞到農村土炕的炕洞里,又在炕上強奸了她……老人邊哭邊說,因為覺得難以啟齒,說著說著,就趴在我的耳朵邊上說。說到傷心處,老人竟從凳子上滑下來,差點摔在地上。”
康健有些哽咽,一直靠在椅背上的她直起身來,停頓了一會,才接著往下講。“后來,她就精神失常了,家里人把她贖回來之后,養了一年多,才差不多恢復了。又過了幾年,她結婚了,但丈夫知道她這個遭遇以后,又和她離婚了。她一共結了三次婚,最后一任丈夫對她還可以。1998年左右,她去日本出了一次庭,回來到北京的時候,我帶著她去天安門、故宮看了看。她特別高興,還照了張照片。但我們那個相機膠卷不好,洗出來也不好看,我想等她再次來時,再給她拍幾張。沒想到,回去沒幾個月,她就去世了。每次我去那邊的時候,都會去她墳頭上看看。”
康健說,受害者的講述每每讓她被震撼,被刺痛。“一方面我很同情他們。但我們做調查還得問細節,問著問著,我就想掉眼淚,但我得忍著,特別難受。另一方面,我也覺得特別內疚,這么多年,這些受害者好像被遺忘了。他們跟我說,你能幫我出這口氣,我死都不白死了。”
集中調查的那幾年,這種痛苦常常纏繞著康健,吃不下飯、睡不著覺,她也不斷告訴自己千萬別精神崩潰。但她從來不把這種痛苦告訴家人和朋友,一來是出于“為當事人保密”的職業習慣,二來是“說一遍還要再痛苦一次”。
她能做的,就是幫這些受害者起訴,幫他們出口氣。“我感覺他們最期待的不是錢,而是名譽問題,打官司一定要把事實真相打出來。我也有想放棄的時候,這些老人很多都去世了,我不做他們也不會知道,但是我覺得我會對不起自己的良心。”
20年前,不少幸存者還健在,律師團還可以選擇一些身體好的到日本法院出庭;如今,在世的已經不多了。但康健覺得,在原則問題上絲毫不能妥協。這不僅來自于她與日本政府、企業打交道的深刻感受,也是她與她的日本戰友最大的不同。
康健告訴記者,她到日本出庭50多次,而日本政府代理人在庭上向來都不理睬他們。甚至有一次,日本代理人說:“你們中國周恩來總理曾說,中國人民是受害者,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如果按照這個邏輯,我們日本國民是不是也可以索賠?”康健反駁說:“當年周恩來總理說這句話,指的日本國民是軍國主義的受害者,不是中國人害你的,中國人沒有到你們國土上去做任何侵略行為。作為日本政府的代理人,連這個事件性質都給混淆的話,我覺得很遺憾。”她說完這話,旁聽的人都鼓起了掌。
在日本,不但有康健的老對手,也有她的老戰友——為中國受害者奔波的律師和志愿者們。“我非常尊敬他們,這么多年,投入了很大精力財力,非常不容易。他們對自己的定位是愛國主義者,他們認為自己是在幫助日本——幫助受害者出庭是讓日本國民認識這個歷史事實,進而獲得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的原諒和信任。所以,有時候我們還是有分歧的。日本律師覺得,有一個基本能接受的事實就可以了;而我們覺得,事實是不能曖昧的。我們的原則是:在承認事實的基礎上謝罪、承擔責任。賠償金額可以討論,但原則沒有討價還價的余地。不能以犧牲歷史真相為代價換取那10萬塊錢,真相不能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