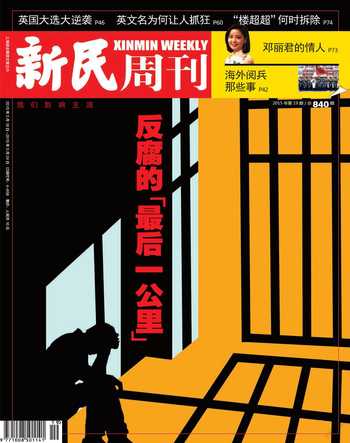讓貝多芬回歸高貴
橙客
有一種聲音以粗糲爛漫為美,比如5月7日晚圣彼得堡交響樂團在東藝音樂廳演奏的肖斯塔科維奇。有一種聲音以精致凝練為美,比如5月8日和10日晚安茲涅斯和馬勒室內樂團在上交音樂廳演奏的貝多芬。后者讓我真正明白,一流樂團和二流樂團之間的區別——不在于歷史長短,不在于編制大小,甚至不在于指揮是誰,關鍵在于樂團的每一個人有沒有以一種貴族精神全身心投入演奏。
馬勒室內樂團的成立時間尚不到20年,這個樂團的成員來自20個不同的國家,他們仿佛有著“共濟會”式的普世理想,聚在一起只為打造出一座完美的音樂博物館。現年45歲的挪威鋼琴家安茲涅斯于2012年開始攜手馬勒室內樂團踏上“貝多芬之旅”,以鋼琴協奏曲與合唱幻想曲為核心曲目,三年來走遍世界各地,其間錄制的專輯獲得多項殊榮,這個樂季是安茲涅斯與馬勒室內樂團“貝多芬之旅”的最后一程。
康定斯基曾將藝術形態比作金字塔,越往上藝術家和作品就越少,他說:“金字塔的頂端上經常站立著一個人。甚至那些在感情上和他最接近的人也不能理解他。貝多芬生前就是這么一個挺立著受盡辱罵的孤獨者。”貝多芬死后,人們漸漸理解了他的音樂,音樂家們尊他為樂圣。到了我們這個貴族精神早已沒落的世界,處于金字塔頂端的貝多芬被徹底庸俗化。樂圣的幾個流行曲調在大街小巷反復播放,他的名字淪為鋼琴品牌和房地產商標,想要附庸風雅的商品爭先恐后地利用這個古典標簽。貝多芬若九泉之下有知,一定會深感欣慰。他一輩子都在納悶自己的名字為什么是路德維希·凡·貝多芬,而不是路德維希·馮·貝多芬——姓氏“馮”(Von)意味著貴族血統。他甚至試圖通過打官司證明自己的貴族身份,卻終究輸了官司。
在古典音樂界,一代代演奏家不斷放大著這位狂人野蠻的一面,他向命運抗爭的動機成為英雄主義的標志。當大多樂團和鋼琴家都在追求更宏亮、更浪漫的效果時,人們漸漸忘記了貝多芬鋼琴協奏曲的本來面目。正如18世紀前后的鋼琴協奏曲并非是我們今天習以為常的宏大音響,貝多芬的鋼琴音樂也是隨著鋼琴制作工藝的進步而隨之演進的,其在創作初期留下的鋼琴協奏曲展現了與其后期創作截然不同的細膩優雅的一面,他的貴族情結在這里一覽無余。
安茲涅斯的演奏突出了這一點。他仿佛化身挪威王子,率領王室成員進行一場華麗的儀式。按照儀式的古老傳統,鋼琴家就是指揮,于是我們看到鋼琴置于舞臺中央,安茲涅斯背對聽眾,在演奏間隙慷慨激昂地指揮樂隊。如果說安茲涅斯是騎士,那么馬勒室內樂團就是一匹難得一見的千里馬,演奏風格的匹配注定了“貝多芬之旅”如此成功。甚至可以說,是這個充滿陽光的樂團成就了安茲涅斯的“貝多芬之旅”,他們的音響發出金屬般的色澤,每一個人的演奏都是全情投入,并未因為已巡回演奏這套曲目多年而出現絲毫油滑。這種一絲不茍的態度還體現在一處細節:當開場的《第二鋼琴協奏曲》第一樂章演奏結束,遲到的聽眾紛紛入場,演奏家們非得等到每一位聽眾都坐下了才開始第二樂章,兩個樂章之間暫停了足足兩分鐘之久!
5月10日晚的音樂會出現了更為離奇的一幕。又是樂章之間,聽眾席一角傳來熱烈的掌聲。上海的聽眾好歹也是受過多年藝術熏陶的,一陣白眼把掌聲翻了下去。不成想,下一個樂章之間,還是那個角落再次傳來熱烈的掌聲——這次只有一個人在鼓掌,放眼望去,一男士坐得筆直,不顧周圍人的勸阻,毅然決然繼續鼓掌,演奏家們搖頭苦笑。我心想,這位男士大概是反感西方音樂會樂章間禁止鼓掌這種陳規陋習吧,但歐洲樂團遠道而來,是不是應當尊重人家的文化習俗呢?更沒想到的是,一曲結束后,那個角落再次傳來巨大響聲——這次是一位女士尖利的訓斥聲,她在破口大罵那位鼓掌的男士——舞臺上的樂團成員不知所措地看著臺下這一景象,目瞪口呆……
這兩晚的“貝多芬之旅”異常精彩,只是,當旅途結束,我們是否還會記得貝多芬的貴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