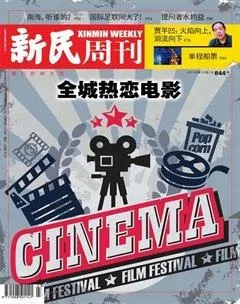當(dāng)金融打倒實(shí)業(yè)
鄭若麟
2008年美國(guó)雷曼兄弟銀行倒閉幾年之后,我曾應(yīng)邀為國(guó)內(nèi)一家電視臺(tái)撰寫有關(guān)歐美金融危機(jī)的紀(jì)錄片腳本。盡管我既是金融外行,又是電視紀(jì)錄片外行,但因當(dāng)時(shí)我在巴黎,可以通過采訪法國(guó)專家,為國(guó)內(nèi)觀眾帶來法國(guó)對(duì)金融危機(jī)的觀點(diǎn)。然而當(dāng)我費(fèi)心費(fèi)力采訪了幾十名法國(guó)專家、準(zhǔn)備寫稿時(shí),國(guó)內(nèi)已經(jīng)對(duì)這一主題不再感興趣。但我的付出并沒有白費(fèi)。幾個(gè)月的采訪,讓我這個(gè)金融外行終于明白了這次金融危機(jī)的來龍去脈。
當(dāng)時(shí)我認(rèn)為,金融危機(jī)是一帖清醒劑,只要理解了這一點(diǎn),我們就會(huì)對(duì)那些所謂的金融創(chuàng)新等所有“以債務(wù)為生財(cái)手段”的做法有所警惕。五年后我才明白,現(xiàn)實(shí)遠(yuǎn)比我想象的復(fù)雜,大多數(shù)國(guó)人似乎迄今為止依然對(duì)危機(jī)的緣由云里霧里……
事實(shí)上,危機(jī)產(chǎn)生原因就在于當(dāng)今世界的金融體系本身。金融的實(shí)質(zhì),就是債務(wù)。債務(wù)是金融的原材料,是金融領(lǐng)域發(fā)財(cái)?shù)拿孛堋>腿缤褪鞘凸局赂话l(fā)財(cái)?shù)脑牧弦粯印0l(fā)行債務(wù)是金融生財(cái)?shù)闹饕馈?008年的金融危機(jī)來源于美國(guó)私人金融機(jī)構(gòu),即“占領(lǐng)華爾街”運(yùn)動(dòng)所反對(duì)的那1%的金融巨頭。這部分1%的人控制了幾乎50%的世界財(cái)富。他們的過度貪婪,使他們?cè)谕媾獋鶆?wù)時(shí)玩過了頭,結(jié)果債務(wù)造成資金鏈的斷裂,從而導(dǎo)致整個(gè)金融體系的運(yùn)轉(zhuǎn)失靈。
歷史已經(jīng)反反復(fù)復(fù)證明,當(dāng)金融脫離了實(shí)體經(jīng)濟(jì),開始其“以錢生錢”、“以債生錢”的生涯時(shí),當(dāng)一個(gè)社會(huì)經(jīng)濟(jì)體的債務(wù)達(dá)到一定程度時(shí),其對(duì)社會(huì)有百害而無一利。能夠獲利的只有那些手頭擁有大筆現(xiàn)金以及交易權(quán)的人。看看今天法國(guó)社會(huì)即可知,發(fā)財(cái)致富的人基本上集中在金融銀行家和房地產(chǎn)商。他們利用手中的巨額金錢,在法國(guó)呼風(fēng)喚雨,左右一切。最高明的一招就是利用法國(guó)國(guó)民議會(huì)的“昏昏”,于1973年1月3日通過了著名的《銀行法》,使法國(guó)國(guó)家從此走上“債務(wù)預(yù)算”的道路。這部法律規(guī)定法國(guó)國(guó)家不能從中央銀行以零利率借款,而必須向私人銀行以4%的利率借貸。銀行家們“空手套白狼”,一手從中央銀行以零利率借出資金,另一手則再以4%的利率借給國(guó)家。40年來,法國(guó)國(guó)家因此而欠下了高達(dá)20378億歐元的債務(wù)(而2014年法國(guó)國(guó)內(nèi)生產(chǎn)總值為21340億歐元,債務(wù)已經(jīng)達(dá)95.4%)。法國(guó)每年預(yù)算的最大開支,就是支付這筆巨額債務(wù)的利息,大約為500億歐元左右。而與此同時(shí),法國(guó)每年還要支付按年償還的本息債款大約1500億歐元(法國(guó)2014年全年稅收為2789億,其中一半以上用于歸還債務(wù)本息的一部分)。由于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乏力,法國(guó)國(guó)家不得不平均每年發(fā)放2300億歐元的債券,來支付這筆開支,這又使銀行家們賴以生財(cái)?shù)摹霸牧稀薄獋鶆?wù)又進(jìn)一步增多……
法國(guó)的例子令人觸目驚心。但我們似乎對(duì)此毫無所知。我們的金融領(lǐng)域也在以加速度的方式迅猛發(fā)展。在全球性危機(jī)的浪潮中,我們的“理財(cái)產(chǎn)品”花樣日益增多。我們的期貨交易種類和批準(zhǔn)項(xiàng)目也越來越多。也就是說,在中國(guó)與在法國(guó)和其他老牌資本主義國(guó)家一樣,“以錢生錢”、“以債務(wù)生錢”的方式越來越流行。事實(shí)上在法國(guó),金融已經(jīng)是掙錢最多的職業(yè)。法國(guó)的精英日益涌向金融領(lǐng)域,造成的結(jié)果就是今天法國(guó)其他行業(yè)、特別是制造業(yè)人才的明顯匱乏。達(dá)索有一篇文章曾一針見血地提出過這個(gè)問題:法國(guó)產(chǎn)業(yè)的空洞化使法國(guó)走向衰退;而產(chǎn)業(yè)空洞化的原因就是人才匱乏。
當(dāng)一個(gè)社會(huì)推崇的是“以錢生錢”而非勞動(dòng)、制造獲利時(shí),這個(gè)社會(huì)必然會(huì)導(dǎo)致貧富分化和社會(huì)創(chuàng)造力退化,國(guó)家走向衰弱。如果說,法國(guó)經(jīng)過了整整一個(gè)世紀(jì)的創(chuàng)造力鼎盛時(shí)代,今天才走到“資本”壓倒“勞動(dòng)力”的所謂“后工業(yè)社會(huì)”階段,我們國(guó)家卻似乎還沒有走完工業(yè)化全程,就已經(jīng)步上同一歸途。這對(duì)中國(guó)未來的走向和發(fā)展必然會(huì)產(chǎn)生嚴(yán)重影響。